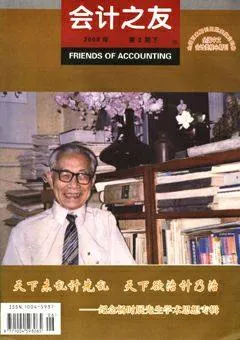杨时展:我这几年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学报的同志要我写写我的情况,却之,不可,实在又“乏善足陈”,就从我这几年的一些想法写起。
《庄子·逍遥游》:“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
会计这门科学和技术,在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确也有个“所用之异”的问题。或以致富强,或止于记青菜、萝卜。
今天,我们国家经济要起飞,从上到下普遍感觉到:管理上不去,经济工作一定上不去。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狠抓管理,而经济效果仍不理想,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抓在点子上。会计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子。会计上不去,管理也必然上不去!今天,在我们国家,从宏观责任人到微观责任人,恐怕很少有人理解并接受这个观点;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会计的作用以及会计和完成他们责任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管理学院、系、科的责任人,也很少了解并接受这个观点。而在西方国家,不精通会计的,就很少能充任经济工作或管理院、系的责任人,管理院系也没有不把会计学科放在数一数二位置上的。会计科学的落后,是我国经济工作落后的反映和结果,今天又反过来,成为我国经济工作落后的原因。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会计这门科学技术,同样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而且,由于底子薄,会计科学的现代化就更迫切。今天,眼看会计工作严重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作为这个岗位上的一个多年的卒子,实在不能不深感到责任的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主要力量就用在和大家一起,使我国会计科学尽早现代化这一方面。
一
我于1913年11月生于宁波。1936年毕业于前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组,得商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同年参加当时的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考试,获优等第二名,因而分发到当时国民政府最高会计机关:主计处会计局工作,以后又出任各机关的会计人员,并在大学里重兼任讲师。当时,政府正在先后推行预算法、会计法、公库法、审计法,这几年的实际工作,使我增加了不少有益的感性知识,使我至今可以不因“一行作吏”而自觉无法解嘲。
我于1945年春起改任国立各大学的正教授,既讲授会计各学科,也滥竽充数,讲授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经济思想史这些我在大学里学过的课程。我在大学里第一次开的课不是会计方面的,而是货币银行学;我在当大学生时第一次发表的论文也不是会计方面的,而是关于外汇控制的。我在初中三年级时,学校为了便于学生就业,加开簿记选课,我没有选;我进高中时读的是文科(当时的高中分文、理、师范三科),也有簿记这一选课,我仍没有选。我报考大学时填的志愿是金融系。学校却以报考金融人数太多,国家正在推行主计制度急需会计人员为由,安排我进了我从未感到过兴趣的会计系。就这样,我和会计科学就结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正如我和我的老伴一样,我和会计也是先“结婚”后恋爱的,感情还挺不错。看来,感情这玩艺,是可培养的。
当时的学校,无论大、中、小学,都实行聘任制。学校有聘任的自由,教师有去留的自由。我初上大学任教那几年,学校怕我走,连年加我的工资;以后,学校又怕我不走,于1948年秋开赶,这样,我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浙江,远走桂林。从那以后,我专任会计学科的教学工作。1949年11月,我36岁,桂林解放。1953年院系调整,来到本校,讲马卡洛夫,讲日布拉克,讲沙洛莫维赤。1980年恢复工作,进了我校的经济研究所。1981年秋,重回会计系,直到今天。一晃,四十多年了!国家的形势,经过几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回会计系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喜人形势已逼人而来,我按照系的要求,根据会计科学现代化的需要,参考美、加、日本十所大学会计系课程设置的情况,制定了一个会计教学改革的方案,并逐步由我和自己的几个课堂,实施起来。
二
1981年秋,财政部委托我校代培一批准备出国工作或深造的硕士研究生,从会计教学的改革出发,我决定采用美国J·A·Tracy的财务会计为教材。这是我解放后32年第一次在大学里讲授纯粹西方的财务会计学,第一次采用原文作教材。根据这批学生出国以后的反映,都认为这门课给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极为有益的基础。Tracy的书,以后由我校一位老师全文译出。由我作了精细的校改,交学校印行。可惜,没有引起意想中和应有的注意。我们的财务会计,可以说,至今基本上停留在50年代苏联那个并不高明的水平上。西方的财务会计,应该说,是从会计报表才正式开始的,而我们的财务会计,无论是会计学原理,或哪个行业的会计,一讲到会计报表,就结束了。这样,人家的起点,就成了我们的终点。且不说差距大,这样的教材还造成我们实际工作中报表归报表,实际归实际,报表和实际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可以由厂长、书记从心所欲的情况,自然谈不上用它来反映实际,指导实际,只好算玩笑!今天,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的并、转、关、停;破产、结算;租赁、出售;独资、合伙企业的兴起;公司的创设;股票的发行;票据、债券的通行;呆帐准备的提取;随着流通形式的多样化而来的销售、结算工作的多样化……等财务会计方面的问题,已迫切要求会计科学为它解决。而我们的教材却仍是三十年的旧惯,对这种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只字不提,作为一个会计学的教师,实在感到无法向人民交代。我国的财务会计,急需加快改造的步伐!
三
管理会计的情况却很令人鼓舞。
我在经济研究所时,即着手翻译美国R·M·Copeland和P·E·Dascher二人合著的管理会计学。1980年夏,译出全文,共25万来字。即以此书为教学参考资料,由学校印出。另外参考西方各家70年代以后的著作,自编教材,通过我校的闭路电视,向全校有关各系的学生讲授管理会计学。由于这门课程本身内容新颖,我在讲授时又注意突出它和传统会计的差别,使听课的学生对现代会计的内容和作用耳目一新,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其他兄弟院校的管理会计课程亦先后开出,一时成为各大学的热门。
管理会计课程的开出使社会上的广大会计人员有了会计知识更新的迫切要求。我校印行的Copeland和Dasher的书很快脱销。由我校学报建议,我在学报上以《管理会计通俗讲话》为题,连续十期刊载以管理会计为主的现代会计学。国内的读者对这一“讲话”普遍感兴趣。以后几年里,又分别在广州、武汉、上海、杭州、南昌、厦门、长沙、西安等地多次以“现代会计对传统的挑战”,“效益十策”,“微观效益基本”,“宏观控制的关健——目标”……等为题,介绍现代会计的内容、作用,由于新颖,在各地都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于此同时,我国会计学者自己编写的管理会计学亦先后在国内出版,管理会计在我校也终于由选修课而改为必修课,并成立了管理会计教研室。管理会计在我国就站稳了脚跟。今天虽然有时还能听到不承认它的声音,已不起主导作用了。
四
我的第三个目标是审计学。
审计学是中外各大学会计系的必修课。我解放前学过这门课,也讲过这门课,解放后停开。我国1982年秋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实施审计制度。在此以前,我校即接受财政部的任务,培养国家实施审计制度以后急需的第一批审计种子人才。1982年春,我校通过财政部和澳大利亚国家总署商定,由中澳两国合作,在我校开办审计培训班三期。由我根据国家审计的需要,订出教学大纲;由澳国专家根据大纲,写出教材;由我校组织力量,译成中文交学生使用,由我和澳国专家,分头讲授。这样,我国中断了33年的审计学的教学工作,就重新恢复了。培训班三期的学生150人左右,今天均在中央和地方的审计机构起骨干作用。随后,各大学审计学课程也先后恢复,我校成立了审计教研室,有的学校还成立了审计学系,审计学又成为会计系的必修课了。
会计学(包括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和审计学是会计学系的两门基础课,熟谙了这两门课程,其他各种专业课程只须花点时间熟悉它,不难迎刃而解。而如只熟悉专业会计而没有会计学和审计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就往往只懂得依样画葫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几年,我对我的研究生,就始终强调这一点。
五
会计科学的现代化中还有一个环节是簿记工作的现代化。1983年我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所至大学,几乎都引导我去参观他们的电算化设备,并几乎都以他们有这样一套设备为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使我深为没有能力向这方面进军自惭。今天,会计系的几位年青教师正在这方面加紧努力,会计系的电算教研室已成立,一位老师的会计电算化教材两年前已交出版社,即可出书。我相信,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会很快跟上的。今天,我校会计系正稳步地向会计科学的现代化迈进,除30年来以部门核算为主设立的四个教研室外,先后已新成立管理会计学、审计学、西方会计学、电脑会计学、企业财务学等以学科为主的教研室和一个会计史研究室,并有近二十位硕士研究生在任教,比起两三年前,面貌已大有不同。会计教学改革初步有了个框架,以后是逐步充实逐步提高的问题。
六
1983年秋起,我转入了正规的会计学硕士生的培养工作。由系里指派我主讲管理会计学和审计学两门课,每门一学期,轮换着讲。为了三个面向,我尽量采用国外最新出版的教材为教本,三年之中,管理会计学换了二次教本。最近一次的教材是C.T.Horngren的Cost Accounting:AManagerial Emphasis1982年第五版;审计学也换了两次教本,最近一次的教材是H·F·Stettler 的in Auditing Principles:A Systems-Based Approach第五版。1985年,一位教师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美国当年出版的著名的Montgomerys Auditing第10版,全文1400面,太厚,学校的复印机无法复印,只好割爱。三年之中换四次教材,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紧张。可是,却毕竟使会计研究生学到这门学科里比较新的知识。
七
有这样一句相当流行的话:教师是蜡烛,照亮了学生销蚀了自己,我却有点不同的感受。教师不是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也充实了自己、完善了自己么?蜡烛没有蜡,怎么照得亮人?古人说,教学相长,正是如此。教师们恐怕只能在自己所任的几门课上,以三个面向为己任,精进不懈,自己上去了,学生才能上得去。今天,学生思想活跃,是十分可喜的事,对一切新知识,学生近乎狂热,管理会计不必说了,审计学这样够“干巴巴”的东西,学生们照样学得津津有味,硕士论文以审计为题材的,甚至超过以管理会计为题材的,这与其说是教学方法上有什么“独到”之处,不如说是由于这些课程给了学生以新的东西。经济、政治的体制的改革,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靠的就是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新的东西。“新”得靠自己去猎取,猎取得有工具,而工具是外文。我打心底里希望我们的硕士研究生们,年青的教师们抓紧今天这个记忆力的黄金时代,抓紧外文,一门、二门、三门,多多益善,至少学会一门。不求全会,只求能看专业书。我从1958年以后,即未参加教学工作,1958年至1979年这漫长的22年中,钻的是“故纸堆”,会计学科连碰也没有碰。1980年后,我甚至仍希望继续钻我的“故纸堆”,而组织不同意,让我仍回到脱离已整整22年的教学岗位上来。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勉强跟着同志们一起教学,主要是得力于我这点并不高明的英语。今天讲三个面向,不免要注意西文,会点英语,自然沾光多了。
英语难学么?把Tracy的财务会计学24万言译成中文的一位老师,自称是“英语盲”,凭着他的毅力,很短一个时期,书就译出来了。翻译是很能提高人的,英语要达到能译原著的水平似乎也不难,所贵在持之以恒!如不会看原著的专业书,而想在会计这一技术性很强的学术领域对祖国做出较大贡献,就不容易。这一点,我有时也有点小小感受。比如,“社会审计”一词,在西方通行多年了,指的是对企业的社会效益、社会责任的审计,如污染、噪音、职工福利等,而我们不了解,用它来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民间审计(西方称“独立审计”),就不免引起国际性的混乱。又比如,用连锁替代法分析差异时的替代顺程问题,50年代初曾在我国引起争论,我当时曾提出一些观点和方法,今天普遍通行于西方名家的著作中,应该说,大体已有定论,但国内出版物至今仍有在50年代水平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就不免徒劳神思。又比如,世界各国的簿记方法按借贷分录,用阿拉伯数字记账,日前已逐步趋向统一。借贷,阿拉伯数字,和阳历一样,为各国所通用,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非抱住阴历,中国老式数码不放的理由,没有非用干支来纪年不可的理由,似乎也就没有非抱住收付记账、增减记账不放的理由(这不是说记账方法已尽善尽美,不必再研究了)。既然是科学技术上的问题,就要求我们放眼世界来看,要求其尽量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中国人民为增加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做出我们一代人的贡献,懂点外文,就将使我们的目光稍稍开拓点,气度阔大点。
八
22年的荒芜,我要完成今天的教学任务是很吃力的,这就要求我特别刻苦点。三年来,我在校内开课不足450小时,为了准备这450小时的课,估计花了十倍于此的时间。我确是战战兢兢、不敢丝毫放松、丝毫托大的。尽管我教书教到头白了,每次上课前,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总怕讲不好,就这样,还经常感到课没讲好。对老师来说,口齿和思路清晰,是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它们毕竟是载运工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载的什么。是老掉牙的?还是符合今天开拓的需要?如果凭仗口齿清晰,而不注意三个面向;或者,注意到了三个面向而不在备课上花功夫,我看,就难免跌跤了,孔夫子说:“执事敬”,又说:“事思敬”。作为一个教师,教书、育人,正是自己应“敬”的事。感到紧张,感到战战兢兢,也许合于“夫子之道”。
九
我是一个十分平常的知识分子,缺乏那种哲理的头脑,也缺乏把自己的“风貌”刻画出来的那种抽象思维能力。但是,和会计打了这些年的交道,似乎却从中浅薄地悟出些人生的道理。
我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人生究竟应该怎样来度过才算有价值?会计上,资不抵债要破产。我想,人们一生中,如果奉献不抵享受,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破了产的没有价值的人,一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一个人格上不高尚的人。这个想法使我经常会想起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们在“出”,“处”、“辞”、“受”四个字上那种十分严肃、守身如玉的功夫,并在这些问题上多少保持一点我并不总能做到的比较不苟的态度,对一些不该伸手的事我想过伸手,会使我感到羞耻,对某些场合上一些人不想捅出来的话,我有时会忍不住捅出来。一个人,当然最好能既是智者,又是仁者,但两者却往往不可得兼。在这种场合下,过分聪明的智者,似乎往往就很难同时又是道德上完整的仁者。这时,尽管我往往做不到,我总设法勉励我自己笨一点,把砝码放在不致使自己太无价值的这一边。对于我来说,今天有一个时间利用的优化问题。我得有些时间把一些大家希望我写的东西写出来,使我不致终于成为一个亏损户,而恰恰我又写得很慢,我似乎就不应再在闭门写作以外恋战了。正是,少壮不努力,老大乾着急。今天,我倒真有点感到急人。●
原载于《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