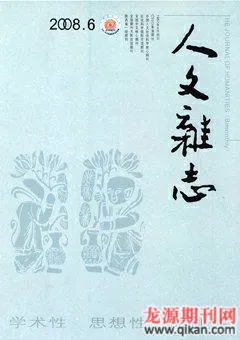对禅之理解及禅宗色彩观在文人画中的“自行呈现”
内容提要 1〉意为“止观”、“沉思”、“静虑”的“禅”是将主体浸入教理的活泼泼的直观性体验,它维持了“宗教”活的生命;2〉禅宗色彩观当是禅宗理论的自然衍生和凸现。庄禅一脉,不可两分。不是现象界的色彩不是知性语言,而是与诗性的描述性语言同质的“摹状词”意义的色彩(素淡-虚空之黑白)承担了本体论(庄子之“道”、禅性性“空”);3〉禅宗色彩观在文人画中“自行呈现”:中国封建后期士大夫阶层禅悦之风大盛,这时的文士画家心理应是儒、道、玄思想积淀经由禅宗综合起作用。深受禅之影响的文人画取代青绿成为画坛盟主是历史而宿命更是境界追求般选择了黑白之韵;4〉禅艺合流,禅以荒寒清冷为最高境,文人画即以“深情冷眼”的荒寒境为最高美学意境。
关键词 禅 禅宗色彩观(素淡–虚空之“黑白”) 文人画 意境
〔中图分类号〕J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6-0118-07
一、对禅之理解及禅宗理论要点阐释
禅,译自梵文dhyāna (“禅那”),意为“止观”、“沉思”、“静虑”。禅,起源于古代印度的修炼方法瑜伽。“瑜伽”是梵文Yoga的音译,主要指通过苦行、克制与沉思冥想,脱离对肉体及一切感觉现象的依恋,达到主客合一、灵魂解脱之快乐澄明之境界。瑜伽修炼通常分为八个阶段,其后三个阶段属于精神修炼,即“执持”(梵文Dharna,指观念、意图、信仰、专注)、“禅”(dhyāna)、“定”(梵文Samadhi,音译为三摩地或三昧,指冥想、恍惚、出神、入定)——“禅”即处于“执持”和“定”之间的中间阶段。瑜伽是印度所有本土宗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共同采用的修炼方法,相传耆那教祖师大雄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都是通过瑜伽禅定悟道的。于是知佛教诸宗都有禅观。进一步言,作为佛教戒(梵文Sila,悉罗,戒律)、定(梵文前述,三昧,禅定)、慧(梵文Prajna,般若,智慧)三学之定学,“禅”是将主体浸入教理的活泼泼的直观性体验,它维持了“宗教”活的生命。(注:参阅王镛《禅思与诗境——禅宗思想对中国诗画的渗透》,《书画艺术与文学——二00五两岸当代学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艺术大学,2005年版;
参阅尤西林:《禅与现代人的主体性的问题》,《文化:中国与世界》(4),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版;参阅巫白慧:《印度哲学》,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参阅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
然而佛教诸宗虽都有禅观,但把“禅”置于本体地位(即演变为人生哲理而当作境界与心灵归宿的)却是禅宗。(注:参阅尤西林:《禅与现代人的主体性的问题》,《文化:中国与世界》(4),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版。)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的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即指除浩浩佛教经典之教义外,还有“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传到菩提达摩,据说已是第二十八代。据佛教传说,达摩于南北朝梁武帝时到中国((约520—526年),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注: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印顺:《中国禅宗史》,上海书画出版,1992年。 )其后传惠可、僧璨、道信、弘忍,弘忍之后分化为南北二宗。北宗领袖神秀,强调经教,力主渐修,晚唐之后,日趋衰落。南宗领袖慧能,强调顿悟,力主自性自悟,实行了一系列变革(“六祖革命”)。慧能实际上是禅宗的真正创始人,禅宗主流,即是沿慧能的路线发展的。禅宗是道庄化的佛学,冯友兰先生即指出:“佛教的中道宗(按:即空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注: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与道家哲学相通,禅宗亦尚“空”观:佛性性“空”,因而慧能以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注:《坛经•八》)来与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注:《坛经•六》)相对。与“空”对立的是“执”(生死、病痛、金钱、权势以及耽迷义学经文和干枯静寂的禅坐,都是“执”)。破“执”之矛是“无”,禅宗遂提“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注:《坛经•十七》)。“无”所集中破除的是“文字相”和“佛祖相”之“执”,从而使“不立文字”和“自性”成为禅宗革命的两面旗帜。(注:参阅尤西林:《禅与现代人的主体性的问题》,《文化:中国与世界》(4),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版。)
禅宗的“不立文字”(“第一义”不可说)比道家、玄学所讲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大大推进了一步。于是禅宗的语言常常不合日常逻辑,若问“究竟甚么是禅?”,禅师答:“庭前柏树子”(赵州)、“西来无意”(大梅)、“一个棺材,两个死汉”(马祖) ……若问“如何是佛?”禅师答:“干屎橛”(云门)“麻三斤”(洞山)(注:参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这种“一棒打回去”的棒喝是在提醒得禅的方法在于去蔽中的自悟,是回到本心的直观体悟:本体自现,即心即佛,顿悟自性,如“哑子饮水,冷暖自知。”(注:《坛经•一》 )
然而禅宗之“空”、“无”并不是脱离现象的彻底抽象,《坛经》体认:“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注:《坛经•二四》)因此“空”观同主客割裂、外在观照的认识论相对。空观即是禅悟境界,“是如击鼓也,其外之声未可摄也,然取其鼓,或取击鼓者,则其声得矣。”(注:《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页。)击鼓得声非执著于鼓,以手指月并非手即月亮,因此禅境“空”观需内在直观地体悟,化认识主体为佛性本体。因而禅宗立“无念为宗”时,亦强调“于一切境上不染”,“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B14(注:《坛经》)这就是禅宗“出没即两边”,“于相而离相”,“于念而无念”,“于空而离空”之精髓和诀窍。 不为外物所缚,不为利害得失而计较苦恼,“无所住心”而得精神的大解放大自由。“出没即两边”,不断“思”与“情”,于是禅宗在“即心即佛”、“顿悟见性”之外即强调“解脱不离世间”,而以“平常心是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B16
(注:《景德传灯录》卷六),“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注:《传灯录》卷八 ),参禅即可在孤峰顶上,亦可在红尘浪里。“一切声色事务,过而不留,通而不滞,随缘自在,到处理成。” (注:《无门关》 )
“无所住心”并不是“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