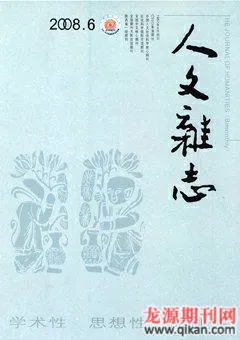美国中国学中的西方中心范式
内容提要 就整个美国的中国研究来讲,西方中心是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范式。从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可以看出,西方中心范式的内涵包括:西方历史经验的普适化;以西方经验,或是以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思考、解释、评判、预测、规范中国社会;西方中心范式的学理渊源主要的就是近代以来以赫尔德、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现代化思想。
关键词 美国中国学 西方中心范式 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6-0049-09
就整个美国的中国研究来讲,西方中心是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范式。早在传教士汉学时期,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认识便带有了西方中心的色彩。张铠在总结早期美国中国研究时指出:以“欧洲中心论”为出发点,对华夏文明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就是其一大特征。
(注:张铠:《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奠基》(殖民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20世纪30年代,皮克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可以说是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中运用西方中心范式的先河。40年代之后,费正清在创建美国现代中国学过程中,不仅将西方中心范式运用于研究实践,而且在实际中创造了“冲击——回应”研究模式。50、60年代,列文森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儒教的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则将西方中心范式进一步加以发展,开创了西方中心范式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传统——近代”研究模式。80年代以后,虽然美国现代中国学中出现了范式多元化的特点和趋势,但是西方中心范式并没有消解。一方面有学者继续运用这一范式研究中国,另一方面西方中心范式也在这一时期被推向了极端,从而使“冷战”思维范式得以大行其道。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学界中存在的三种中国研究的模式,即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模式。柯文认为,这三种模式在本质上都是西方中心的,并且都存在严重缺陷。“这三种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冲击——回应框架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就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做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近代化或“传统——近代”取向的错误,“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同时也是狭隘的——西方观点,即关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界说,强加在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取向“也有若干弱点,易遭攻击。有时它陷入了非历史的困境,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种‘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道路,可是这种道路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但有时它又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因此迫切需要来自外界的一次震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此一取向的人变得不知究竟应如何解释西方的作用”。(注: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3-4页。)柯文主要分析的是上述三种模式及其缺陷,并进而提出他自己关于中国研究的新模式——中国中心观。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西方中心范式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发展观,及其方法论观念,同时也未能揭示西方中心范式的学理渊源。因此,本文主要以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为例,分析美国现代中国学中西方中心范式的上述方面。
一、西方中心范式的内涵
从历史观、发展观方面来讲,西方中心范式主要是指将西方历史经验——特别是近代的——普适化;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它体现为以西方经验来预设、评判、甚至是规范中国历史发展,这往往又直接体现为:在实际研究中以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来解释和评价中国。
(一)西方历史经验的普适化。
西方中心范式在历史观、发展观方面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西方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具有普适性意义。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观念,是与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有着密切关系。
从欧洲近代历程可以看出,近代欧洲一方面是其崛起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其对外扩张的过程。欧洲的崛起及其向外扩张既向其他非西方国家输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通过对比,既在西方人思想中也在其非西方人的思想中形成了西方先进,非西方落后的观念。于是,西方近代历史经验的普适化就通过西方对外扩张的结果得到“验证”。这样,就形成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将是整个世界发展轨道的观念。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说:“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③
(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7、29-30页。)“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
自16世纪起,西欧开始全面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精英的推动和鼓动下,民族——国家理念逐渐成为西欧族际政治思想的主流。“国民——国家现象被理论化和神圣化”(注:王建娥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5-276页。)。这就意味着,在政治、社会等领域,随着近代欧洲民主政治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的兴起,三者之间以及它们与经济工业化、启蒙思潮之间的互动,在人们的意识中,就将民族国家发展模式、民族主义是世界其他非西方地区发展的模式加以固定化了。
(二)以西方经验,或者是以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思考、解释、评判、预测、规范中国社会。
这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以西方经验作为标准来思考、衡量近代中国;二是从理论前提出发,以理论解释、评判、预测、规范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这两方面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的。在这样思维理路的指引下,人们在接触中国过程中,不仅强调中国落后于西方,而且开始追问中国落后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等问题。
第一,何谓现代化,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西方中心范式中,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他们在考察中国时,往往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理论来分析中国。这一点,在民族主义研究中,最早以卡尔斯•皮克等为代表。皮克在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在考量近代中国的教育与民族主义问题时,他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之间是何种关系。在他的研究中,皮克所要强调的就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他所说的教育、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很显然就是西方近代的教育、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皮克认为,“它强调的是对于政治国家的忠诚”②(注: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New York: Howard F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