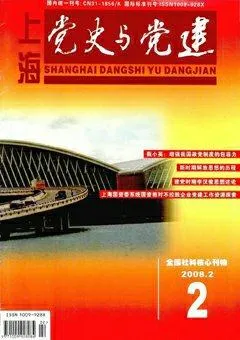迈开上海郊区改革第一步
口述:李学广
采访:吴振兴、张永斌
时间:2006年4月17日和5月16日
整理:张永斌
李学广,1977年11月至1981年10月,任上海郊区嘉定县委书记兼县长(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展开。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的郊区,该如何根据自身特点,采取切实可行路径找到工作的突破口?嘉定县率先在郊区进行了承包制和农工商一体化等方面的探索,迈开了郊区改革的第一步。我们就此话题对李学广同志进行了采访。
嘉定是上海市近郊,改革开放初期有50万人口,19个乡镇。我是1977年11月到嘉定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的,1981年10月离任。
当时,农村、农业向何处去,改革如何搞,思想非常活跃,但阻力比较大。因为“文革”10年,思路都乱了。嘉定大胆尝试,搞了两项比较大的改革,即建立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在探索后一项改革中,又把双季稻改为单季稻。这些举措,体现了嘉定敢闯敢试的勇气,今天想起来,仍觉得意味深长。
郊区首行责任制
农业责任制的探索,发源于广大农民从切身利益出发,对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大呼隆”消极现象的反思。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农村中广泛盛行的“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带来严重的后果。主要有六种表现:一是大呼隆、磨洋工。二是劳动计量不计质。三是农业劳动的主力是“三八六一部队”(即妇女和儿童)。四是干群关系不融洽,群众理想很模糊。五是饲养场普遍亏损,饲养员的报酬要在农业上开支。六是空壳队、不合理透支户多。
面对这些,我睡不着觉。农民的日子怎么过?社会主义的出路何在?我思之再三,答案只有一个:唯有改革,才是光明大道。对于是否搞责任制,如何搞,领导层有几种看法:有的认为不能改革,觉得责任制就是分散劳动,分散劳动就是单干,而单干就不是集体化,不集体化,还能叫社会主义吗?只有维持现状,才是社会主义。有的认为不改不行了,关键是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本没有调动起来。
经过争论后,嘉定在上海郊区10个县中最早进行了责任制探索。改革的步骤是先副业,后农业;农业上是先经济作物,后粮食作物;粮食作物上先包产到组,后联产到劳,再包干到户,专业承包,由点到面,逐步展开。
最初,在养猪场获得了突破。当时,全县养猪场普遍亏本,饲养员的报酬靠农业收入补贴,副业吃农业的“大锅饭”。1978年初,马陆公社北营大队饲养场搞了承包,对饲养员实行定人、定饲料、定饲养量、定产仔率、定报酬、超产奖励的“五定一奖”责任制。饲养员何小弟和2名副手中标。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承包者3人住进了饲养场,以场为家,尽心尽力,使连年亏损的饲养场一举转亏为盈,年底一算帐,3个饲养员除应得的报酬外,还可得120元奖金,其中何小弟应得80元,两名副手各应得20元。何小弟一时还不敢多拿,因为以前都是平均分配的。这时,有些讽言讽语也传开了,有人说当初的标准订得太低了;也有人说,一个人拿这么多奖金,不是两极分化吗?由此,我们在全公社、全县开展了一场“何小弟这80元奖金该不该得”的大讨论,讨论场面活跃而热烈,一扫以往的沉闷气氛。思想越讨论越解放。《解放日报》专门报道了这场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大意是:嘉定县这场讨论,其意义已超出讨论本身,像一声春雷,扫去了10年“文革”那种“大批判”、“打倒一切”的沉闷空气,给农村大地带来了欣欣向荣的和煦春风。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指出,这场讨论更是一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经验。这场讨论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极大震动,要求改变“大呼隆”“大锅饭”的愿望更加强烈了。随着何小第奖金的兑现,全县所有养猪场都实行了“五定一奖”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年,2000多个生产队、大队养猪场由原来亏本161万元,一跃变为盈利710万元,扭转了亏损的严重局面。
农业种植业从饲养业责任制的成功探索中得到有益启发。我们对种植业的改革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包产到组。全县最早实行包产到组的是嘉西公社皇庆大队第三生产队。1978年,经社员大会讨论,将全队劳动力划分为5个常年固定的作业组,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责任制。年终结算时,组组超产,家家得奖。1979年春又加上包工和包本措施,以产值计酬,取得了增收、降本的效果,全队净收入比上年增长11%,人均集体分配由上年的278元增加到360元,增长29.5%。第二步是试行家庭式联产到劳责任制。1980年秋,封浜公社的朱家村生产队,曹王公社的张北等5个生产队突破包产到组,实行家庭式联产到劳责任制,按户、按劳动力承包。我们坚持面向实际,让事实说话,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县机关和各公社、镇的领导干部,分成几个组,深入到这5个生产队去实地调查研究,最后终于在事实的基础上统一了认识。到当年秋天播种时,全面实行联产到劳承包制的生产队从5个发展到785个。第三步是“双包干”到户。1981年秋播时,嘉西公社胜利大队杨家生产队创造了取消工分制、实行粮食和经济作物“双包干”到户的方法。这种形式因其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82年底,全县实行“双包干”取消工分制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90%以上。
嘉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包产到组,联产到劳再到包干到户三个阶段的发展,做到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劳动报酬与最终产品相联系,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个人的积极性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嘉定县作为上海郊区10个县中的首富县,在郊区实行责任制最早,普及面也最广,成效显著,到1982年底,全县农、副、工三业总产值比1976年翻了一番还多,农村集体分配收入人均达到436元,比1976年增长1.16倍。
直到1982年12月,市委在莘庄召开郊区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取消于1980年11月提出的“三不”禁令(即本市郊区不准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不分口粮田,简称“三不”)。会议要求郊区从实际出发,主要总结推广“统一经营、包干分配”的责任制形式。会议以后不到半年时间,郊区有95.4%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户为105.4万户,土地面积为321.9万亩。
探索农工商一体化
嘉定经济尽管在上海郊区是名列前茅的,但发展中遇到一个深层次的严重阻碍,就是农工商割裂。其弊端主要有:一是影响农业现代化资金积累。二是由于农工商经济割裂,农村商业流通渠道狭窄,“官商”作风严重,服务质量下降,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三是影响了农副业生产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四是由于工农商割裂,造成了很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浪费。
要改变农工商割裂的现状,必须实行农工商一体化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对于如何搞农工商“一条龙”,当时有很多议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还有怀疑的。这种现象是件好事,说明大家都在思考。嘉定农工商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纵向的生产、加工、销售,简称产加销“一条龙”,即狭义的农工商联合经营;另一方面是广义的在农村基层经济组织中即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除搞农业外,同时兴办工业企业、经营商业,实行横向的农工商综合经营。
嘉定县是在1978年9月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农工商联合企业试点单位的,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探索:
首先,调整了作物布局和耕作制度,理顺经济结构,创造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良好环境。众所周知,在“以粮为纲”方针指导下,农村经济生产中出现了“全面砍光”的畸形格局。为了保住粮食的年年增产,在耕作制度上改变了原来的用地—养地相结合的麦—稻—绿肥轮作制,变为麦—稻(单季稻)—稻(后季稻)纯粮三熟制。这种100%的粮食三熟制,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大幅度增产粮食的掠夺性效果,但却违反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竭泽而渔”,造成严重后果。一是不符合江南鱼米之乡用地养地规律,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在成本大量增加的同时,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采用双季稻后,农民更穷了。二是这种制度促使农村经济从多种经营向单一经济退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三是劳动力被束缚,劳动生产率下降。实行三熟制后,人的绝对劳动时间在增加。据统计,1976年与1966年相比,若按出勤的劳动天数计算,人均报酬下降16.2%。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劳动力愈发紧张,出现农忙时社队工业要停工的现象。
为了组织农工商综合经营,1978年、1979年,率先落实归还农民的自留地;接着,恢复黄豆、大蒜、黄草等经济作物面积;同时,逐步减少双季稻面积,1978年把双季稻由100%减到80%,1979年减至70%,1980年减至63.3%,1981年减至34.2%,就在这一年10月,我被调离了嘉定县。后来得知,到1985年双季稻降为1.5%了。另外,发展蘑菇、香菇、湖羊、水貂、蚌珍珠等多种经营。但改革仍然是走小步的。
第二,面向市场,组织了商品率高、商品量大如大蒜、食用菌等经济植物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1979年先在城东公社试办了蘑菇的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小龙”,一经组织,成效就出来了,农民增收28万多元,增长28.5%。同时,马陆公社以香菇为主的“一条龙”规模更大,以香菇大楼为中心,办起了菌种场、切片厂、烘干车间,以及小包装、样品陈列、洽谈接待,还有科研小组、技术指导等系列化生产经营,吸引了中外客商,参观者、洽谈者门庭若市。“一条龙”的成功,引起了全县各个生产蘑菇、香菇单位的兴趣,纷纷要求联合起来,纵向联合已是“水到渠成”。于是,1980年5月,成立了全县性的大蒜、食用菌联合公司。参加的有1400多个生产大蒜的生产队,1600多个生产食用菌的生产单位和菌种场,还有4家社队办的大蒜、食用菌加工厂。联合公司成立了董事会,制定了章程,规定工、商利润的50%返回原料生产单位。到9月下旬,大蒜食用菌公司已返回生产单位利润12.35万元。
我们还组织了手工艺品的产供销“一条龙”,主要是刺绣的花样设计、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人数最多时发展到6000多人。还在嘉定联合企业中成立了手工艺品公司,统筹全县手工艺品的生产、设计、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业务。
第三,在组织纵向“一条龙”的同时,着手组织横向的农工商综合体。综合体的核心部分是办工业。联合企业最先联办的是为大工业、为出口、为人民生活服务的“三为”工业。这种跨地区、跨单位、跨所有制的合作,加快了产品结构调整,使分散的生产能力成为实力雄厚的企业。工农联营也兴起了,因为它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另外,我们尝试把地域性的生产单位组成农工商综合经营,这是广义的联合企业,全县成立了“嘉定农工商联合企业”,马陆和曹王两个公社各自成立了“农工商联合企业”。我们还进行跨省市联合经营办厂,例如与福建省合办家具厂,对方进行粗加工,嘉定再作精加工并销售。利润分成为闽六沪四,取得了互联双赢的效果。由国务院外交部联系,支援了南斯拉夫生产食用菌项目。又经上海外事办介绍,与日本大阪结为友好交流单位。
我们的探索得到了许多关注和支持。1980年元旦刚过,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到嘉定考察,对我们的改革表示支持。经过2年的试验,1980年9月,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肯定下,嘉定县农工商联合企业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上海郊区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联合企业。一经挂牌,嘉定试办农工商的影响就扩大了,中国农经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于当年10月在嘉定召开了全国农工商一体化学术讨论会,经过8天的热烈讨论,一致肯定了
嘉定的试点。会上我受邀作了题为《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发言。
我的两点思考
一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每位领导者都必须经常思考的大问题。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左”的教条主义盛行,片面地从变更生产关系的角度,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长期未能踏上比较切实的轨道。嘉定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之时,在上海并无先例。我们的成功就在于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解放思想,面向实际,胸怀未来,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二是关于创新与求实的关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本应是每位领导者在开展具体工作时的必然要求,但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尤其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发生了“上海不为天下先”,还是“上海敢为天下先”之间的搏弈。嘉定探索农业联产承包制之际,就曾遇到阻力,说上海存在“三高”现象,即复种指数高、机械化程度高、生产水平高,不适宜搞承包。但实践下来,“三高”与责任制并不矛盾。应该说,“三高”所要求的责任制,一定是能够体现“三高”特色的责任制,而非简单照搬一般地区的经验模式所能行得通的。如果无路就止步,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就只好原地踏步,最终只能是毫无出路。在提倡“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的今天,允许脚踏实地,大胆尝试,营造创新氛围,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