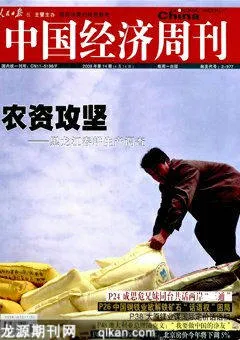首份《中国基金持有人调查报告》发布 学生成为基民主力之一
1998年3月,中国基金诞生;2008年3月,它完成了发展道路上第一个十年。从最初的5家基金公司,5家托管银行发展到今天60家公司,12家托管银行,81家代销机构,资产规模已超过了3.2万亿元。最初的“富人游戏”已经发展成今天传说中的“1亿基民”。
3月21日,“第三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调研作出的首份《中国基金持有人调查报告》同时发布。《报告》显示,目前学生身份的基金投资者占总基民比例高达13%,仅次于公司普通职员(30%)和管理人员(17%)。
报告执笔人、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主任杜书明博士说:“这让我们颇感意外,说明基金热也波及到了大专院校。”
“家长投资”
网易基金吧里有一个关于80后基民的调查,调查显示,一大部分学生基民的投资来源是家长的不菲赞助。比如20岁的Rose,妈妈是职业经理人,给她拿100万去炒基金,2年不到全赔了,她准备先瞒着家里借钱再战;一位87年出生的网友已经是上海的“小地主”,“06年买了80万股票,现在还是80万。中间用挣来的钱买了套160平方米的房子,在乡下买了块1000平方米的地,房地产总值130万”;还有比较普遍的,“从04年开始炒基金,老爸最开始玩的,后来我看他技术不行就换我了,现在他买基金我炒股,赚了一些,反正没赔过本,家里人就对我没意见。”
对于正在渐成气候的学生基民,中国建设银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马梅琴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学生如果具备了以成人思维来思考问题的能力,投资基金当然是可以的。我儿子也在炒,他学的是经济,我就给他开了一个户让他尝试着买一下。因为他关注这个市场,就会关注市场的背景: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法规等等。”
“但要是把家里的钱都去给他买基金,出现损失的话他也会坐不住,肯定影响学习,所以要给他定个纪律:投资的金额控制在就算都赔了也不会影响到全家生活的基础上。我认为对于基金来说,不管亏跌都是一个长期的投资,不能让他天天都为此胆战心惊。”马梅琴说。
“没钱才‘养基’”
大多数人认为,对于这些还在上学的基民来说,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太多心理负担,“玩”的是父母的钱,“就当练练手”。
但学生基民周遥(化名)的经历却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富二代”,父母只是农民,并不懂基金,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养基”的理由也很简单——赚生活费。
25岁的周遥目前就读哈工大物理电子学系研一,2006年开始养“基”。算学校中小有名气的“基神”,很多同学随他入市。
他说,入市那会儿正是牛市。有笑话说“一个老太太烧纸钱,边烧边说,收到了都拿去买基金吧”然而,飙升过后,去年秋天到今年年初,市场一片萧索。经历了几番历练,周遥觉得“自己长大了。”
从最初投4000元买基金,到现在净赚2万,他称自己“只是小赚一点生活费而已放银行也是别人用你的钱,干嘛自己不用呢。就算赔了不也就2—3万吗?你说呢?”
学生基民和所有基民一样,忌讳“赔”字。在别的同学选择打网游或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奔波于教室和电脑之间,花2—3个小时上网浏览新浪、搜狐以及晨星网等新出炉的基金测评,从亲戚朋友那里学习经验。
周遥对于基金的知识大多来自互联网,“开始我也是一无所知,浏览和过滤信息的能力是这几年才培养起来的。”现在,周遥每天吃过午饭还会到报摊买份《中国证券报》,学习分析金融市场的动向。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时间,学生的主业毕竟还是学习。”
投资过激是最大风险
事实上,学生基民和中国近80%的基民成长曲线完全吻合:牛市入市,大部分在去年加入养“基”。他们“基”龄相仿,共性很多。
在首份《基金持有人调查报告》中,低收入者(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群比例接近10%。报告指出,这说明基金投资热已经波及到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人群,这将有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
周遥也认为,学生基民最怕投资过激:“投入的资金要对你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千万不要全部投入去搏。”
但在学生中急于暴富的人不在少数,一位炒股一年赚了8000元的英语系大四学生马岩说,毕业后他打算专职做股票投资,现在也在带人炒,“我不买基金!买基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