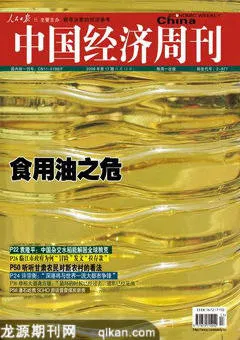农民缘何对“新农村”水土不服

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却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了”。
建设自己的家,按理说农民最有发言权,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如果这个主体难以发出声音,导致的后果就是,由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设计的新农村并不对农民的“胃口”。
因为在新建的“新农居”水泥砖房里住不惯,苏树海又从刚刚搬进去住了没多久的房子里搬了出来,“还是土房子住着舒坦”,今年57岁的苏树海这样告诉记者。
苏树海是甘肃省庄浪县南坪乡苏湾树四社的农民。听说搞新农村建设,去年该乡在村里最好的一块地上建起了一排排整体的水泥房。刚开始,许多村民跃跃欲试都想住进这个所谓的“新农居”,但后来听说住这样一栋“楼房”要交6万块钱,一些农民就打消了想法,最终住进去的是村里那些“有钱人”,苏树海就是其中一员。
据了解,和苏树海一同住进去的农民不少都有类似的想法。“不仅仅是习惯问题,而且房子太小,几代人住在一起转不过身。农具也没地方放,更为重要的是巴掌大的一点牲舍,让给牛,猪就没地方去;让给猪,鸡又无处藏。很不方便”。一位村民这样告诉记者。
“很不方便”,是农民们对新农居的最大感受。
《中国经济周刊》还了解到,农民对新农村“水土不服”,不仅表现在住房,而且在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方面,“一刀切式”的做法,也在伤害着他们的合理诉求。在一些西部偏远农村,在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指导的思路下,政府的好心和农民的想法正在发生激烈的碰撞。
新农居工程,农民“不服水土”
近一阶段,各地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盖新楼房的举措接踵而至,一时掀起了建新楼房的热浪。试点村建楼房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种示范典型,许多地方政府对试点村的规划纷纷效仿,只要走在农村的公路两旁,甚至在高山上都可以看见拔地而起的楼房或小别墅。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将新农村理解为统一规划盖新房或住楼房。在甘肃天水,一位农民这样告诉记者,本来今年计划翻盖新房,但听说村里农民自己建房都不批了,原因是国家正在搞新农村建设,县乡要在村里建设集体新农居,因此自建房的计划就搁置了。
采访发现,很多地方领导对当地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也都是从建楼房开始。苏树海告诉记者,并不是农民们顽固不化,谁都想住得好一点,但真的不符合农民的生活习惯。他说:“下地干活回来,一身土一脚泥的,踩在雪白的瓷砖地上,一脚一个印子,随时都要擦地,很难伺候。是人住房子,还是房子住人呢?”不仅如此,因为土坯房子有冬暖夏凉的特点,住惯了土坯房子的农民普遍觉得,住在水泥砖房里要比原来感觉还冷,尤其是在冬天。
如果仅是个习惯问题,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还能凑合”。村民席彩菊告诉记者:“由于房子少,只能和公公婆婆同住一室,生活很不方便”。在西北农村,三代同堂或者四代同堂住的大家庭很普遍。他们不象城里人,一旦成家就与父母分开住。为了照顾长辈,他们常常住在一起,新农居就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甘肃民勤县西渠镇的煌辉村,地处青土湖边缘,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大部分农户都迁居异乡,只剩下121户。去年以来,围绕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民勤县确定将剩余的农户全部迁到境内蔡旗乡农场,建立新农村示范点,村民张兆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他至今还清楚的记得搬迁前,温家宝总理来到他家,盘腿坐在炕上和他拉家常时,他告诉总理:“盖房子给补助,大小五间砖房,比我现在这个家好多了。”但他没想到的是人和家畜要争住处,“由于院子小,搭个草棚的地方都没有,农具只能露天放置,集中供水点经常停水”。据了解,由于集中居住,相关的配套设施跟不上,新居工程给已经入住的农民带来极大的不便,使本来准备入住的农民又打起了退堂鼓。
建设新农村,一方是热情高涨,建设正酣;另一方则是不停的抱怨甚至拒绝。
本来,住新楼房,改善居住环境对农民来说是一件好事,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是普遍表示欢迎和拥护的,但这样一件有利于农民的好事,缘何得不到他们的理解?用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农民也有自己的希望和要求”。
除了居住习惯和面积小之外,农民也有一个对于房屋、院落的需求上的不同偏好。农民对于农村住宅,在宅基地地段、房屋大小高低、门朝哪个方向开、选购什么材料等,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不象城市居民只能被动地听从开发商摆布和宰割。
有一个自然村搞旧村改造,仅拆迁和村庄美化,就要农民每人集资几百元,还不包括农户家庭的改水、改厕,建沼气池的费用。另外一个自然旧村整治,政府只拿出很少资金,农民每户则要拿出一定资金,造成了新的农民负担。目前的这些试点村,一旦成为样板在面上推开,农民的负担就会加重。
兰州大学研究员申培德这样告诉记者:“目前的新农村建设试点都是在政府和工作队强有力推动下进行的。基层尽管知道中央要求不搞大拆大建,但在试点中总要搞出样板来,特别是有些地方搞自然村撤并规划,迈的步子就更大。如有个行政村50多个自然村庄,合并为一个中心村和10多个基层村,农民感到难以接受。新建的一个中心村,仅土建和上下水政府就花掉200多万元。进入中心村的农民一户建房最少要7至8万元,一般农民户搞不起,也无法进入中心村。”调查表明,这种做法,只有1/3的农民赞成。
富民工程,难讨百姓欢心
时值暮春时节,在甘肃东部山区,应该是小麦拔节灌浆的大好时节,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在甘肃清水县一些乡镇,本来麦浪滚滚的良田却生长出一株株树苗。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是当地政府为老百姓办的一件大事。
据了解,早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