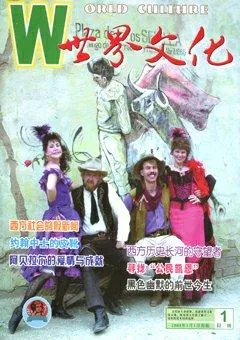阿贝拉尔的爱情与成就
“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阿贝拉尔)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从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戈夫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阿贝拉尔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阿贝拉尔出生于1079年,逝世于1142年,是中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中世纪盛期文艺复兴的主将,经院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巴黎大学的创始人。他的墓志铭上这样写着“高卢的苏格拉底”、“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精细的、敏锐的天才”。
然而他的永垂千古不仅在于他在哲学上的成就(激进的思想)和创立了巴黎大学,还在于他凄美的爱情。在本文中将先介绍他被人们忽视了的凄美的爱情,然后再介绍他的成就。
凄美的爱情
大约1114年,刚刚三十五六岁的阿贝拉尔便达到了声望的顶点,他不仅以辩证法著称且在神学方面也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遇见了使他生命发生转折的一位女性——爱洛伊斯,一位年轻漂亮且又有学识的姑娘。爱洛伊斯在其叔父的栽培下,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拉丁文著作,而且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这在那个世纪里难能可贵,于是17岁的她便成为当时巴黎有名的才女,无怪乎阿贝拉尔对其一见钟情,并想尽办法通过其叔父当上了她的家庭老师。
一个是年轻漂亮,一个是才华横溢,于是,阿贝拉尔和爱洛伊斯在授课的过程中相爱了。他们借着上课的机会,感情与日俱增,直到难分难舍。阿贝拉尔在晚年写的《受难史》中这样写道:
“由共居一府邸发展为两颗心合二为一。整个授课时间我们都在卿卿我我,耳鬓厮磨,不过,每当我们渴望一个僻静的角落时,我们只需埋头书本便足够了。书总是翻开摆在那里的,只有爱情成为优先话题时,提问与解答才十分热烈。相互的亲吻多于箴言的解释,我的手往往不是放在书上,而是伸向她的胸脯。我们不看书本,只是相互凝视对方的眸子。我们贪婪享受爱的各个阶段,挖空心思变换着花样丰富着我们的爱。在此以前,我们从未品尝过这种欢乐,这时却怀着烈火般的倾慕和激情不知厌足的享受它,从不感到厌倦。”
在这期间,阿贝拉尔无暇于他所热衷的教学与学术,灵感萌发时写下的不是哲学的秘密,而是爱情的诗篇,哲学家变成了诗人,他的情诗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可是在那个基督教主导一切的时代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爱情,更何况阿贝拉尔还是一位低级修士,一位著名的学者。很快他们的恋情被爱洛伊斯的叔父得知,他暴怒地把阿贝拉尔从自己家中赶走,并勒令他们不再见面。但是短暂分离反而增加了他们彼此的感情,于是他们频繁的偷偷约会。最后,爱洛伊斯怀孕了。阿贝拉尔偷偷的把她装扮成修女,送回他自己的家中,在那里,爱洛伊斯产下一男孩。
在那个时代,按照教会法,阿贝拉尔这样的低级修士可以结婚,但这会给他的教师职位和学术生涯带来消极影响。博学的爱洛伊斯要的是纯洁的爱情,她不愿意给阿贝拉尔的事业带来影响,想一想也便可知,一个哲学家不可能同样细心的关心妻子和哲学,在学生和保姆之间,书桌和摇篮之间,书本和女红之间,笔和纺锤之间,如何能做到和谐?她不愿意和他结婚,她宁愿做一个情人。但阿贝拉尔坚持己见,婚姻还是秘密缔结了,双方决定保持不公开,这样不会影响阿贝拉尔的事业。但爱洛伊斯的叔父却散布他们的婚姻消息,阿贝拉尔迫不得已又把爱洛伊斯送回修道院。爱洛伊斯的家人误以为他欺骗了他们,在狂怒之下,其叔父派人闯进阿贝拉尔的房间,阉割了他。从此,这对相爱的恋人双双遁入修道院,那一年,阿贝拉尔不足40岁,爱洛伊斯大约19岁。
修道院的生活是单调且乏味的,虽然爱洛伊斯最后升为修道院院长,但她对阿贝拉尔的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她一直担心着他的身体、他的事业。每天期盼着他的来信,期望他给自己以指导。 她对阿贝拉尔的爱丝毫没有减少,在给他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共同度过的每一段时光、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连同你的影子都深深铭记在我的心里,每每重温则仿佛昨日重现。”
“就我而言,我们的恋情带给我极大的快乐和甜蜜——这种甜蜜的感觉总是让我感到愉悦,一直萦绕于我的脑中。不论我走到哪里,这种感觉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带给我苏醒的渴望和幻觉,令我无法入睡.。”
对于阿贝拉尔来说,他毕生以孤独和寂寞把自己献给了真理;他是一个斗士,渴望荣誉和权力。尽管和爱洛伊斯的爱情受挫,并惨遭厄运,但他的斗志并没熄灭,他把他们的苦难当成主的特意安排。1120年,他在香蒲又开了一所学校,恢复了以往的名誉。
他没有遗忘爱洛伊斯,并时刻关注着她,在爱洛伊斯和其他修女被从阿让特伊修道院驱散的时候,他把他创立的圣灵修道院及其附属财产无偿赠给了她们。应爱洛伊斯的要求,他给她们写了大量的指导信件,为她们制定教规,提供指导意见;为她们撰写了大量赞美诗,传至今日的有133首。此外,他为圣灵修道院写了34段布道词,对修女们提出的问题予以详细而耐心的解答。他们通过信件来彼此鼓励,来发展共同的信仰——对上帝的爱。
爱,并未随着阿贝拉尔的苦难而终结,而是持续到两个生命的终结。这对尘世间的至爱在身后永远结合在一起。1142年阿贝拉尔在圣马塞尔修道院去世,后来遗体归还圣灵修道院。1163或1164年,爱洛伊斯去世,被埋葬在阿贝拉尔身边。他们的遗骸后来多次迁移,19世纪最终迁至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直至今日。如若他们地下有知,应当会感到欣慰的。
激进的思想
1100年,20岁的阿贝拉尔第一次来到巴黎,此时巴黎有一个少有的知识分子团体 “哥利亚德”,他们表达情爱的诗歌在市民中广泛流传。对“哥利亚德”来说,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而阿贝拉尔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最初受到孔比耶尼的洛色林的影响,洛色林是唯名论创始人,他奠定了阿贝拉尔批判唯名论的思想基础。然后在巴黎圣母院教堂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师从香蒲的威廉,这是一位在逻辑学方面声名显赫的巴黎著名教师,但是在听了香蒲的威廉一段讲课后,他很快与老师分道扬镳,并开始攻击其言论,最后老师的学生全都离开了,这位老教师受到打击,放弃了授课。阿贝拉尔凯旋,并且正好是在他的老对手退隐的地方——圣热内维耶伏山开业授徒。巴黎文化的中心从此永远不再是在城区的小岛上,而是在圣热内维耶伏山,在塞纳河的左岸:一个人就这样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命运。然而这只是他接二连三的与那个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绝交的开始,从此他作为他老师的对手而存在。
从1113年起,阿贝拉尔师从拉昂的安塞尔姆研究神学,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对老师失去了尊重:“我接触了这位老人,他的声誉与其说靠他的才华或修养,还不如说靠他的这把年纪。所有向他求教的人,本来对事情的答案没有把握,离开时却更觉得茫然。如果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他看上去还是可敬可佩的,但只要一开口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暴露出自己是草包。说起空话来他倒是说得头头是道,他有的是可鄙的才智和空洞贫乏的理解力。他的才华的火焰不是令四壁生辉,而是把屋子薰黑。那是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从远处看招人注意,走到跟前站住仔细一打量,枝头却没有结一个果实。”
最终他离开老师,1114年他重返巴黎并以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的资格出任圣母院教堂学校校长,教授辩证法与神学。
1117年到1119年,阿贝拉尔不仅感情上受到挫折,而且惨遭酷刑,他不仅身体上,而且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躲到圣丹尼修道院,但不久对知识的激情使他重新找回了斗争的兴趣,学生们没有忘记他,从欧洲四面八方赶到他的隐居地,听他讲课。巴黎大学由于有了他而成为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学术文化的中心,以致他有“巴黎的骄傲”之称。
他在此后所写一系列逻辑论文反映了他的神学思想,其中《论神圣的三位一体和政体》在1121年召开的索松主教会议上被谴责为否认上帝独立人格的撒伯里乌主义,从而被控为异端。但他毕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对待爱情的遭遇,他把它看成是自己受到的上帝的惩罚。
此后,他考证本院崇拜的圣丹尼斯传说中的讹误之处,僧侣群起攻之,迫使他出走,隐居乡间。有很多学生慕名而来,他在法国西北部的一所修道院为这些学生设立学校,写了《是与否》、《基督教神学》、《神学导论》等著作。他的教学活动引起教会精神领袖圣伯纳德的敌意性的关注。不安全感迫使他逃到偏远的布列塔尼地区,1126-1134年他在简陋的鲁伊修道院任院长,力图改变那里的愚昧习俗,却差点因此被僧侣所谋害。《劫余录》即叙述了他至此为止的经历。但他在此后的遭遇更为悲惨。
1136年他回到巴黎主教座堂学校任教,写了伦理学著作《认识你自己》。他的一系列著作激怒了贝纳尔。1140年召开的桑斯主教会议谴责他的学说。圣伯纳德专门写了《阿贝拉尔的错误》一文,列举其十六条罪状。阿贝拉尔的《神学导论》被焚烧。他不服从判决,准备到罗马上诉。他还在途中,教皇英诺森二世就已批准了圣伯纳德报告,宣判他的学说为异端。阿贝拉尔的敌人圣伯纳德“始终是个乡巴佬、封建主,而且主要一直是个大兵,他对城市知识分子(Intelligenzia)毫不理解。对待异端分子或异教徒,他只知道一个办法:武力。他是武装十字军远征的先驱,但他不相信用知识进行的十字军。”
阿贝拉尔在哲学上采取概念论,既反对威廉和安塞尔姆的唯识论,又反对洛色林极端的唯名论,认为共相是存在于人心之中表示事物共性的概念。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的理性,没有人像阿贝拉尔那样致力于把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他作为新神学的重要创始人圣托马斯的先驱,超过了圣安瑟尔姆。因阿贝拉尔强调理性,而被认为违背正统教会的传统教义,所以两次被指为异端。但他的这种思想却是对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最大贡献。
巴黎大学的创建者
阿贝拉尔死后60年,即在13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巴黎大学才正式建立起来,但毫无疑问阿贝拉尔应该被看作巴黎大学的真正创始人。巴黎大学的建立为中世纪的其他大学树立了模型和榜样。学者卡蒂诺·纽曼在他的有趣的论文《大学的优缺点》中说到,“阿贝拉尔的名字是与巴黎大学的发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教学方式无疑给将来的学校课程树立了典范。” 阿贝拉尔于1101年在麦伦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由于他长期寓居帕莱修养而关闭。随之,他在科贝创办了第二所学校,最后在巴黎的日奴维拉山创办了第三所学校。
在世俗学校开始建立以前,教会学校一直存在并很繁荣,且伴随世俗大学的成长在很长时间内与之并存。之所以称阿贝拉尔为巴黎大学的真正建立者,原因首先在于,由于他的名声很多人到巴黎学习,聚集在他的周围,听从他的讲课。其次,他扩展了巴黎的那些学校的课程和方法,提高了教学水平。最后他是第一个有突出成就的老师,在他的学生里有20个红衣主教、50个主教、一个教皇。他使得巴黎神学院成为基督教欧洲的神学院。阿贝拉尔是法国哲学家中发起智力运动的第一人,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一场现代精神的“文艺复兴”。
阿贝拉尔对巴黎大学的贡献,他对理性的强调,无疑都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影响,他是中世纪的法国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虽然他与爱洛伊斯是中世纪基督教的牺牲品,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爱情劫难成就了他的伟大,爱情的遭遇,成就了这个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