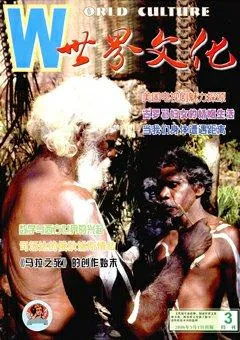天竺梵歌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把世界上的诗人分为两种:第一种诗人的幸福和痛苦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心潮共鸣;另一种诗人则通过作品重现整个国家和时代,并因智慧的灵光而永远受到崇敬。按照这种说法,身为“宫廷九宝”的诗人迦梨陀娑只能归属于前一种,而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传说的作者蚁垤仙人和广博仙人,则像恒河一样属于整个印度,他们当之无愧佩戴第二种诗人的桂冠。
一
有学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古印度、古希腊)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简单而优美的诗律,它可以在长篇诗歌中千变万化,因此听众总能体验到一种清新之感。以印度史诗在讲唱时所使用的语言为例。两部史诗都是经过数百年才得以形成的,成书的年代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之间。作为新兴的世俗讲唱文学,它虽然用梵语写成,但在语音和语法变化上比吠陀梵语简易许多,也有别于正在形成的古典梵语,是一种适合大众的通俗梵语。
《摩诃婆罗多》的产生相对较早,包括18篇,共有10万颂,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作为蕴藏印度文化的一座宝库,诗歌通过叙述俱卢族和般度族之间的战争,描绘了当时印度的巨幅画卷。《摩诃婆罗多》的叙述者自诩道:凡是有关法、利、欲和解脱方面的知识,史诗均收录进去了,并且史诗还有着神奇的魔力:“听过这部史诗的人,/再也没有更好的诗歌能使他欢欣,/好像一个人听了公杜鹃的歌唱,/再也不会喜欢乌鸦嘶哑的声音。/……/这篇叙事诗是获胜的名言至理,/国王若想赢得胜利,/应该将它洗耳恭听,/他便能征服敌人、战胜大地。/这是一部神圣的道德经典,/也是实际生活中最好的指南,/……/唱诗人就是智慧无边的广博大仙。/谁听了这部史诗,/一切源于行为、思想意识/和语言的罪孽,/都会从他身上消失。”言语之间,我们不难体会这部史诗在古印度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史诗前后情节的矛盾、语言的差异来看,《摩诃婆罗多》不可能完全出自广博仙人一人之手。其情节本身就交待了三个说书者:首先,广博仙人把《摩诃婆罗多》说给弟子发喜听;然后在一个蛇祭大典上,发喜在老师的首肯下,把故事“转述”给镇群王听,发喜的儿子骚底听到了这篇诗歌;第三次是骚底讲给寿那迦等修道仙人听。很明显,这里采用的是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框架式叙述结构”,让人感觉《摩诃婆罗多》几乎从头到尾都是直陈文体,是通过不同的说书者讲出来的。史诗开篇描写聚集在飘忽林里的仙人请求骚底讲述他从发喜那里听来的故事。骚底欣然同意,但他首先讲述的是镇群王蛇祭的故事,然后才讲唱发喜演唱的内容。因此,修道仙人在尘世广泛传唱的史诗是经过骚底添枝加叶后的版本。
口头流传的史诗,因传播途径的特殊而衍生出各种不同的版本。首先,口头讲唱的故事层层演绎,最初的讲唱者广博仙人给发喜讲述的是原始版本,后来的两个讲唱者则加上了自己创编的故事。其次,每一次讲述都会发生讲唱者和听众之间的互动和问答,这也对故事情节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三,史诗原本是刹帝利歌手的巅峰之作,是英雄主义和征战沙场的作品,后来则在婆罗门影响下变成了教诲民众的工具。最明显的篡改当属史诗前后的立场对峙:前半部分歌颂俱卢族,因为是依附俱卢族国王的歌人创作的;当“江山易主”后,艺人们又加进了偏袒般度族的颂歌。基于上述原因,学者们便把《摩诃婆罗多》称为“发展中的史诗”。
与《摩诃婆罗多》的动荡幻灭相比,《罗摩衍那》则充满着理想情怀,更多诗情画意的叙述。《罗摩衍那》文风老练,用典雅的语言成功再现了古印度社会中的崇高精神、国王职责和社会理想。
《罗摩衍那》具体产生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从很早的时候起,古印度的讲唱艺人便四处云游,讲唱有关罗摩的传说。到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民谣素材在蚁垤仙人手中经历了创造性变化,发展成为一部完美的作品。传说有一天,蚁垤仙人在树林中看到一对快乐的麻鹬。突然,雄鸟被猎人用箭射死,雌鸟由于惊恐和悲哀而尖叫起来。这时蚁垤仙人脱口而出几句谴责的话。余音未了,他发现这几句话里流动着一种完美的韵律。蚁垤仙人反复琢磨这一现象,并分析当时的心境,终于悟出诗歌创作的奥秘。这段“插话”告诉我们:口诵诗歌作为一种韵体表达方式,人的内心感受是其灵魂;而讲唱者蚁垤既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诗歌批评家。在“插话”最后,印度大神梵天显圣,指导蚁垤用其新创造的“输洛迦”诗体来赞颂罗摩的业绩,同时保证说:“只要在这大地上,青山常在水长流,《罗摩衍那》这传奇,流传人间永不休。”历史发展到今天,证实了大梵天的预言:数千年来,史诗已经和印度人民的心灵交织在一起。
经过蚁垤仙人的汇编,《罗摩衍那》的故事情节基本完备,但史诗的定本却出现很晚,公元7世纪,玄奘旅印时,《罗摩衍那》只有1.2万颂,而今天通行的本子却有2.4万颂之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讲唱歌手的“灵活多变”,他们在演唱时,会根据具体情况拉长听众喜欢的情节:当他们发现悉多凄恻的自诉能感动听众时,就加上几句哀婉幽怨的唱词;如果战争的场面能在武士居多的听众里引起共鸣,他们便机敏地创造出一批又一批的英雄,让他们继续厮杀;如果听众是有学问的婆罗门,他们就在教诲篇章上大做文章,用更多的伦理格言来博得婆罗门的欢欣。直到有了权威的文字版本后,史诗形式才固定下来。而此时,罗摩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吟诵和聆听这部史诗也成为一种宗教功德,人们甚至认为“天堂也会为抄写史诗的人敞开大门”。
二
印度人很早就发明了文字。公元前8世纪左右,印度商人从西亚带来闪族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创编印度字母。但是印度人并不重视书写,除了商业与政务方面,他们依然广泛使用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这大概与婆罗门垄断知识的心态有关。当然,印度气候炎热潮湿,其主要书写材料(树皮、贝叶等)难以长期保存,也是重要原因。所以,19世纪以前,印度典籍主要是靠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
在古印度文化传统中,学习梵语的方法是师徒对坐,口耳授受。对于专司祭仪的婆罗门来说,能否准确地记忆和唱诵圣诗是职业成败的关键。古印度人认为吠陀经典是“天启华章”,它的每一句诗乃至每一个音节都是神圣的,必须朗诵准确,不能出丝毫差错,否则会引发灾难。秉承这一传统,后世吟诵英雄史诗也被看作是娱神的行为。歌人将英雄(族长、国王等)的家谱整理成诗歌的形式,并在各种场合吟诵。例如,在马祭典礼上,要吟诵王族的传说,并且内容每隔10天重复一次,日夜不停:婆罗门在白天赞美主祭国王的慷慨好施,刹帝利则在夜晚讴歌他的征战业绩。此外,古印度还有一些讲唱诗歌的风俗,譬如在葬礼之后,服丧的亲属在室外一个荫凉的地方坐下来,请人为他们演唱传说故事,借以排遣哀伤。据一位公元7世纪的诗人描述,这种风俗在他那个时代依然存在,并且范围不再局限于丧葬:每当发生重大的损失之后,为了避免再发生不幸,人们便把灶火移到室外,在屋里则用钻木取火的方法点燃新的火种;然后,家庭成员把火烧旺,一直守坐到深夜,这时,还要请歌人讲述古人的故事和带有吉祥预兆的传说。
在古印度,歌人又被称为“苏多”,意为“王之御者”。“苏多”阶层,按《摩奴法典》记载,是“刹帝利男子和婆罗门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因是“逆婚”所出,只得位列6种低贱小种姓之首。不过,这只是婆罗门反对自己的女子下嫁给刹帝利的一种惩罚措施,实际上历代婆罗门女子嫁给刹帝利的现象屡见不鲜,所生“苏多”更不在少数。他们由于受到婆罗门的歧视,在政治上多倾向刹帝利,常以编唱英雄颂歌为业,以博得王室赏识。印度古代没有专职的史官,只有“苏多”负责记诵帝王的族谱,他们生活在宫廷之中,不仅善于编制和吟诵赞美诗歌,说唱长篇故事,而且学识渊博,精通各种礼仪,因此颇受王者敬重。
一般而言,传统史诗中的英雄首先是演说家,“苏多”自然也不例外。作为“王之御者”,他们要亲临战场:《摩诃婆罗多》中的全胜是持国的御者,他不仅负责为双目失明的持国描述战场上的情景,同时也是大战前俱卢族派往般度族的使者;《罗摩衍那》中的苏曼多罗,是十车王的御者,有着“大臣魁首”的美誉。据考证,歌人阶层在宫廷中的重要地位颇有缘起,早在《百道梵书》中就有记载:“苏多是国王的珍宝之一。正是因为他,他(国王)才登上神圣的地位。”苏多为国王执鞭御车,作用有二:其一,随侍左右,目睹时政,以便能根据自己的亲眼目睹讴歌英雄事迹,这与中国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的史官职责相似;其二,讲唱先王的业绩传说,作为教诲和娱乐,为国王、官兵等人解除烦闷,鼓舞斗志,这又与中国古代的瞽矇职责相似。
数千年来,《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部史诗一直代表着印度悠久的民族生活、宗教伦理和文学传统,是历史、传说、法典、哲学和颂歌的综合。今天的印度,每逢喜庆佳节,剧团便会在寺庙里公演史诗的片断,有些讲唱诗人甚至会一连九十多个夜晚为听众演说。所以泰戈尔说:“几个世纪过去了,但是《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源泉在印度这个国家里并没有枯竭。每天,每个村子里的每个家庭,都在朗读其中的诗句。不管是市场上的商店,还是在国王的宫廷门口,它们都受到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