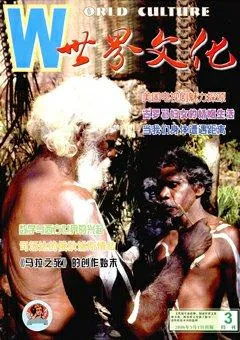永远的梦露
梦露的诞生,使男人对女人多了一种梦幻。她的美艳激起男人的不是邪恶,而是怜爱;不是占有的冲动,而是朦胧的快感。梦露属于那种世所罕见的,可将男人的低级欲望变成审美通感的女人。
然而1962年8月5日,梦露不再是梦露,她只是停放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的一间陈尸所的一具女尸,依然美丽却冰凉僵硬。于是,人们的所有关于梦露的诗意想象,瞬间即被这具女尸无情地拉回尘世。
死亡与梦露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她的周身溢满了大自然所赐予的厚爱,只要你葆有一颗健康的爱美之心,无论你是男是女,或老或幼,面对梦露(即使是照片)你都不会漠然视之。她是那种我们无意间在某个场合见过一面而终生不忘的女性。这样的场合包括挂历、画报、影照、书刊。世界公认她象征了一种高级性感,而引起性感又并不由于裸露。
她因此而成了美丽的焦点。她的姿色是一种自然资源,总会吸引形形色色的开发者。她最初不知道珍惜。因为孤苦无依的日子实在太久了,像一片瑟瑟抖动无处寻根的落叶。梦露既是遗腹女,又是私生女。母亲长年住在精神病院。幼年始寄人篱下,遭人歧视,甚至有一次被奸污。8岁时逃进孤儿院当洗碗工。她16岁那年,为离开孤儿院的非人待遇而同21岁的飞机工人吉姆·多尔蒂结婚。婚姻的不幸使她曾试图自杀。为生计她当过摄影模特,后长期被好莱坞的制片人把她的美色当作摇钱树。他们专门安排她在一些电影里扮演淫乱放荡的女人角色,以她的美貌倾倒了各国观众,也引起了巨商、政客、名流甚至美国总统的注意。她知道许多人只对自己的性感表演有兴趣,这使她渐生厌倦。一个晚上,她回忆拍摄影片《安娜·克里斯蒂》的情景时深感难过:那样的表演她觉得皮肤似乎在脱落,内心的感情也似乎裸露于世。
有多少美艳就会有多少骚扰。这骚扰不仅来自好色之徒,社交界、新闻界也不肯轻易地放过她。1954年岁末,整个好莱坞的著名人士都出席了庆祝《七年的思考》拍竣晚会,这意味着他们最终接受了作为影星的梦露。而这晚,梦露却从一片赞扬声中隐去,套上黑色假发套,戴上墨镜,更名改姓“逃”到了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农场,与她的女友艾米·格林共度圣诞节。电话不断地打来又被不断地拒绝。之后,梦露和艾米如同两个恶作剧的小女孩儿一般竟乐得在地毯上打滚。“名声对我来说犹如昙花一现,那不过是侥幸得来的东西……当它一旦逝去,我已体验过这只是一种轻浮而易变的东西,我并不靠她才能生活”。清醒如梦露者或许已经感到,对于她,名声日增恰恰意味着安全感的递减。
遗憾的是,超凡的美艳常常置她于诸多误解之中。不少人仅仅视她为“性感明星”而拒绝给予理解,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艳星只需要展示千娇百媚即有市场,表演才能与之无涉。其实不然,只看美国“影星之家”创始人李·斯特拉斯伯格的评价就可以了:“我曾和上千个男女演员一起工作过,但我感到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出众的,第一个是马龙·白兰度,第二个是梦露。”她出身贫寒,无缘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她却表现了强于他人的自学热情。她受益于许多书籍,包括传记、历史、诗歌。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一书也曾伴她度过旅途时光。闲来她还写诗。就我有限的阅读看来,她的诗歌水准不具多深的造诣。但意义显然在于:从贫民窟、孤儿院走来的梦露,尚未被灾厄频临、险象四伏的生活所扭曲。
梦露又是那般弱小。她坦言她“十分害怕孤独地面对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我最需要的就是爱”。但很多权贵、要人仅仅将她视作猎艳的玩物,一旦酿成桃色新闻而公诸于众便以牺牲梦露为代价洁身远行。那一段日子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夜里需服镇静剂方能入睡。终于在36岁时的一个子夜,她不明不白地辞别了人世。她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团。美应该是永恒的,美的毁灭却是那样无奈。大自然生命规律难道不应该是存优汰劣吗?
奇异的是,梦露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早亡成全了她的不衰魅力,说这话不免有些残酷。倘若今日依然健在,梦露该是耄耋之年。请设想,那迷人的满头金发变得枯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双眼昏花浑浊,鲜润欲滴的嘴唇苍白干涩,丰满挺拔的胸部松弛萎缩,活泼欢快的女儿态已是垂垂老矣。而这一切尚未发生,梦露便凝固了永恒的风韵。
红颜薄命,幸或不幸,谁人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