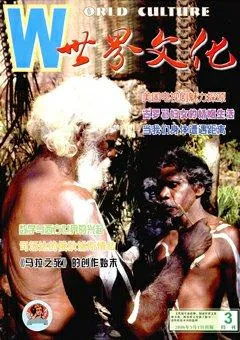司汤达的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概念。美国心理学专家约瑟夫·洛斯奈在其所著《精神分析入门》一书中,对俄狄浦斯情结解释说:“由于婴儿时代和童年早期的环境状况,每个孩子都渴望从与自己异性的父亲或母亲身上满足性欲,而怨恨与他同性的父亲或母亲。原始的社会和文明的社会都有反对乱伦的严厉禁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禁忌;因此,这些渴望在暗中被感觉到,却一生永远地埋藏在潜意识深处……有时候,潜抑的俄狄浦斯情结突破潜意识的封锁,溜到意识里来了。不过,它们是以伪装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比较不会被我们所反对。我们常可看到的是:某个男人与一个年纪大他很多的女人结婚,就是很好的例子。更戏剧化的是,报纸偶尔也刊载这类报道:一个女孩子为了某种原因杀害了她的母亲……”
有人把俄狄浦斯情结称为恋母情结。其实,称其为恋母(父)仇父(母)情结更为全面而准确。本文向读者介绍一个令弗洛伊德也感到吃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例子——作家司汤达。
恋 母
在司汤达晚年写的自传里,有许多关于他幼年时对他年轻的母亲的爱的回忆。他写道:“我发现了许多使我在1835年(写自传时)吃惊的事情,是我幼年时代的主要事件。”
在书中,他勇敢而诚实地记录了他如何“尽可能放肆地以一种疯狂的热情爱恋着我的母亲……”又如何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朦胧地形成了对父亲的妒忌。他写道:“我母亲热烈地爱着我,常常吻我。我也常常热烈地回吻她。我常想吻遍母亲的胸部,并希望她不要穿衣服。有时她不得不逃走。当父亲出现,打断我们的亲吻时,我就非常憎恶他。”“在我大约6岁(1789年)爱着她(母亲)时,有一种和我在1828年以疯狂的热情爱阿尔贝特·德·吕邦帕(司汤达的情人)的极其相似的特征……”
仇 父
对于父亲,司汤达这样写道:“皱纹满面,丑陋,冷酷,”“永远不可能找到把我同我的父亲这样两个如此完全敌对的人联结在一起的机会。他不能说一句不使我扫兴的话……他并不是像一个人爱他的儿子那样爱着我,而是把我看作是家庭的继承人。”
母亲死后,父亲请了一个耶稣会神父做家庭教师,教育他的3个儿女。小司汤达对这个顽固的神父的愚蠢、严厉的教育(例如,一次散步时,小司汤达用像“可怜的犯人”那样渴望和羡慕的目光看着那些在河里游泳的孩子们,这位神父却对他说:“品行端正的孩子们是从来不在河里游泳的,那些在河里游泳的孩子最终都会被淹死。”这种恐吓使司汤达从小就怕水,后来差点儿因此而丧命)非常反感,并且将其归罪于他的父亲。对此,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父亲和雷纳拉神父毒害了我的童年……我恨神父,我恨我的父亲——他是神父强权的后台。”
少年司汤达对父亲仇恨的程度可以从以下一件事上看出来。1792年秋,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逮捕、审判,看到父亲、耶稣会神父和他们的那些保皇党朋友们对国王的命运的担忧,9岁的小司汤达暗暗地希望国王被处死。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偷偷地编制了一份历史上最大的弑君者的名单。1793年1月,路易十六真的被处死,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最强烈的快感所支配……我不能继续读我的小说了。为了能够尽情地享受这一伟大的事件,我闭上了我的眼睛。”
这是司汤达有关自己少年时代的回忆中非常可怕的一幕。他不知不觉地把国王的罪过(共和国的报纸控告国王阴谋判国)在潜意识里迁移到他父亲头上。他自我分析道,他在国王被处死这件事上所感到的极度欢乐,是因为他在想像中看到他自己的暴君般的父亲被杀而引起的。而虽然岁月不断流逝,这种快感却一直在他身上持续,到他在自传里对其进行反思时,已有42年之久。据此足可见出,他的仇父情结有多么强烈和深刻。
而这仇父情结的隐秘的根源就是对母亲的爱恋。他勇敢地对世人承认:“在我内心深处,我仍然妒忌着我的父亲。”
这些回忆是虚构的吗?
有人称,司汤达有关他自己恋母仇父情结的回忆是最早的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记录,它在弗洛伊德对心理学作出伟大发现前半个多世纪就提前证明了俄狄浦斯情结说的科学性,并和司汤达生活中另外两个事实一起,成为对俄狄浦斯情结说的全面的注解。这两个事实之一是,司汤达年轻时曾经疯狂地追求过的两个女人,都年长于他——女演员梅拉妮,年长司汤达3岁;彼得拉格鲁阿夫人,年长司汤达6岁。另一个事实是:他的两部重要作品《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中的年轻的男主人公所爱的女人,也都比他们年长——于连曾对之说:“我一直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的恋人是比他年长10岁、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母亲德·雷纳尔夫人;法布利斯“爱她爱到了崇拜的地步”的,是年龄比他大十多岁的姑母。
但是,也有人对司汤达恋母仇父情结的早年回忆及其他人类似的回忆持不同看法。19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认为,这类回忆,主要是由“一个老人告诉我们他虚构的青年时代的不真实的事情”所组成的。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哥德把他晚年写的自传题为《诗与真》,因为他知道对自己的过去不可能再重复其真实,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诗情的回忆。那么司汤达呢,他的回忆能否重复其遥远的过去的真实呢?他说他6岁时对母亲的爱,有一种40年以后以疯狂的热情爱他的情人的极其相似的特征,这是否在幼年回忆中混杂了成年时期的经验与感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