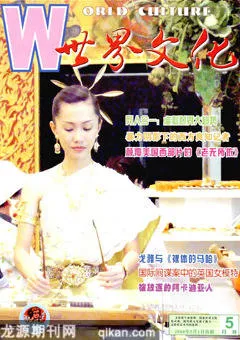福克纳:游走在家乡与世界之间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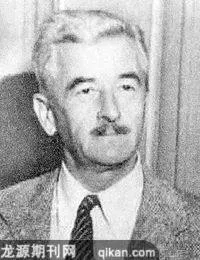
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南方作家,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据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以及完成的博士论文,在英语作家中,关于福克纳的已占第二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在我国,有关福克纳的著述虽然不及在美国那么丰厚,但也成就卓著, 2007年是福克纳诞辰110周年。今年中信出版社版出版的美国作家杰伊·帕里尼撰写的《福克纳传》,无疑是福克纳研究领域内的又一新成果。该书2004年在美国出版后好评如潮,其最重要的特点也许是:除了没有虚构外,它完全可以当作小说来读。当你打开这本书后,在你没有读完之前你很难将它放下。
福克纳是一个游走在家乡与世界之间的作家,这一点对于福克纳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专家学者无论怎样关注和强调都不算过分。他的家乡观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的家乡;而他的创作又是如此具有普遍性意义,以至于影响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一代又一代作家。“他发现的、创造的、复制的、重新想象的故事,既是南方的故事,也是整个美国、整个人类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福克纳是在要求读者考虑这些宏大的问题: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活着?”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说:“当你回顾上一个世纪的欧洲文学,你到处可以发现清晰的或不那么清晰的福克纳的指纹。”其实又何止是欧洲,整个世界都留下了福克纳的指纹。拉丁美洲作家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等都受到过福克纳的影响,中国当代许多作家都曾经震惊并倾心于福克纳的叙述和描写,余华称福克纳为“我的师傅”,莫言甚至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福克纳”。
福克纳1897年9月25日出生于密西西比州一个庄园主家庭。祖先为苏格兰移民。他是家中的老大,还有三个弟弟。1902年随家庭迁居到离出生地不远的拉斐特县的奥克斯福镇。此后,福克纳一辈子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他在那里创作了绝大多数作品,他小说中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界就是以这个县为蓝本虚构的。福克纳的曾祖父是一个传奇式人物,被人们称为“老上校”。福克纳曾不无自豪地说:“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地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约翰·萨多里斯的原型:性格丰满、行动有条理,在1861~1862年曾组织并指挥过密西西比步兵团……他建造了我们县的第一条铁路,写了一些书,在那个时代完成了伟大的欧洲之行,死于决斗。他死后,提帕县为他竖起一尊大理石的雕像。”祖父被人们称为“小上校”,但他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重现“老上校”昔日的荣光。他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家,家业在他手里开始衰败。父亲瞧不上福克纳,他们永远难以友好相处。南方人对于讲故事有着特殊的热爱。他们有这样一种传统:“男人们围坐在篝火旁,喝着酒,抽着烟,回忆过去的日子,往往一聊就是一个通宵。”幼年的福克纳往往是那些传奇故事的热心听众。正是家乡的故事,还有那里的山山水水滋养了福克纳,并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他的小说中的字里行间。
福克纳有浓郁的家乡观念、荣誉感和责任感。他说:“我不是文人,我是个农民。”1957年,当一位记者询问他眼下正在看什么书时,他回答道:“没有,夫人。我读书很少,我只是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乡下人。”福克纳敢于承认、也乐于做一个农民。只要他稍有闲暇,他就会去他的“绿野农庄”忙一阵农活。他开拖拉机耕地、整理栅栏、清扫场院、维修机器、刈麦、割草、喂马等。他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曾对那些向他表示祝贺的人说,他打算继续当一个淳朴的农夫。他不打算离开他的棉花田,千里迢迢地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去领奖。当然,他最后改变了主意。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办公室里工作时,上司叫他把脚本拿回家去写,意思是要他回公寓去写,他却回到了几千里之外的老家。1961年他甚至拒绝了肯尼迪总统的邀请,没有去白宫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聚会。他说:“我已经老到不适合做这种跑很远的路,和陌生人吃一顿饭这样的事了。”福克纳在心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他的“山楸橡树”。他在小说《我弥留之际》中写道:“当他(上帝)造一直在动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把它们造成平躺的,就像路啦,马啦,大车啦,都是这样,可是当他造呆着不动的时,他就让它们成为竖直的,树啦,人啦,就是这样的……人老是不得安宁,老是要上什么地方去,其实他的本意是让人像一棵树或是一株玉米那样呆着。因为倘若他打算让人老是走来走去上别的地方去,他不会让他们肚子贴在地上像条蛇那样躺平吗?”在这里,福克纳把漫无目的的胡乱运动同蛇,也就是同恶相提并论,表明了他对世界的总体看法,这也是他对美国生活的总体评价。
1925年,他像他的曾祖父一样第一次游历了欧洲。他在那里逗留了五个多月,实地感受了欧洲文化,接触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从而慢慢开始摆脱美国南方传统的守旧意识和偏执思想。在随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福克纳经常离开他的家乡,去纽约、好莱坞、弗吉尼亚等地,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很多地方,欧洲、非洲的埃及、亚洲的日本和菲律宾,还有拉丁美洲。但他每次外出都几乎匆匆而回。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奥克斯福,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取名为“山楸橡树”那所住宅。
就像神话中的安泰一样,福克纳的双脚不能离开地面。他从他脚下那片“意义深重的土地”中获取力量。当他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听到了四周空气中的各种声音,这些声音后来被他一一加工成了小说。1953年年底,福克纳在普林斯顿遇到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后者问他:“你从哪儿弄到那些故事的?”福克纳说:“我听见了很多声音。”爱因斯坦点头微笑,他显然明白了福克纳的意思。福克纳的故事虽然都来源于美国南方,但是,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读者不只是南方人,他们应当遍及世界各地。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随处可以发现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命题:传统社团的消失、原始自然的消亡、资本主义的残暴、阶级和种族分离的诱惑力和破坏性、清教徒式的自高自大、战争的荒诞与意义……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的世界终于成了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福克纳一生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近百篇短篇小说,这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描写美国南方生活的,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体系”。“约克纳帕塔法”原是穿越他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北部拉斐特县的一条河的名字,其意思为“在平坦的土地上缓慢流动的水”。“福克纳以这个假想的县为背景,写了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有时,为了找出一桩邪恶,他会追溯到很久以前,有时,他又讲述他自己生活时代的故事,直到一个完整的社会在他的笔下逐渐形成。”
约克纳帕塔法县是福克纳虚构的一个县。他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为这个县绘制了一幅地图:它的面积为2400平方英里,人口中白人为6298,黑人为9313。这个县唯一的业主与所有者是威廉·福克纳。福克纳反复讲述的就是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他自己和这个世界。但是,福克纳拒绝像写自传那样去创作作品,人们不能指着福克纳的任何一部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说:“看,那就是福克纳。”福克纳如果存在于自己的作品中,那他一定像上帝一样:哪里都找不到他,但他又无处不在。
福克纳说:“我的家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这也是美国“南方文学”的共同特点之一:“对家乡的炽热感情、对南方的历史既骄傲又沉痛的心理、一种大家庭的共同命运感、在种族问题上的内疚与对资本主义文学疏远、陌生感。”“地域感对于福克纳来说意味着一切。和任何其他20世纪的美国作家不同,福克纳知道如何挖掘一个地域——包括人文历史在内的诸多细节,从而创造出一种文学效果。”家乡的那片土地,是一块流动的疆域,没有边界的文本,是福克纳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福克纳作为一个“南方作家”,他对南方的感情也比较复杂。他说:“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根本就不喜欢,但是我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使是怀着憎恨。”
评论家艾伦·塔特说:“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地方主义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在空间上则是无限的。”一个作家,若想概括整个大陆,包罗万象,他将会一无所有;一个作家,若执着于某片土地,有所选择,有所舍弃,他反而获得了一切。福克纳无疑属于后者。
综观福克纳一生,他扮演过太多的角色:孤僻的少年、负伤的老兵、流浪汉、波希米亚诗人、好莱坞写手、酒鬼、游手好闲的家伙、邮政局局长、丈夫和情人、猎手和养马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化大使、驻校作家、慈爱的外公、贵族……但他最终却是一个作家。虽然他经常为赚钱而写作,但他内心深处只想当一个纯粹的作家。“他写了一些书,然后死了”,这是他理想中的墓志铭。作为一个作家,他首先是一个南方作家,一个美国作家,但他无疑也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