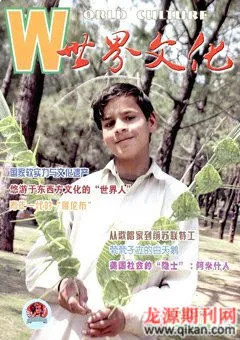从觉醒到幻灭只需一小时
《一小时的故事》是美国19世纪下半叶妇女文学的代表作家凯特·肖班(1851-1904)的短篇小说。她曾经由于长篇小说《觉醒》被当时的舆论谴责为有伤风化,但后来的评论界却给予了她很高评价,认为她是D.H.劳伦斯和西蒙·德·波伏瓦的先驱。
《一小时的故事》的篇幅非常短小,三千字不到,情节也相当简单。作者选择了马拉德夫人突然听说丈夫车祸身亡这样一个时刻作为故事的起点,她真诚地为丈夫的死而悲痛,但又突然发现自己是跟一个多么平庸乏味的人过了大半辈子,现在终于感到“自由”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不是这种过度兴奋,她也不致在见到丈夫生还时受到那样大的刺激,致使她为这一刹那的自由感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短短一小时的故事讲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女人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又迅速幻灭的过程。虽然作者惜墨如金,凭着高超的叙事技巧——伏笔和悬念的巧妙运用,使故事读起来跌宕起伏,百转千回。
小说一开头是这样描写马拉德夫人从姐姐口中得知丈夫死讯的反应的——“要是别的妇女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手足无措,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她立刻一下子倒在姐姐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为什么马拉德夫人的举动会和别的妇女不同呢?她和丈夫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夫人稍稍平静了一些之后,便独自走进自己的房间,对着窗外坐了下来,这时她又看到了怎样一幅图景呢?——“她能看到房前场地上洋溢着初春活力的轻轻摇曳着的树梢,空气里充满了阵雨的芳香,下面街上有个小贩在吆喝着他的货色。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微弱歌声,屋檐下数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对着她的窗的正西方,相逢又相重的朵朵行云之间露出了这儿一片、那儿一片的蓝天。”俨然一幅祥和、喜悦、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色,这难道是一个沉浸在丧夫之痛里的女人该有的心情吗?这又加重了读者的疑问。
夫人坐在对着窗口的椅子里偶尔啜泣一两声,“她还年轻,美丽。沉着的面孔出现的线条,说明了一种相当的抑制能力。”这短短一句是唯一一处作者对女主人公外貌上的描写,“年轻,美丽”也许说明了夫人有并不绝望的资本,她可以再嫁,她的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然而那种“抑制能力”是什么,难道夫人此刻正在抑制着心里的某种情感?是悲伤吗?显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根本无须抑制这种正常的感情宣泄!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夫人望着远方的蓝天在理智地思考着问题,她突然感到“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又有点害怕。那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太微妙难解了,说不清、道不明。” “她开始认出来那正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可是她意志就像她那白皙纤弱的双手一样软弱无力。”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夫人这样呼之欲出,却又拼命压制呢?她终究是压抑不住了,感情瞬间爆发——“当她放松自己时,从微弱的嘴唇间溜出了悄悄的声音。她一遍又一遍地低声悄语:‘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夫人的丈夫猝死,她却发出了这种违背常理的呼喊,这不是太大逆不道了吗?!随着夫人真实感情的表白,读者的疑惑到达了顶峰,小说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接着,在夫人开始激情澎湃地构想她那丧夫之后的光明未来时,娓娓道出了他们夫妻关系的实质——“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替她做主;她将独立生活。再不会有强烈的意志而迫使她屈从了,多古怪,居然有人相信,盲目而执拗地相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 “当然,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他的。但经常是不爱他的。”此刻读者心中的疑云彻底消散了,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夫人根本不爱她那个专横霸道的丈夫,而丈夫的死亡对她来说正是一种求之不得的解脱和自由!
至此,作者开始把读者引入对“妇女地位”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的思考,用冷峻的讽刺隐隐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的不满和对妇女深切的同情。
在19世纪那个男权至上,等级森严,虚伪势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妇女是没有办法自主选择婚姻的,财产和门第是婚姻中主要被考虑的因素,而爱情与幸福则往往是不得不被牺牲的代价。妇女嫁入夫家、冠以夫姓之后,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个性与尊严也跟着娘家姓一并被抹杀了,从此成为了丈夫和家庭的附庸,努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
可以想象,马拉德夫人也许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在很年轻时就由别人做主嫁给了一个她根本不了解的马拉德先生。青春勃发的马拉德夫人曾经对新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而马拉德先生却是个自私冷酷,独断专行,过于理性而生命意识匮乏的人。在多年的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家庭生活中,夫人的梦想、激情和生命力被彻底地窒息了。她渐渐变得麻木、绝望,和别的妇女一样俯首帖耳、亦步亦趋地跟随着丈夫的脚步。这种生活让“她一想到说不定自己会过好久才死去,就厌恶得发抖。”
正在这时,上天为夫人送来丈夫的死讯,伦理道德告诉她应该悲伤难过,所以她真心诚意的痛哭流涕;可当她一人独处时,却“有一种邪恶的快感控制着她”——“自由了!身心自由了!”是的,从此以后,丈夫消失了,不会再有人钳制她的自由,不会再有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她的身上,她终于“有了独立的意志”,她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了!——“来日方长的岁月可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张开双臂欢迎这岁月的到来。” “她在纵情地幻想未来的岁月将会如何。春天,还有夏天以及所有时光都将为她自己所有。她悄悄地做了快速的祈祷,但愿自己生命长久一些。”那曾经的梦想,激情,和生命力又一股脑地重新回到了她身上,她憧憬着可以无拘无束的读书、写信、游园,甚至邂逅真正的爱情!当她怀揣这些走出门去的时候,“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她的举止不知不觉竟像胜利女神一样。”
可是,情势突然急转直下——等到夫人随姐姐下楼来时,布兰特雷·马拉德(马拉德先生)却泰然自若的出现在她们面前…… 原来马拉德先生并未搭乘那列火车,幸运地逃过了那场劫难!至此小说到达了第二个高潮。而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又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呢?——“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说她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小说戛然而止。
短短几分钟,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生活又以不可阻挡之势逆转回到原来的轨道。“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她又怎么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承受这样来回往复的愚弄!死亡成就了她的尊严。可讽刺的是,夫人是因极度高兴而死的,也许马拉德先生会痛不欲生,毕竟他无辜的夫人是因见到他“意外生还”而狂喜不已,激动致死的!他甚至要求树碑立传来感激追悼他那忠心耿耿的妻子!——可真相又是如何呢,只有马拉德夫人自己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夫人,这样的结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既然原来的生活让“她一想到说不定自己会过好久才死去,就厌恶得发抖”,那么当梦想破灭之时,她倒不如早早的抽身而去……
凯特·肖班这位女性主义作家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演绎了一个妇女急欲挣脱家庭和男权的牢笼最终希望幻灭的过程。作品揭示了在当时那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妇女们满足于作为丈夫的附庸、家庭的奴仆而存在,心甘情愿地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那些为数不多的觉醒者们为了能在家庭中获得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空间,做出了艰难的努力,但冷酷的现实却常常当头棒喝地告诫她们,那些妄想仅仅是痴人说梦,就如同本文的女主人公,从觉醒到幻灭只需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