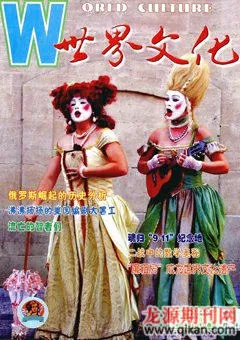科马克·麦卡锡和他的《路》
为庆祝出刊1000期,美国《娱乐周刊》推出了一份“新经典”榜单,在1983-2008年这25年间出品的电影、图书、电视和音乐等多种文化娱乐产品中,分别选出了100部最佳作品(产品)。百部最佳图书之首为科马克·麦卡锡的《路》、第二和第三名分别为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和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其实早在2006年,《纽约时报书评》在评选“过去25年出版的美国最佳小说”时,科马克·麦卡锡1985年出版的《血色子午线》就名列第三。《血色子午线》也被誉为20世纪最出色的一百部英文小说之一。而《路》也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即2007年赢得美国普利策最佳小说奖。
在我国,麦卡锡的名气似乎没有那么大,数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过他的“边境三部曲”——《骏马》、《穿越》和《平原上的城市》,其中的《骏马》曾获199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评论界图书奖”。
生 平
科马克·麦卡锡1933年出生于美国罗得岛州,爱尔兰裔。在家中6个孩子中行三,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律师,名叫查尔斯,他也被取名查尔斯。1937年,他们家从罗得岛搬到了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麦卡锡在罗马天主教家庭长大,在诺克斯维尔上的也是天主教中学。1951-1952年,麦卡锡进入了田纳西州立大学,主修文科。1953年,他加入美国空军,服役4年,期间两年在阿拉斯加主持一个广播节目。出于某种原因,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科马克,他似乎是沿用了一个爱尔兰国王的名字。1957年,他重返田纳西大学,这期间,他在学生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但没有获得学位便再次离开学校。1961年,他和大学同学李·霍尔曼结婚,生有一子。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不长时间。在芝加哥,他当了一名汽车技师,并在这里写下第一部小说《看果园的人》。小说于1965年发表,并以其“冷峻,严肃和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生动鲜活的语言”荣获当年福克纳基金会的“最佳新人奖”,麦卡锡在小说中表现出的文学天赋也得到了评论界的承认。
1965年夏天,借着从美国艺术文学院获得的游学奖金,麦卡锡乘船出海,游历了爱尔兰。在海上他遇到了船上的歌手安妮·戴丽丝。他们于1966年在英国结婚,并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得以继续环南欧旅游,直到登陆伊比沙岛并在那里安家。他在那里完成第二部小说《黑暗》并于1968年回到美国时发表。麦卡锡的第三任妻子杰尼弗·温克利是位学者,目前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居住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北部。
麦卡锡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极端贫困,或者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或者住在汽车旅馆里。他一半靠补助金,一半靠老天爷维持生计。“我没有钱,我什么也不是,”他说,“正当我用完牙膏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想起邮箱里有免费试用的样品。”
他离群索居,极少接受采访,排斥公众活动或谈论自己的作品。不过近年来,他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可能他希望他的露面会给那些崇拜他的人一个交待。他的崇拜者对他的一切都感兴趣,如有人统计过,他的作品中有13次提到可口可乐。有人甚至拍了一部名为《科马克的垃圾》的短纪录片,其中的一位妇女说,她已经收集了好多袋麦卡锡的垃圾。她说从垃圾上可以看出作家喜欢吃什么牌子的冰淇淋。他是个台球高手,喜欢高尔夫球,酷爱牛仔靴,驾一辆平板卡车。他在打字机上写作,最多时同时进行5部小说的写作,哪部先写完就现发表哪部。尽管他有隐者的名声,《纽约时报》还是发现他是个“颇有魅力的人,世界级的谈话者,有趣,固执,动不动就笑。”他身高不足6英尺,蓝眼睛,从不参加投票选举。他个性耿介,拒绝参加巡回书展,不讲课,不做演讲,不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做任何宣传,不愿意接受采访,被认为是“塞林格以来美国文学界最著名的隐者”。
确实,就是在美国,科马克·麦卡锡的价值也是在近十几年才被人认可,或者可以说他是大器晚成。因为直到1992年《骏马》出版后,他才被认为是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之前的小说,包括《萨特尔》(1979)和《血色子午线》(1985),哪一部的精装本销量都没有超过2500本。2006年,根据他的《老无所依》改编的同名影片获多项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编剧,最佳男主角奖),再加上他的后启示小说《路》获得普利策奖,这个老作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被认为是海明威与福克纳的唯一继承者,是他的作品帮助美国式文艺告别了低级的大众消遣。据称根据《路》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在2008年底推出,并且也有望冲击奥斯卡奖。
创 作
科马克·麦卡锡的崇拜者认为,他是威廉·福克纳以来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从主题上说,他的小说有存在主义和启示文学的冷峻和庄重。他的主要角色不是孤独落魄的失败者就是罪犯和流浪者。在文体上,他被认为是福克纳和乔伊斯的继承者,通常没有情节,缺乏传统的标点符号,用词稀奇古怪。索尔·贝娄最赞赏他“对语言绝对的强势使用,他的那些关乎生死的句子。”如《血色子午线》写的是19世纪40年代一帮雇佣军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边界驱赶屠杀印第安人的故事。他们剥下印第安人的头皮拿去换金子。“在美国文学史上,只有《白鲸》有资格与《血色子午线》相提并论,”批评家斯蒂芬·夏维罗认为,“两者都有史诗般的宏大,都能引起广泛共鸣,语言奇巧复杂,以一种偏执的细微去探索无限的宏大与遥远。”
也有人说麦卡锡是美国小说史上最大的赝品,《纽约人》说他是“美国最拙劣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写作戏剧化的花言巧语为乐,他出色地使用了《圣经》、莎士比亚悲剧的语言,成功地模仿了麦尔维尔、康拉德和福克纳。”《纽约时报》有书评嘲笑麦卡锡有“感伤癖,矫情做作,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有人对他对女人的描写多有微词。这个结过三次婚的作家说:“我不想装模作样地说我理解女人。”
如果在麦卡锡的作品中有什么绝对主题的话,那就是暴力和残酷。他说:“没有流血的人生不多见。”他的早期小说写的是恋尸狂、性变态和杀童,读他的作品,我们会不断受到这个恐怖作家在表现残忍快感时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如有人说《血色子午线》是“文学史上所能发现的所有野蛮行径的集大成者,对暴力、屠杀、折磨、掠夺、谋杀的描写都很精彩。”
麦卡锡喜欢的是科学家,而不是作家。除了麦尔维尔、陀斯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福克纳之外,他基本不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他对不关注生死问题的作家不以为然。在《纽约时报》对他进行的一个难得的采访里,他透露了他对包括亨利·詹姆斯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不屑:“我不理解他们。对我来说,那不是文学。许多被认为优秀的作家在我看来很奇怪。”
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致力于描写美国及墨西哥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经历及人生感受,这些在美墨边境地区发生的动人故事,既有恶梦般的屠杀、令人心惊肉跳的暴力,又有田园诗般的艺术表现,被评论家称为“地狱与天堂的交响曲”。麦卡锡钟情野外生活,人烟稀少的荒凉沙漠,黑暗中的激烈争斗,简洁有力的语言,构成了其小说的主要元素。
麦卡锡的西部故事是从几个坚忍脱俗的青年流浪者展开的。他们感悟人生,探索生命价值,情节高潮之处每每伴随着神意的启示。他的大部分作品描写的都是福克纳式的西部小人物的转变。抽象灵性的启示主题既是作者自身思想的升华,也映衬了他对大自然的炽热感情及对人类社会的深切关注。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始终是最伟大的存在。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动物、甚至日月山川都在无时无刻地审视着人类的种种行为——愚蠢、邪恶与残暴,它们也欣赏着人类的不朽英雄史诗,铭记着英雄们的善行义举。
麦卡锡既是思想天才,又是语言大师,他能在小说中纯熟、确切地使用英语、西班牙语表现人物的不同文化背景,能灵活自如地用俚语、土语和牛仔语言表现角色各异的身份、性格、教养和志趣。
他的作品多显示南方哥特风格,属后启示文学流派。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把他和托马斯·品钦、唐·德里罗和菲利普·罗斯一起,列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四大小说家。
《路》
《路》是麦卡锡的第十部作品,被认为是一部“残酷的诗学”。2006年9月出版以来好评如潮。
小说讲述的是核爆炸之后的冬天,尘雾笼罩全球,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也没有了政府和任何组织。夜间伸手不见五指,白天灰蒙蒙一片。风夹带着黑灰永远不停地刮着。河是黑的,海是灰的,最干净的是阴沟里的水。即使在南方,气温也常常降到零度以下。
公路上到处是汽车残骸,熔化的轮胎在地上结成一堆堆黑渣。楼房的玻璃全部熔化,成了一串串冰挂,贴在楼壁上。森林只剩下一根根焦黑木柱。动物都死了,植物也都死了。曾经熟悉的世界,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出现,绿色只有梦里才见得到。红色还看得到,那是仍在燃烧的火和人吐出来的血。
在这场浩劫中,有一家人侥幸活了下来。他们有一支手枪和一发子弹。父亲告诫儿子不要轻易使用子弹,如果遇到危险就用仅剩的子弹自杀。可是,孩子的母亲却不堪忍受生命的残酷而拔枪自杀。父亲常常对死去的人羡慕不已,他们解脱了,不用再忍受生存的苦难。但是,他不能死,他要带着儿子,去寻找可能的希望。于是在烧成灰烬的荒原上,在漫漫长路上,父子俩开始了前往南方海岸的艰难旅程。路上凶险莫测。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死了,死于核爆炸,死于寒冷,死于饥饿,死于绝望,但少数坏人靠着吃人生存下来了。他们不但要寻找食物,还要躲避那些饿红了眼的吃人者。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他们面对的将是生与死的选择和善与恶的较量。他们唯一拥有的是彼此的关怀和对生存的渴望。
在这部小说中,核爆炸的一闪替代了作者西部小说中的暴力打斗。核爆炸的一闪也闪掉了我们对作者的期待。小说的开始,事件仿佛发生在作者早期小说中的精神病人的世界中,就好像《血色子午线》中法官的枪已经升级到了原子弹,并在向全世界发泄他的不满。世界变了,改变的不仅是地球的外观,还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的其他作品中,到处是对死亡的恐惧,而在《路》中,人还充满了对生存的恐惧。人体几乎成了没有思想和信念的躯壳,以前的一切,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都融化到了虚无和黑暗中。正像主人公的亡妻所说,“我们是恐怖电影中行走的死人。”当然,小说也不乏恐怖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幽默:地球上最后一瓶可口可乐的美味,一块布告牌保留的世界毁灭后的仅存文字:“岩石城一览”。
小说由数百个互不相关的时段、对话和情节组成。麦卡锡的小说大多不注重情节,而《路》又是他所有小说中最缺乏情节的。我们看到,这对父子实际上无路可走,也走得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在无法抑制的冲动下向前走。所谓情节实际上只是父亲的一种现实需要,即在一个不能给人生命与希望的世界里,要让儿子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在他和死亡之间,孩子就是一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们冒着严寒,忍饥挨饿推着一个小车向前走着,小车上的一点点物品是他们从几年前被洗劫过的老屋中找来的。
但是,面对没有生机的世界,父亲坚守着最基本的信念:“我的任务就是照看你,”他告诉儿子,“是上帝派我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谁要是碰你都将死在我的手下。”在让儿子活命的同时,更大的挑战是精神上的,在儿子目睹种种道德堕落的行为的同时,他要设法保留儿子善良的天性。“我们还是好人吗?”儿子在震惊和困惑中问道。父亲坚持说他们是好人。“这就是好人的所作所为。”他告诉儿子。“他们不断努力,他们从不放弃。”接着,儿子问他,为什么他不帮助那些他们在路上碰到的逃难者,而是躲他们远远的,甚至还向他们开枪?“我们应该走向他,爸爸,我们可以收留他,带他一块走……我可以把我的吃的分一半给他。”在坚持他们是“好人”和“持有火种的人”的同时,如何给儿子解释置他人于死地而不顾成了父亲的又一个难题。
面对种种凄凉悲惨的情形,孩子依然天性纯真,他有帮助别人的冲动,他对偷窃他人的食物感到不安。但父亲知道,即使是为活命而战斗,真正使他们的战斗有价值的是孩子善良天性显现的纯真,也正是这种纯真使他抵制住了“诅咒上帝然后去死”这一古老的诱惑。《路》讲述的故事寓意深刻,它要把我们拉向我们不想去的地方,逼迫我们思考我们不想问的问题。任何玩世不恭的人面对麦卡锡的小说,面对父爱的淳朴之美都会陷入沉思。
麦卡锡是悲观主义者,认为所有人都会下地狱。他说他描述的大灾难不会是流星撞击地球造成的,这样的灾难将由我们自己制造。
小说的最后,儿子遇到了一个女婴。终于,绝望的旅行有了意义,人类生命的火种有了延续的希望。他们仍然走在路上,他们仍然时时面临危险。但是,只要他们有面对毁灭而生存下去的勇气,有做好人的信念,人类还有希望。
《时代》杂志评价说:《路》揭开了隐藏在悲伤和恐惧之下的黑色河床,灾难从未如此真实过,科马克·麦卡锡仿佛是这个即将消失于世界的最后幸存者,延续着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文学风格,他把未来发生的那个时刻提早展现给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