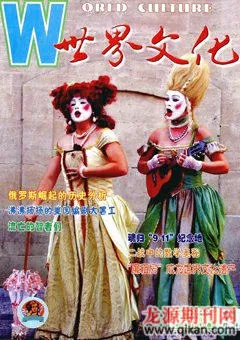卡夫卡与弗洛伊德
卡夫卡(1883~1924)与弗洛伊德(1856~1939)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奥地利人:一个是伟大的作家,一个是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他们是如此相似:都出生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在种族的仇恨和歧视之中,接受的是德语教育,都对探索人类心灵的秘密兴趣浓厚;但他们又是如此的不同:弗洛伊德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他可以并且能够克服一切障碍,他相信理性和意志的力量;卡夫卡则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他相信“每一个障碍都摧毁了我”,他怀疑理性和意志的力量。没有材料证明他们曾经会过面,但有材料证明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曾经受到过弗洛伊德的影响。卡夫卡不经意地成为了弗洛伊德理论的论证材料;弗洛伊德却因为不了解卡夫卡而终成遗憾。两个同时代的伟人擦肩而过,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却意味深长。
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曾经说过,“不可否认,卡夫卡的情况可以作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解释太容易了。事实上,卡夫卡本人对这些理论是非常熟悉的,但并不很重视,只是把它当作事物非常粗略的和近似的图像。他认为这些理论在细节上并不是很恰当的,特别是关于冲突的本质。”卡夫卡在日记中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1912年9月23日,卡夫卡写道:
在22、23日夜间,从晚上10点到清晨6点,我一气呵成写完了《审判》。由于一直坐着,我的腿如此发僵,以至都不能将它们从桌子底下移出来。当故事情节在我面前展开时,我处在极度的紧张和欢乐之中……夜里我多次将批评的重点落在我自己身上……写作期间我的情绪是:高兴,比如说,可以给布罗德的《阿卡狄亚》提供某些优秀的作品,当然也想到了弗洛伊德。
卡夫卡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弗洛伊德,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卡夫卡对弗洛伊德及其理论是比较熟悉的。卡夫卡上大学时有一位专攻心理学的朋友奥托,他后来曾去维也纳跟随弗洛伊德继续研究心理分析,并参加过弗洛伊德组织的“星期三晚间研讨会”。卡夫卡与他的亲密交往,无疑使卡夫卡增加了对弗洛伊德的了解。1899年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创办了《火炬》月刊,他在这份杂志上经常刊登攻击弗洛伊德的文章,而这份杂志卡夫卡是非常熟悉的。卡夫卡当时还听过克劳斯的有关弗洛伊德理论的讲座。1913年,卡夫卡结识了一位朋友,名叫恩斯特·魏斯。他是一位犹太医生,早年在维也纳学医时他便发现了弗洛伊德。他对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有一定影响。
卡夫卡与弗洛伊德的个人身世和经历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比1883年出生的卡夫卡大27岁,死于1939年,比1924年去世的卡夫卡多活了42岁。弗洛伊德生于莫拉维亚一个小镇弗莱堡,以后主要在维也纳受教育和行医;而卡夫卡除了在欧洲有过几次短暂的旅行和逗留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布拉格。这些地方当时都属于奥匈帝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他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卡夫卡的父亲经营纺织品、百货;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个羊毛商,只不过弗洛伊德很小的时候他父亲的生意就败落了。他们都是极端敏感的犹太人,接受德语教育,虽然都精通或熟悉多种语言,但他们的母语都是德语。当时欧洲的排犹主义情绪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但是,他们两人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或挑战这种环境:卡夫卡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封闭起来,越来越深地去探索自己的心灵和人类的灵魂;弗洛伊德则反而更加增强了他的反抗和叛逆情绪,并发愤图强、有所作为。面对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卡夫卡变得越来越内向;弗洛伊德则变得越来越外向。有趣的是,弗洛伊德的外在成功最终却是通过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而获得的。
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似乎给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可惜弗洛伊德并不知道卡夫卡。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卡夫卡大概可以算得上最典型的“弑父娶母”病例了。卡夫卡在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许多年后,我还一直保留着这种惊恐的想象:那个巨大的男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深夜里向我走来,毫无理由地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带到阳台上去──换句话说,这才是他所关心的,而我则是无足轻重的。”在“父子矛盾”中,母亲似乎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在这场争夺母亲的斗争中,卡夫卡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怀恨他父亲,甚至想谋杀他父亲,都应当是十分自然的想法。
更有甚者,年幼的卡夫卡本来就没有获得多少母亲的关爱,而当他的两个弟弟分别在1885年和1887年出生时,卡夫卡对这两个闯来同他争夺母爱的竞争者更是怀有强烈的怨恨。“卡夫卡一定希望他们远离他的生活,并且,在最初的想象中他试图通过魔法将他们谋杀。”事情后来果然按照他的想象发展,他的幻想变成了事实。格奥克1887年春天死于麻疹;亨利希1888年死于中耳炎。卡夫卡在无意中“谋杀”了两个年幼的弟弟。弟弟的死给卡夫卡心灵留下了沉重的负罪感,以致于他从来都没有觉察到,而多年后他在作品中却泄露了他的这份压抑情感,这也许就是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犯罪、赎罪和惩罚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卡夫卡完全有可能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和学说,并将其灌注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去。卡夫卡非常重视梦的意义和作用,他的某些有关梦的观点与弗洛伊德颇有相同之处,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卡夫卡曾经读过弗洛伊德的《释梦》。布罗德认为,“若没有弗洛伊德,卡夫卡也许从来不会对自己的梦给予那么多的注意。”“卡夫卡似乎只对自己的梦感兴趣。”1910年,卡夫卡第一次写日记就记下了自己的梦。以后他在致女友菲莉斯的信中曾数十次谈到梦,他说他几乎天天梦见她。卡夫卡说过,“我们只是以自然性质的无法理解的高速度走过真正的事件之前或者之后经历它们,它们是梦幻般的、仅仅局限于我们心中的虚构。”他说,他的小说《司炉》是“梦呓”,是“闭着眼睛的图像”。另外,在创作中,父子矛盾一直是卡夫卡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卡夫卡曾计划将自己的全部作品命名为“逃离父亲势力范围的愿望”。总之,卡夫卡的所有小说几乎都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分析和阐释。
但是,卡夫卡与弗洛伊德毕竟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弗洛伊德具有英雄气概,卡夫卡更多的却是弱者情怀;弗洛伊德试图对非理性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概括,卡夫卡则更愿意对理性进行非理性的描述和说明;弗洛伊德爱情幸福、婚姻美满、家庭快乐,卡夫卡则爱情失败、没有婚姻、没有家庭;弗洛伊德活着的时候就已看到他的思想和学说风靡世界,而卡夫卡活着时却几乎默默无闻;弗洛伊德活到83岁高龄,有6个子女,卡夫卡则只活了41岁,而且孤身一人。卡夫卡因为肺结核而早逝,弗洛伊德则因为癌症而病逝,“结核病是源自病态的自我的病,而癌症却是源自他者的病”;作为结核病患者的卡夫卡在一点点回归自我,而作为癌症患者的弗洛伊德则在一步步走向世界。特别在信仰和宗教问题上,卡夫卡则坚决地抵制弗洛伊德的理论。卡夫卡反对弗洛伊德的“理性主义”,反对他所坚信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信条,反对将信仰当作疾病来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凡此种种,均说明卡夫卡与弗洛伊德是有距离的,卡夫卡不可能不假思索地选择和接受弗洛伊德,并且,卡夫卡的创作从来都不拘泥于任何理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弗洛伊德的理论。卡夫卡以独特的思想和方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以及他周围的所有作家,当然,他也超越了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