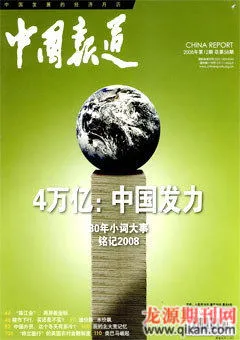我的北大荒记忆
编者按: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这个号召,随后响彻四海,影响至千万人。
196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6年,高考制度被废除,数百万高初中毕业生滞留学校;1967年9月,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组织率先提出要去农村和边疆插队落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被迅速推向高潮。
40多年前的某个初冬,伴随着第一缕照耀大地的温暖阳光,近2000万年轻人就这样陆续离开亲人,离开从小生长的家乡,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而归途未卜。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路径中,“知青”这两个字所代表的丰富内涵,或许少有词语能出其右。在这个群体中,陌生者可以相拥,言谈间便可涕下,回归者总是对曾经劳作过的土地魂牵梦绕,而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扎根异乡的人们,一辈子乡愁无限。
因为一代人的青春,梦想,彷徨与失落,从城市到乡间,一路悉数洒落,捡不起,拾不尽。
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都已年华逝去。年轻时候,陌生而剧烈的劳作方式,让大多数的知青落下了各种病根。不论当年的知青们如今身在何处,是平稳富足,还是依旧在为生活低头折腰,都深深地祝福他们,祝他们安康如意。
他们写就了一段有品格的历史,正直、善良、勤劳、执著,侠肝义胆,大公无私。
这段历史及其主人公们,将始终顶天立地。
“沿着田野,沿着群山,筑起这钢铁的战线,兴安岭南北是我们的战场……”这是属于我们的青春之歌——《兵团战歌》。初中毕业后,因为“文革”,升学停止了,国家的政策是让我们这些人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的秋天,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无知少年就一车皮一车皮地被拉到了遥远的北大荒。
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5年。不能简单地说那段经历是苦难,苦难中也有欢乐。往事并不如烟,时至今日有许多往事,还像刚被拖拉机犁过的土地,发散着泥土的清新气息……
“翻身稻田”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是深夜下的火车,又乘汽车到了营部。营部前黑黢黢的空场上,站着一地的知青(从那天开始,我们的身份就叫知青了),一个声音在点名,叫到名字的人再上车,分赴各自的连队。
我们连队是兵团版图最边缘的一个连队,距离团部50多里地。那真是山高皇帝远,不通长途汽车,看到的报纸还是4天前的。连部有一个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那样的电话机,没有拨号盘,不能先摘话筒,而是得摁住它,把一个摇把“咣咣咣咣”摇上几圈,才能叫通营部的总机,然后再把话筒拿下来放到耳朵上,而嘴要对着一个喇叭讲话。我们知青去了都不会用那种古董话机,没少叫人笑话。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地方,我们了解外部世界就靠听广播。新闻是不太多的,常播的歌曲也就是那么几首。有一首《翻身道情》,不知怎的,传到我们那里就走样了,不仅语音一转变成了“翻身稻田”,还给这个词赋予了新的含义,意思就像是打牌先输后赢,翻本了,那就是“翻身稻田”了。
我虽不是满腔热情写血书报名去农村的,但我也随遇而安,看不到出路,也就不去想它,反正扔在这山旮旯里的也不止我一个,所以心情倒也不焦不躁。但我有一桩苦恼的事儿——不会干农活。站起来个子比谁都高,但干起活来,总是“打狼的”(北大荒人谑称干活落在最后的人。原意是大伙儿一起上路,走在最后的人其实不是笨,而是负有特殊使命——负责打狼)。
我不是不努力,但拼尽力气也胡撸不到前头。我觉得这事很丢脸,我的要求不高,只求在这人堆儿里别显得太差,所以我决定:
去向干得快的人请教。
我虚心学习,认真观摩,总结出人家的步法,记下来。然后就像学舞蹈一样,先迈左脚,再迈右脚……反复练。
结果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也终于名列前茅了。尤其是割豆子,一猫腰噌噌一路往前窜,等到直起身子,回头一看,千军万马都在身后了。心中一种丑小鸭变天鹅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句话:“翻身稻田”了!打草的比基尼少女
我们连地处小兴安岭脚下的丘陵地带,距我们最近的一个连有8里地。其问是杳无人迹的原生态荒原。连队有800垧(1垧=15亩)地,按人头平均,每个人都是大地主。
连里最长的一块地有6里长。铲地(锄草)时,一条垄就够一个人足足铲上一天。在地里四下望去,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到地平线,其间没有村庄,没有人烟。早晨看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晚上看到比太阳还大的月亮也从地平线冒上来;而繁星之夜躺在黑土地上,那星星却是伸手可及……
夏天的时候有一个活儿,是我们爱干的——进山打草。坐上拖拉机拉的爬犁,慢慢吞吞地走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深山之中的草甸子上。那里长着一种一米多高的草,用它打成草帘子,可以用来苫盖粮食。
北大荒的夏天是宜人的,不冷不热,但阳光下干活还是会流汗的。深山草甸子里除了我们几个姑娘,再无别人,有几个胆大的放得开的姐妹,索性脱去了上衣,还不住地撺掇我们:脱了吧,没人看!每逢回想起这些画面,我都会会心一笑,也许在那个年代,她们是在用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释放青春的吧。
草甸上开遍了各色野花,美丽但多是不香的。其间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溪,红色的溪水流向林深不知处。我们干活儿渴了,就喝那因泡着草根而染红的溪水,不时还得拨开蟾蜍的带着薄膜的卵。有一次,突然下雨了,我还没完成自己的定额100捆,一着急被镰刀把手指给割了,至今留下一个刀痕。
“小资”的节日
那时候也有“小资”这个词,不过批判的意味更多一些。我们学校去的人不多,十几个,但几乎都是“家庭有问题”的,父母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有人评价说,我们第三批的(我们是第三批到连的北京知青)干活儿还可以,只是小资味儿较浓。
干农活是没有固定休息日的,只有农闲了才放假休息。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节日,那就是几个要好朋友的生日。那天不论休不休息,我们一定要在收工之后,包上一顿饺子庆贺一番。
到菜园里要一棵圆白菜,开两听红烧肉罐头,用我最好的朋友的脸盆和面,由我出面到老职工家要豆油、到食堂买酱油——不是我面子大,而是我不会干活,找点力所能及的干,吃的时候好不脸红。
饺子之后才是庆典的高潮,那可是小村庄里最排场、最吸引人的节目——放花炮(是我的姐姐从河南干校带回北京,我又从北京带到兵团的)。那真是我们的节日,我们这一伙人簇簇拥拥来到麦场,唱着歌等天黑。
麦场是连里唯一的一块水泥地,夏日的晚上,全连的孩子都爱到这里玩,像鸽子一样在麦场里追逐飞跑。当我们的节目上演,耀眼的烟花腾飞升空时,那一群“鸽子”全部落定,张着嘴眼睛一眨都不眨,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
在那个时代,那真是一种顶级奢侈的娱乐了,我想这也算是我们几位在连里最出风头的事了。
老韦
我们连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汉、满、回、蒙古、朝鲜、鄂伦春族,甚至还有维吾尔族和广西壮族人。
这就要说到兵团的前身——国营农场了。东北解放得早,我们所在的赵光农场是1947年创建的,是全国第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农场职工来源复杂,其中也有一些所谓的“混进革命队伍”的“有问题”的人。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处偏远,便于隐匿吧。
但是“文化革命”来了,他们的“历史问题”也统统被揭发出来了。人们对待这些人的态度有双重标准:对那些人品不好的、不好好劳动的,人们就“亲不亲,阶级分”——坚决斗争,无情打击;而另一种人,他们在兵团的日子倒也并不太难过,只要他好好劳动,人们并不会歧视他,对那些有本事的,人们更是另眼相看。
壮族人“老韦”即是后者。老韦据说是国民党兵,打仗还到过菲律宾呢,有他家里的花洋伞为证。初到北大荒时,老韦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儿,曾只身跟狼搏斗,狼咬了他一口,他剥下一整张狼皮,还因此得了一个“韦大狼”的诨号。
他是属于有“历史问题”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黑帮”,在我们连却身居要职——麦场主任。麦场主任负责组织人员将刚打下来的粮食上场晾晒、入库,待水分达到标准后,送交国家粮库。这项工作专业性强,可以算是半个连长,我敢说,连长也未必能如老韦那样,把麦场的工作安排得那么有条有理,忙而不乱。像他这样专业和敬业的,我们连里,找不出第二个。
夏收季节是兵团最具活力的季节,地里的麦子成熟了,连里的几台联合收割机昼夜不停地在田里收割,3台汽车也穿梭往返于麦场与田地之间,把打下的麦子拉到麦场。往往是这台车刚走,那台车又到了。每到此时,你就会看到老韦大步流星地奔到麦场门口,指挥卸车,这时的老韦,完全不像个“黑帮”,俨然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
因被狼咬了那一口,伤疤阴天下雨就会有反应,老韦便多了一项特异功能——识天气,他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哪片云彩没雨,还知道雨几时几刻到。只要老韦在,你就不用担心晾晒的麦子会被突然而至的雨水淋湿,老韦会在大雨到来之前迅速收场,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老韦是麦场的灵魂人物,也是麦场的“地标性建筑”,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那里。你早晨到麦场,他在那里;打夜班的知青半夜跑回宿舍睡觉了,也是他去敲窗户把人喊起来的。
知青管连里的老职工都叫师傅,但老韦例外,叫他师傅有阶级立场不清之嫌,所以直呼其老韦。有几个顽皮的知青爱跟他逗趣:老韦,听说你去菲律宾打过仗,真的假的?老韦则面无表情不置一词。只有当不自量力的知青小伙儿跟他比试力气,挑战失败的时候,他的脸上才会漾起难得一见的菊花样的笑容。
老韦厚厚的嘴唇,宽宽的鼻子,宽且平的肩膀,步幅很大很快,走路时上身前倾,脚趾从鞋中露了出来。操着一口广式普通话。他从不因为自己是“黑帮”而自卑,也不居功自傲:干活是他应该应分的,功劳跟他无关也是应该应分的。
工作如此繁重,但运动一来,尽管不是“地富反坏右”,在批斗会上,老韦也须敬陪末席,在一边立着——陪斗。每次看到他木然的样子,我脑际中不知怎的总是不恰当地闪现出“大无畏”这个词……
毛主席《到韶山》中有一句: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他老人家一别故乡三十二年才回家。我如今离开北大荒也三十二年又二年了。年年都说,今年回去,也曾几回回梦里回故乡,但终未成行。
明年是我们下乡40周年,是时候该回去看看了,看看我们“战斗”过的林海雪原,那见证了知青爱情故事的白桦林,那里的乡亲,和洒着我们汗水和泪水的黑土地。上山下乡虽然不是我们情愿的,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我仍感谢那段岁月给予我们的磨难和历练,它使我们的性格中多了一份坚韧和隐忍,多了一份善良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