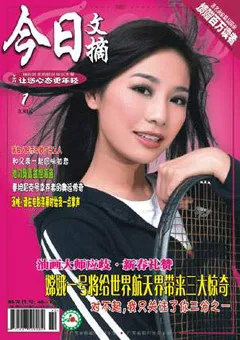在坦桑尼亚用风油精“行贿”
在坦桑尼亚,离我们驻地不远有一个水塘,开车只需半个多小时。那个水塘属于一所监狱,但周围的老百姓也到里面取水做饭。水塘里有许多鲶鱼、乌龟和罗菲鱼,我们每周去这个水塘钓一两次鱼,似乎成了例行的公事。钓上来的鱼新鲜又好吃,红烧、干烧、清蒸、水煮、油炸……变着花样吃,每周吃好几次,真是过瘾。
这样钓鱼、吃鱼有半年的时间,突然就出了“岔子”。原来,我们只知道去钓鱼,却没有到水塘的主人那里去“认认门”。当我们又一次兴冲冲地去钓鱼时,两名狱警很严肃地说,不许我们在水塘里钓鱼了。气氛一时有点儿尴尬,我们不得不说些好话,甚至连中坦友谊之类的“主旋律”都搬了出来。
好说歹说,见那两名狱警似乎有些“松动”,我们不失时机地送给他们一点儿小礼物,比如风油精、清凉油什么的。“拉非克”(斯瓦西里语的“朋友”)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推辞了一下后就“笑纳”了。我们又提出请他们到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喝两杯,这次他们答应得倒挺痛快。
说是酒吧,可除了啤酒、可乐外,居然什么都没有。我们“头儿”让我穿过一条公路,到对面的商店里买点儿东西。我是翻译,自是责无旁贷。没想到,拿着很多钱却买不到什么。我原本打算买点儿炸花生米、香肠什么的,可是非常令人失望,只买到了一点儿油炸土豆片和几块面包。好在“拉非克”们并不计较,就这么喝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几个同事就去钓鱼了,由我陪着“拉非克”们喝酒、聊天。最后,那俩狱警似乎还有话要说,我心中明白,主动告诉他们,我们下周到监狱长的办公室去拜访他。
钓鱼归来,我们把这段经历一说,坦方新换的那个联络官不停地自我批评,一个劲儿地说是他的失误——他还以为他的前任已经带我们去拜访过了呢。于是,没过几天,我们就和坦方的联络官一起,直奔那座监狱而去。
监狱长办公室比较简陋,里面的沙发也有些破旧。监狱长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体形有点儿“夸张”,前凸后翘的,有着好笑的曲线。他表情冷淡,见面就说我们不够礼貌,每周来钓好几次鱼,却从来不打招呼,钓完就走人,就像是在自家园子里钓鱼。我们赶紧道歉,说前一段时间工作非常忙,没能抽出时间来。坦方的联络官又与他说了好一阵子斯瓦西里语。
见监狱长的脸色有些缓和,我们赶紧送上了礼物,不过就是从国内带来的床单、被罩、蚊帐之类。看到礼物,监狱长的脸上立即有了笑意。原来他并不是那么“酷”,笑起来甚至还有些“弥勒佛”的味道呢。他最后允许我们每周来这里钓一次鱼,我们也诚恳地请他到我们的驻地去玩。他欣然答应,一场“外交风波”就这样圆满解决了。
现在仔细想想,人家也不是在乎我们的那点儿礼物,在乎的是我们的诚意。■
(王兴友荐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