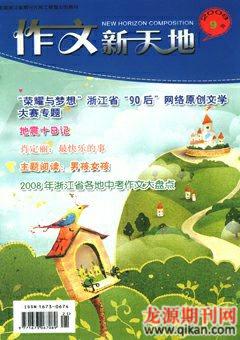雪夜漫步
薛 涛
下面的故事缘于我和雪拉对爱情的不切实际的估价。我们都不谋而合地认为爱情产生的热能足以抵御北方冬夜的寒流。我们坚信给对方一个拥抱足以胜过一件纯毛大衣。我们按计划出发,我想门卫老头一定很不理解眼前这两个走向冰天雪地的孩子。
“这天挺凉快的!”我大声说,是想让他听见。在冬天里说“凉快”本身就是对寒冷的一种蔑视。
“我们一起走一夜吧!”雪拉也大声说。
“对,一整夜!”
我们发誓开创这所学校建校以来的恋爱纪录:为了爱情,来一次雪夜的长途散步。那老头尽可以按学校规定锁上宿舍所有大门切断我们的退路。
我们走在大街上,那是我们相爱以来最彻底最到位最唠叨的一次长谈。我为此热血沸腾。雪拉的脸格外的红,弥漫着一层热气。这女孩挽着我高兴得像夏天草地上的一头小花鹿。我原以为我们的肆无忌惮会引来行人的品头论足,事实上那些行人都把自己裹得像份绝秘文件,只顾踩着分秒瞄着某个方向紧赶。
又过了一段时间,车辆行人似乎都找到了家,这城市的大街变得宽阔无比,路灯闪烁,一派冷色调。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颤了一下,我便感到不妙,我应该永远热血沸腾才对。雪拉则更加拥紧我,后来雪拉不情愿地说,天“凉”多了。我说,没有啊。
我们都不愿意怀疑爱情的巨大御寒作用。
我们在一家餐馆吃掉了两碗热拉面,吃得狼吞虎咽。雪拉多多地喝汤不肯浪费一点点“热量”。这一遭挥霍掉了我们那晚的所有金钱。我们出发是只带了“爱情”,别的都忽略了。
夜在延续……
得说这半夜我们基本上是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度过的,雪拉一个人提供给我的热量,远比我以往18年中所吃的米饭提供的总和还多。
一切变化发生在零点以后。我相信那天的后半夜来了西伯利亚寒流,一下就冲垮了我们用爱情构筑起来的防寒大堤。我们在一个避风的角落拥抱,并夹杂着身体的颤抖。而我们都明白,那不是激动,是寒冷。寒冷像一头猛兽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所措。
我们决定逃向火车站,那里的候车室至少不是露天的。很明显任何守法任何以赚钱为目的的旅行社都不会接纳我们这对既没带身份证又没带钱的疯孩子。
我们死心塌地地躲在候车室里,时而拥抱搓手跺脚,并暗暗咒骂每一个出入不关门的长尾巴家伙,渐渐地我们都没有了谈话的热情。这又让人感到尴尬。雪拉的脸色苍白得像擦了很厚的一层增白霜。余下的夜开始拉长,寒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雪拉缩成一团说,我真想死掉,真想。我于是一阵悲哀,我说我也是,不过为了你,我得活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产生侥幸心理。所以我理解雪拉。我们便开始向学校挪动,幻想着能穿过一道道大门钻回自己的被窝里去。走近校门时我俩变得小心翼翼,远远地能看见校门旁的收发室还亮着灯。
我不小心踢响了一块东西。马上听见小屋里一声咳嗽。
“是你们回来啦?进来。”那个老头的说话声。接着他出来了,手里的钥匙叮叮当当,很诱人的乐曲。
“我早掐算好了。过不了后半夜两点就得逃回来。还想走一夜?傻话。”
“您一直在等我们?我们其实是困了,不是怕冷——”我支吾着。
走进学校了。我回头看见老头儿站在那儿,借着灯光能看见他正瞧着我们狡黠地笑,还笑出了声。他救了我们,他违反了学校的规定,给两个夜不归宿的学生开门,他居然等了大半夜——我的思维开始复苏。
我突然感到冬天又暖和起来了。雪拉也说,怪了,天不冷了。
我就说,那咱们再呆一会儿?雪拉没反对。
我俩站住,一起看着门口那个小屋,直到那儿的灯唰的灭掉了,才感到寒流又来了。
(摘自《与花交谈》,略有改动)
秦俑点评:有的时候,爱的力量很伟大,大到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但有的时候,爱的力量也很渺小,小到甚至抵挡不住一夜寒冷的袭击。想一想,禁止早恋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一条规定。爱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还没有做好抵御寒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