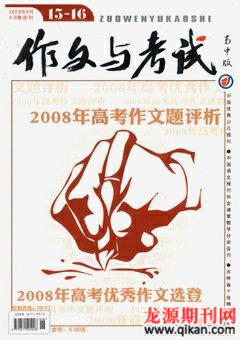食粥记
宗 璞
宗璞(1928—)女,1928年7月生于北京,原名冯钟璞,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
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我们处处可以寻到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艺术深远的、潜在的、溶解性的影响,从而赋予她的文字幽雅、淡泊、洒脱、内省的独特精神风貌。在一片时尚灵动、标新立异的阅读环境中,读一点宗璞的文章,正如她在《食粥记》中所言:“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
从小便多病,以这多病之身居然维持过了花甲,而且还在继续维持下去,也算不简单。六十年代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我也得了一场重病。年代久了,记忆便淡漠,似乎已和旁人平等了。可能是为了提醒吧,前年底,经历了父丧之痛之后,又是一次重病,成了遐迩闻名的大病号。
病中得到广泛而深厚的关心,让我有点飘飘然。有时卧床而"飘",飘着飘着,想起二十年前,我的夫弟--俗称"小叔子"的,他们只有兄弟二人,不必说明第几位--从上海寄了一本《粥疗法》,是本薄薄的旧书,好像还是古籍出版社一类的地方出版的。书中极称粥食之妙,还介绍了许多食粥之法。有的很普通,如山药粥、百合粥、莲子粥等,不必查书,我也曾奉食老父。有用肉类制作的,就比较复杂。无论繁简,都注明各有所治,"粥效"可谓大焉。不过此书的命运同我家多数小册子一样,在乃兄的管理下,不久就不见踪影,又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
后来又听朋友说,还有一种书,题名为《一百种粥》,所记粥事甚详。可见"粥"在出版界颇不寂寞。
病中不能出门,只在房中行走。体力恢复到能东翻西翻时,偶见陆游有一首食粥诗,"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再一研究,写《宛丘集》的张耒,更有一篇《粥记》,文字不长,兹录如下:
张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每将旦一粥,甚是厉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道,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
这位张耒是自称"吾苏学士徒也"的,如此再作推理,原来东坡也嗜粥。他说:
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
看来宋代便有不少大名士深知粥理。想想我曾那样不重视粥疗,不觉自叹所知太少。
南方人似乎喜吃泡饭胜于粥。幼时在昆明,一度住在梅家,曾和小弟还有从小到大的友伴和同窗梅祖芬三人一起偷吃剩饭。那天的饭是用云南特产的一种香稻做的,用开水泡一下,还有什么人送来自制的腐乳,我们每人都吃了两三碗,直吃到再也咽不下,终于胃痛得起不了床。梅伯母不知缘故,见三人一起不适,甚感惊慌。好在服用酵母片后,个个痊愈。梅伯母现已年近百岁,对于一起胃痛的奥妙,还是不甚了然。当时若吃的不是泡饭而是粥,谅不至于胃痛。
一九五九年下放在桑干河畔,那里习惯用玉米匙又蟾煞梗称为"格仁粥",煮成稀饭,则称"格仁稀粥"。我印象中稀粥比名为粥的干饭容易下咽多了。房东大娘把炒过的玉米、小米和豆类碾碎,煮成粥状,也笼统称为粥。下放回来后,大娘还托人带来一小口袋这种粥的原料,试者无不说好。但若吃久了,这些粥都比不上白米粥。只是大米在北方农村不多,米粥也就难得了。
有一阵子以为广东粥很好。记得那年夜游洛杉矶,午夜到一小吃店吃鱼片粥。只那端上来时的热气腾腾便赶走一半夜寒。碗中隐约现出嫩绿的葱花,浅黄的花生碎粒,略一搅动,翻起雪白的鱼片,喝下去不只暖适而且美味。回来每每念及"广东粥",或外购或内制,总到不了那个水平。这也许和当时的身体情况以及环境有关。
陆游还有一首诗云:"粥香可爱贫方觉,睡味无穷老始知。要识放翁真受用,大冠长剑只成痴。"食粥的根本道理在于自甘淡泊。淡泊才能养生。身体上精神上都一样。所以鱼呀肉的花样粥,总不如白米粥为好。白米粥必须用好米,籼米绝熬不出那香味来。而且必须黏润适度,过稠过稀都不行。还要有适当的小菜佐粥。小菜因人而异。贾母点的是炸野鸡块子,"咸浸浸的好下稀饭"。我则以为用少加香油白糖的桂林腐乳,或以落花生去壳衣,蘸好酱油和粥而食,天下至味。
不知当初东坡食白粥,用的什么小菜。
(原载《收获》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