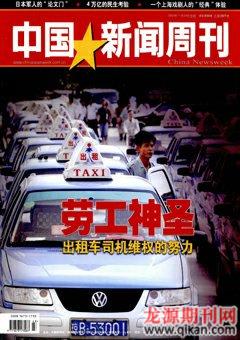张永和:很多传统,我们没有很好地关心它
河 西
作为著名建筑大师张开济之子,他却自言“学建筑只是偶然”;他教的设计,却带着学生盖房子;他受到的教育,以西方的文化为多,却对中国年轻人惧怕传统,觉得特别遗憾。
他充满矛盾,却立场坚定
对于中国建筑来说,张永和这名字代表着一种趣味、一种立场、一种前卫性。
他在北京的工作室叫“非常建筑”,2002年以前的几年里,张永和带着一帮学生,在北大未名湖边的一个四合院里,像真正的建筑匠人那样造房子,同时在外面做设计项目。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建筑工作室,全国仅此一家。
当山语间、竹化城市、晨兴数学中心、席殊书屋、分成两半的房子(二分宅)为他赢得声誉,一个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明星张永和、一个经常出现在展览中的艺术家张永和和一个踏踏实实进行建筑工程的张永和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981年,张永和自费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保尔州立大学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分别取得环境设计理学士和建筑硕士学位。1985年开始相继在美国保尔州立大学、密执安大学、伯克利加大和莱斯大学教书。1989年成为美国注册建筑师。其间曾在一系列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
自1993年起,与鲁力佳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并开始在国内的实践。1996年底正式辞去美国莱斯大学教职,回国。
在中国建筑界,张永和比一般的先锋建筑师要主流些,但仍在主流的边缘。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学习建筑的留学生,著名城市建筑研究评论家史建说他“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人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及其意义,以此来体察人们的活动与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不过,对于艺术批评家对他“一杆翠竹打天下”的论断,他显得不屑一顾。
2008年,由于颇具争议的SOHO中国前门项目和刚结束的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工作,张永和又一次进入了中国公众的视线中。
全世界都有人在用竹子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那么喜欢竹子?
张永和:我发现竹子有三个特性。第一,它的根系是一个串的系统,所以不能一棵一棵种。我在北京发现,竹子的根系将老房子的基础破坏,所以要种在一个竹槽里,竹子有放射状和线性两种生长的根系,北京普遍是线性的,在地下埋一个水泥槽子,这样竹子的根就不会乱长,我特别受这个的启发。
第二,平时看一棵树,树冠多大,树根就多大,可是有两种植物,一个是竹子,一个是芭蕉类的植物,根系特别小。你移植一根竹子,三十厘米一个土疙瘩团就可以了。
第三是竹子的生长期特别短,所以从材料来说现在也是全世界研究的绿色材料。因此,我就想一种植物可以在城市里长成一个系统,而且可以长在建筑上面(棕榈也可以,我们在成都的建筑屋顶就种了棕榈)。竹子是草,可是它有乔木的高度。
中国新闻周刊:有建筑评论家对你的竹子符号提出了“一杆翠竹打天下”的批评,你怎么看?
张永和:我对建筑以外的意义并不太感兴趣,并不是说它没有,只是我觉得这不是我工作的重点。王南溟(现代书法创作和当代艺术评论、策划)说我“一杆翠竹打天下”,那完全是胡说了。
一个建筑师要干很多工作,盖起房子,哪那么简单?竹化城市反映的是对城市环境的關注。王南溟对这个事件是不是有一些误解?我当时也许应该多做一些解释,但是恐怕也会造成更多的误解。
文化的意义当然存在,人们看《卧虎藏龙》中的竹林,就会觉得这是中国的符号。可是竹子与建筑关系的研究中国其实是很落后的,最先进的是南美的哥伦比亚,当然这和南美竹子长得好有关。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筑师用竹子来做结构建房子的国家,当然那和竹化城市又完全不同,他们是把竹子作为建材来研究。欧洲对此也有很好的研究。其实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在用竹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分成两半的房子”(二分宅)这个项目是否受到什么启发吗?
张永和:我那个名字反映的是建筑的一个基本状态。
建筑界的朋友经常批评我太理性,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思维的人。我对院子感兴趣,我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出生长大,那种感情是专业知识不太能取代的,那是我的第一个建筑经验。一直延续到13岁。后来,我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超)过十三年。
所以我把它作为北京的一个住宅原型,一开始做了一个方案,但觉得拿到山沟里不合适。四合院是内向的、都市的,而山里有风景。后来做了很久才做出这样一个方案:山坡成了我的院子的围墙,把分成两半的这个房子围着,这样就把基地上的树全留下了。而建筑变成了一个“splited”(分开)的房子,室内的设计也体现了这个“分”,如果把它们合起来,你会发现,楼梯就会合成一体,(名字)就这样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设计首先考虑的还是基地的环境情况?
张永和:对。有些建筑师,像彼得·艾森曼,一开口就是形而上的哲学,实际上做的时候,每件事情都要考虑实际,才能把建筑造好。
大家都需要有沟通的诚意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的泉州“小当代美术馆”到这个“分成两半的城市”,你还是很注重建筑传统和文脉?
张永和:这和我的经历有关。我接触到的东西以西方的为多,音乐、油画、小说都是如此,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起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真是差太远了,我对西方当代艺术比较熟。
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特别遗憾,发现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真的不同,每个美国人老想的是自己如何和别人不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日本,发现他们真的能将最现代的观念和传统的形式并存在一起,特别有意思。
回国后我发现许多年轻人怕传统,这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还是应该去理解传统,当然我不是说完全拿来,还是要理解它。很多传统并没有那么快的消亡,可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关心它。
中国新闻周刊:青年建筑师大展的时候,萧默(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提出来说有些设计他看不懂之类,你觉得是否中国一些老的建筑师太保守了?
张永和:老的建筑师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我们是这个时代的见证。
我说的对传统的关注、关心,和尊重他们这一代人的想法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不同代之间的建筑师也很少有交流。看不懂看得懂这事,我也有一个经验,我写过一本书叫《作文本》,出版后一片骂声,说看不懂,说我故弄玄虚。可能中国和美国相比有更多的不信任。
不过有一次,碰到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老师让他看的《作文本》,他看了以后觉得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如何用文字来搭一篇文章,它是非常精确的。
大家都需要有沟通的诚意,反过来说,我们对那些老先生恐怕也没有很好的沟通。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你是个特别理性的人,怎么也喜欢文学呢?
张永和:我喜欢的文学范围特别窄,我喜欢的艺术也特别窄。我不太习惯表达感情的演出,像诗歌、跳舞,我都有点吃不消。
我喜欢的其实都是很冷静的作品,比如罗伯·格里耶的《嫉妒》,这部小说完全是设计出来的,挺枯燥,可是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把小说搭起来的。所以我喜欢侦探小说,恐怖小说我就完全看不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9月你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至今三年了,你觉得中美之间的建筑教育差异大不大?张永和:差异不算大,中国和欧洲的差异大。中国的建筑教育基本上是一个美术教育,这20年受到许多思潮的影响,但是又没有系统理清这些思想,就变成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美国少一点混乱。特别是东岸那些所谓的大学校,一般都是从理论到实践,中国还没那么清晰的认识。
但是我恰恰不认同的就是从理论到实践,我觉得就直接造成了美国建筑好房子少的情况,也造成了建筑这行业脱离社会的事实。中国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有些学生鄙视建筑的物质性,他不关心房子怎么造,认为这是工匠应该关心的问题。
美国文化和中国不一样,我去了以后就提出“从实践到实践”。第一个实践是建筑的核心知识,基本怎么盖一个房子,这样的基础知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都不好好教,所以建筑系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常常不会盖房子。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都市建设过程中,你对中国当代建筑和建筑师有什么评价?
张永和:就中国的建筑来说,从质量来说已经提高很多了,和质量一般的荷兰建筑比,我们差不太多。
但是就思维方式来说,有些中国建筑师的确有点狭隘。我不是指那批根本没有想法没有抱负的建筑师,而是指在中国的建筑体制下(以留美为主)的建筑师恰恰限于一种形式主题的出发点。尽管我觉得很多建筑师做得也不错,可是我看不到太多持续发展的可能。不管是它与外国建筑像不像,至少思维方式里缺乏独立的思考。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