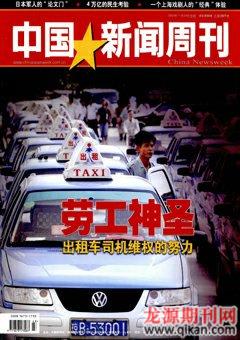我还活着,但已被拆散了
秦 轩
上海市的历史很短,但作为中国的现代城市,它的历史也许最长。保存和展现这个城市历史记忆的博物馆,随同上海的拆迁而不断沉浮,自己的历史反而一直被别人攥着
我叫上海历史博物馆,我还活着,为了保存和展现上海的历史。你可能很久没听过我的消息,也可能根本没意识到我的存在。
这8年,我被拆散了,我的宝贝文物大都存在上海郊外的文物仓库里,我的办公室在延安西路最西头的一栋商务写字楼里,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文物展厅。

也许我的苦日子要熬到头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要来上海,所有“博”字头的都跟着沾光。上面有人认为,这么个大都市,应该有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博物馆。所以,我的人马在2008年8月搬到工部局2楼,还在办公室门上贴了“新馆筹建处”字样。
有个事得说清楚,东方明珠电视塔下面那个上海市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不是我。那是我最伤心的一段往事,想起来就心碎。
是的,那个馆不错,录像、蜡像、模型都用上了。可那更像电影棚,而不是博物馆。如果说那个陈列馆就是我,那在我们博物馆家族里,会是多没面子的事。我的宝贝摆在那里的还不到一半。
虽然拆散了,但我还活着,还在悄悄地保存上海的历史和现实。上海体育馆外那个高9.99m的《千禧龙塔》雕塑,就是我的杰作。那个雕塑里封存着关于你们的信息,还有一些孩子写给未来的信。50年后,人们会打开那个雕塑,通过那里面的光盘、资料来了解你们。不过我也发愁,这几年上海变化太快,要收集的东西太多。
这些东西现在不收集,过几十年就很难再找。可是,当哪天上海第一条地铁的第一辆机车退役,我该怎么办?放到仓库里?
等等,你可能有点听糊涂了。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一江隔断上海的历史记忆
我出生于1986年,在博物馆的家族中,我属于方志博物馆,是专门收集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历史的。在我这儿,你们能看到1865年就进入上海的汇丰银行那两个大铜狮子。这是原件,在香港汇丰银行门口那两只是它俩的复制品。在我这儿你们能看到100年前上海的纺织机车和清理棉花的清花机。我还能告诉你们,上海的历史可以上溯6000年,比上下五千年还多1000年。知道么,考古史上有两个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一个叫崧泽文化,一个叫马桥文化。
嘿,不要说上海博物馆,南京路旁人民广场上的那个大块头可不是我。原保管部的工作人员段炼至今还记得,当年66路公交车的乘务员,一到人民广场就说上海历史博物馆到了。
上海博物馆是艺术品博物馆。它的确很大,工作人员有400多,差不多是我的10倍。可是,你要想找上海的历史,就得找我。
好多人都不太记得我,也难怪。今天的上海和100年前的上海都一样,是一个移民城市。上海今天的年轻人每天坐地铁上班,吃快餐。有时看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或者看看画展,或者,去购物。如果要看历史,他们可以开一两小时的车去杭州,或者再远点去南京。到了那个地方,他们才想到“看历史”。
上海有什么历史?许文强?杜月笙?还是中共一大会址?他们去衡山路都是去泡妞,去蹦迪,哪里会去问那些洋楼和教堂背后的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记者找我,找上海的历史,找得好辛苦,穿过座座高楼,来到离黄浦江边中山南路董家渡不远的江陰街。一位妇女一掀门帘,旗袍下的大腿也露出来了。水池子在门外,灶台在屋里。时近中午,她开始准备做饭,两个孩子跟着她出来进去地转。旗袍是藏红花色的,上面有碗口大的黄花图案。若在解放前的公共租界,这套旗袍也算惹眼。而现在,淮海路、南京路上,见不到这种旗袍了。
房子分两层,窗户、门都是木制,楼上看起来很矮。一条街的房子连在一起。斜对过儿是个里弄,拱形的门洞旁写着大大的“拆”字。门口坐着几个乘凉的老头,穿着睡裤,摇着扇子。
东、西、南面被高楼围着,都是在住户的眼皮底下盖起来的。北面是城隍庙,被改成仿古式的商品街,卖牛骨梳子、古玩玉器之类的玩意,和老北京的前门大栅栏差不多。有时,收垃圾的把车横在中间,过往的车就堵在那里。
说不准过些日子,这条街也会被拆掉。在市中心人民广场的城市发展规划馆里,这片土地上已竖起现代化高楼。而现在这里还是密密麻麻的青苔。从90年代至今,这样的老街,大多像青苔一样从土地上抹去了。
董家渡是黄浦江上3个渡口中最靠南的,一般游客不知道这个地方。每15分钟有一班渡轮过浦东去,7角一位,若带自行车或摩托车要1元3角。
江这边是老上海,有城隍庙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有市井木屋外乘凉或穿旗袍下厨的百姓,有欧式洋房、南京路、外滩,还有教堂。对岸是浦东新区,有国际贸易大厦、东方明珠、4车道的大马路。上海所有的历史记忆都在黄浦江的西岸。
以往,黄浦江是租界的边界,江对岸是乡下。90年代初,政府决心开发浦东,十几年过去,浦东早已超越外滩,成为上海的新标识。维基百科中文版的上海条目,用的头图就是浦东建筑群。
呵呵,我又打岔了。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故事上吧。
我的父亲去世20年后,我才诞生
历史博物馆退休的学者薛理勇说我的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上海通志馆。负责人是当时著名的南社领袖柳亚子。1843年上海开埠,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殖民地。1854年太平天国打过来,清政府不管事,洋人就自己成立工部局。以后租界势力一直扩张,终于成了十里洋场。我父亲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段历史整理清楚。
原保管部工作人员段炼说我还有一个父亲,那就是解放前的上海市博物馆。我的宝贝有很多来自那里,还有一些是来自考古新发现。
解放后,我的父亲上海通志馆也换了身份。当时博物馆界向苏联看齐,1956年,我的父亲也起了一个很苏式的名字,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他还把他最宝贵的政治方面的资料统统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我的父亲命不好,改名不到1年,就被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取消了。
我的父亲去世20年,我才诞生。当然,这在你们人类是不可能的事情。父亲留下了搜集上海历史记忆的种子,“文革”以后,才得以孵化成型。这一切要拜上海市文化局当时的副局长方行所赐。有人说如果不是他那么热心,我可能就不会存在。
方老自上海解放就在文化局当副局长,分管我们文博这摊子事。他那时候应该和我父亲很熟。
老爷子经历很传奇,解放前是老上海的地下党。上海出来的张春桥在延安办报的时候,他在上海办报,还开过药品公司为新四军提供药品。这样的人按说解放后都当大官了,但是方行却一直在文化局搞文博书画。“文革”他受到迫害,一出狱,就去文化局,问明代末年版拱花木刻彩印的画集《萝轩变古笺谱》有没有被毁。
1981年,方老向上面打报告,申请成立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就是我。当时他给我想了两个名称,一个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一个是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他还请陆定一给我题了馆名,听说他俩私交不错。1983年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一批本科生,分配到我这儿。听上海文博界泰斗汪庆正说,这也是在方行的坚持下安排的。
经过三四年的筹备,1986年,我正式对外开放了。不过那时我的名字是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大概他们觉得我还不够成熟。
我借用的是西郊的农业展览馆的地盘。农业展览馆也是个大家伙,他把原来陈列拖拉机的第五馆分出来给我。面积不大,只有800多平米。不过坦白地说,那时我收集上来的好文物也不多。能有个窝就不错。
回想起来,刚开始的日子还是很风光的。去博物馆是当时年轻人一件很时髦的事情。那时西郊还有个公园,一到春天,去那里郊游的人,都坐57路车先到我这儿转一圈。我还是上海市青年轮训的基地,经常人满为患。
当时该馆弄了张霓虹地图。上海租界地域的几次变迁通过不同颜色灯光的依次闪现来体现,这在今天很土,但在20多年前是新鲜事。每次那里都会围很多人。
那地方在当时还是太偏僻,周围都是稻田,上海人会过来逮蛐蛐。
1996年农展馆翻修扩建,更名为国际农业展览中心,和紧挨着的五星级大酒店——万豪虹桥大酒店浑然一体。大约3年前,农展馆对面开了一排小饭馆,饭馆的老板们可不知道我的故事。
这时我已经鸟枪换炮。我,成年了
1992年,我搬到虹桥路1286号,离市区比原来近了两站地。这里是宋庆龄陵园的东北角。我租了陵园的一个大仓库。仓库改造成两层的展馆,一层是临时展区,二层是藏室展区。总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当时的租期为10年。
不过这地方也不全是我的。一层有500平方米的展区属于上海市博物馆的钱币馆。后来人民广场上的新馆建好,他就搬过去了。
这时我已经鸟枪换炮,收藏有从远古到近代的文物近3万件。此前一年,我已正式挂上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牌子。我,成年了。
有个家真好。我在那儿过了10年,我的伙计们跟着我奋斗了10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我的藏品越来越丰富。我有旗袍、杂货、瓷器、顾绣、黄包车,还弄来了铜炮。
1994年,我推出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历史陈列》的基本陈列展。它按照历史顺序,列了六大块,第一部分是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第二部分是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市政建设,第三部分是日渐近代化的城市经济,第四部分是开风气之先的近代文化,第五部分是新旧并存的社会生活,第六部分是风云激荡的政治舞台。
这可是我的看家法宝。
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史越来越受关注,这可不是我说的。1999年出版的大部头《上海通史》总序上说,当时关于上海史的讨论会几乎无年无之,有关上海史的西文专著如雨后春筍。英语世界最权威的亚洲研究刊物《亚洲研究季刊》,在1995年特辟上海史研究专号。
后来,上海史专家熊月之在《上海学评议》中也说,每个城市,无论历史长短、规模大小、市容美丑,都有独特的价值。每个城市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自恋情结,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自己、美化自己、强调自己、夸大自己,在情理之中。但是,现在的情况,如同《海外上海学》一书所展示的,上海史早已越出上海,走出国界,成为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学者、那么长时期共同关注的课题。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得说,一个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应该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在这种背景下,我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光1998年1年,我就办过12个展览,画画的,钱币的,都有。那时候我们还请上海最好的一批油画家,画上海历史的油画。
一切都被改变了。我经历了一场梦
宋庆龄陵园仓库的租期2002年将到期。借这个契机,我很想换个更大的、离市区更近的房子。要知道,我们每次办展览打广告,都会有人跑到人民广场去找上海市博物馆。有几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替我呼吁过几次,居然很快有了效果。
市里领导提供了两个地方,一个在上海市体育馆,一个在东方明珠电视塔。我最终选择了东方明珠电视塔。
2000年2月29日,我在虹桥路的家宣布关门,看门的老头还以为我经营不下去,倒闭了。当时大队人马派到东方明珠电视塔去布置新家。
但是,一切都被改变了。我经历了一场梦。
我的陈列部前工作人员记得,刚搬去那阵,每周都开会。陈列部想怎么安排展厅,把上万平方米空间填满。保管部设了临时仓库,每次拿文物出来摆效果,摆完还得归档。坦率说,我这里确实缺少博物馆陈列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了学习经验,陈列部的人还去日本和澳门考察过。
那时,大家很想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干了大约1年多,新家总算布置差不多了。新馆定于2001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2周年纪念日对外开放。开幕式的票已经赠了一部分出去。
开馆前夕,市里分管文化的领导来视察。当晚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80%的内容不够让群众喜闻乐见,没有做到场景化,得推倒重来。
紧接着上面成立了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有限公司,挂在东方明珠集团下面。
没几日,上海电影厂的人来参与布展。我的人告诉他们要按什么样的观念做,他们负责让陈列的效果更喜闻乐见。表面上看,最终合作的效果是不错的,最后还拿了当年一个全国文博系统的陈列效果奖。
这个馆建好和我没太大关系,从那以后,多年收集的那些文物,我能瞒就瞒,瞒不过去的就要求放复制品,实在太有名的东西,我们也得交出去。
比如汇丰银行的铜狮子是最早运到临时库房的文物之一,这两个狮子是汇丰银行的看门狮,见证银行和外滩的历史,意义重大。但是,在东方明珠陈列馆里只陈列了一只。你要不仔细看,还不见得找得到它。
另一只至今放在周浦文物基地的库房里。它俩当年在外滩、在虹桥路都在一起,威风凛凛,而今也落得个两地分居。有一年钱币博物馆借了一只到香港去展出,人们都不知道这个其实是历史博物馆的宝贝。
上影厂的摆设观念和我也有分歧。他们道具组那几个老先生对老上海倒是颇有研究,但是搞电影的,先天考虑的不是文物价值,而是美观。有一次,上海电影厂要把一只瓷碗放到“酒店”展区,理由是它很漂亮。而这只碗上印着“永安公司”字样。对于历史博物馆的人来说,这只碗和永安公司的历史记忆相连。这家公司于1918年在南京路成立,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
这种争执时有发生,甚至在撤离的时候也发生。那天保管部工作人员看到2楼墙角靠着一块三角型的石头,是一块租界的界碑。那块界碑好沉啊。他找了两个工人好不容易抬下楼,刚要抬上车,电影厂的人追上去,说这是场景的一部分。两边人吵起来。电影厂的人去找领导。我们这边的领导说,算了,顾全大局吧。
他们说,有一天会还一个家给我
2002年,我从东方明珠电视塔撤了出来。保管部和陈列部留了几个人在,其他人去延安西路最西头的一座商务写字楼办公。文物拉到上海文博管理委员会统一的周浦文物基地仓库。
我的编制也改变了。没有展厅,不需要讲解员,撤销了宣教部。原先的陈列部分成陈列部和研究部,保管部变成征集保管部,加大了研究和征集工作的力度。我的领导,文物管理委员会还把我的员工全部请去吃安抚饭。他们说,有一天会还一个家给我。
我一直等了6年。这6年我没闲着,有时在鲁迅纪念馆,有时在文化馆或者图书馆办办展览。比较有影响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摄影展,在鲁迅纪念馆。有些很不错的馆员也离我而去,不过好在他们大多还在搞上海史研究,让我欣慰。
让我感到内疚的是潘馆长。他从1983年我开始被孵化那天就陪着我,一直到2004年退休。21年,他的同学大都功成名就,都是我拖累了他。
不说了,凑合着活吧,总比彻底消失强。
感谢世博会,上面似乎有了新的安排。吃了那么大亏,我现在可谨慎了。新家到底在哪儿,据说还没有敲定。又有小道消息说,想帮我的那个领导又调走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筹备会已经建起来,而且在工部局办公,我收藏的字帖、手稿什么的也搬过来了。现在似乎是个很微妙的时刻。《中国新闻周刊》有个记者想见我,都被办公室的人婉拒了。
瞧,就是这样,我的命运一直在别人手里攥着。有什么法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