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过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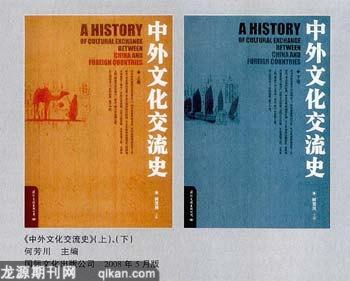
永远的接力棒
何芳川
时光倒流,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
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读书,周一良老师突然来访。我一阵惶恐、忙乱,一良师依旧是一片淡定的笑容。听了来意,方知这一次老师的“下访”,是来约稿的。原来,“文革”之前,一良师曾在周扬同志的领导和关切下,主持过世界史教材的编撰。那时,周扬同志即有意请一良帅再组织编写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未几而“文革”爆发,一切无从谈起。待到尘埃落定,一良师秉承我中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优良传统,不顾已逾七十的高龄,毅然放下手边的研究,决定偿还这笔自己心中的“文债”。其实,那本来无“债”可言,但对一良师来说,却是一种君子的承诺,一份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
蒙恩师青眼,自然受宠若惊。于是一诺无辞,努力从事,终于敷衍成篇,与众多师辈及学长共襄盛举。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这样问世了。在我国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它无疑是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专著性质的成果。
时光竟不能倒流。
转眼之间,近二十年过去,我们迈人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2004年早秋时节,周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责任编辑鲁锦寰先生陪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杨华女士来访,希望我出面将该书修订再版,或者重新组织再编撰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
两个选项中,我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当年的作者中,有几位已经仙逝;有几位年届耄耋,还有的远赴边陲乃至海外。小子何能,岂敢贸然“修订”?!于是仿效一良师当年,重新邀约了一些学兄学弟,撰写一部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新邀的这些朋友,多是一个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自然百忙。蒙大家慨然允诺,纷纷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专为本书贡献佳篇,令我由衷感动。
这部新撰《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一良师主编的那一部书,是传承关系。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学术研究、薪火相传,有如接力赛跑。一良师一辈师长的学术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还会一棒一棒地传下去,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
薪火相传,接棒疾行,是我们的义务;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更是我们的责任。这部新撰的文化交流史,与一良师主持的那一部比较起来,我们在下列几个方面努力作了一些改进:
首先,增加了“导论”一章。就文明、文化与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尝试着做一些归纳、梳理工作,并力求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其次,增加了纵向历史勾勒的几章,就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尝试着作一个纵向的勾勒。勾勒的范围,从两汉到明清,限于古代。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未能予以勾勒,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加之本人学浅,未敢贸然从事,只能期诸未来。
第三,各章的安排,不再按国名汉语拼音字母先后排序,因为那样容易显得杂乱无章。这次依地区排列,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而西亚、非洲,然后则是欧洲、美洲,由近及远,大致符合我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先后序列。每个地区数国再组成一篇,力求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上所述,各位作者均尽心竭力,贡献了佳作。大致而言,与先后召开的三次编撰工作会议所定下的宗旨也还是相符或相近的。由于每位作者的学术背景与研究领域的不同,所撰写的内容也就不尽相同:有的从古到今,比较全面、系统;有的侧重于文化的某一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有的着眼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有的则侧重于这一双向互动中的某一单向。对于读者而言,在求得系统认知时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不过,由于这些侧重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的文字多是作者们的强项,因而读者对问题的深度上的了解或许有更多的受益。
文化交流的历史图象,是极难把握的。
首先,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就始终处在发展这一动态上。这一动态的难以把握,在于它的多样性。在众多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中,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依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而彼此有别的众多发展频道:有的快速发展,很早就达到过某一时代的巅峰,而后迅速滑落向无边暗夜;有的曾经存在,踪迹鲜明,却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而“蒸发”;有的屡屡历经挫折、迂回甚至倒退,却百折不回,千年一脉,不断再造辉煌;有的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浮;还有的后来居上,等等。这种动态的多样性,造成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性现象,也给文化交流制作了基本背景。
其次,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都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是一种立体网络式的结构。正因为如此,诸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是立体网络式的。如果对它们仅仅作平面式的认知与理解,人们笔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苍白的,远远不能表现其错综复杂的无比璀璨。按照常规,我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的(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大的范畴,同时要知道它还有众多的、层出不穷的专门范畴。当文明之间发生碰撞,文化之间发生接触,这不同的三大范畴与众多专门范畴的内涵之间,必然发生的交流,显然也呈立体网络状。如果再向纵深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时候,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换的物质(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着丰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间碰撞,其交流的内涵中,亦包含着对物质(器物)文化赖以产生的不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与理解。
第三,它是双向与多向的,而非单向的。在讨论文化交流时,人们一般都注意到它的双向互动。这一认知,比较起那种单向认知的片面性、偏执性、主观性来,自然是大进了一步。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时期,不同文明与文化相遇的时候,其中某一种处在发展较高阶段的文明与文化,可能对另一文化呈高屋建瓴式的倾斜式“文化出超”。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上述這种双向运动时,就会发现,除了上古时期人类社会处在低级的原始的发展状态因而可能发生比较纯粹的双向运动以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典时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双向互动中,早已包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至更多种文化内涵,因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其实也是一种多向性互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化交流的立体网络模式。
第四,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时,其璀璨辉煌的物质文化出超现象常常令人眼花缭乱。当人们集中注视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现象时,其实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事物往往被掩盖了。发掘并探究这些容易被掩盖的比较陌生的领域,尤具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制度、精神层面,中华民族似乎并非出超大户,相反,却有“文化入超”大户之嫌。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兰教文明流入中华,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国境内一度“寺满百城”,而中国的儒家学说流播的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来新加坡与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又如,即使在物质文化层面,比较起丝绸、瓷器与四大发明这些高级复杂劳动的产品来,在那些比较简单劳动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华民族恐怕也处于“文化入超”之列吧。
文化交流史的学研、撰写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这场任重道远的接力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一良师主编、各位师辈学长共同合作的那部专书,就是我们接力赛的前面一棒;我们接过这一棒,努力疾跑,尽自己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这一棒的得失,自本书问世之日起,就已经要请下一棒去评说了。我深信不疑的是,这一永远的接力赛,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那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真实。
(本文是作者为该书撰写的卷首语,本刊略有删改。作者已于2006年6月病故,生前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