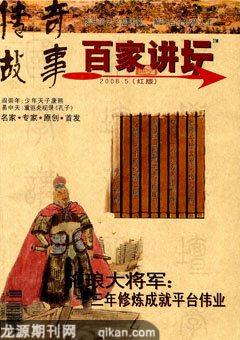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上)
吴 思
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有着这样一段话:“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意(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啉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这里描绘了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那么,这多余的五六个人及其所属的集团叫什么名字呢?
现代汉语称这五六个人为“超编人员”,古汉语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作“冗员”。事实上,描述这个集团的文字并不少见,也有不同的学名和诨名流传下来,例如“传奉”、“小书”、“白书”、“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白役”等等,其中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或不领工资而做官事,这就是白役,《汉语大词典》将之定义为“编外差役”。
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自书”单指编外书吏,见于清代四川巴县档案,“白役”一词流行稍广,却偏指差役。这两个词中都没带官员的位置,很不尊重领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不妨依据“白役”和“白书”的造词法,生造它一个“白员”,用以统称白役和编制外官吏。
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一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屡战屡败。
一、朱元璋的发现
明朝的并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县,时辖上海县和华亭县)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穷追根由,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竟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竟拿着官府批文,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这样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现在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看来,同一正吏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四川巴县的正吏(典吏)不过15名,一等临时工(半正式工)“经书”常有200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其人数与师傅相近。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20位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这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也竟是正员的3倍。
二、赶尽杀绝
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下旨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又下令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籍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管干、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徙;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但朱元璋竞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大诰续编·吏卒额榜》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洪武十八年的20锭等于100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八九千元人民币。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其地位相当于“严打”时期的暂行法规,发行全国。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把这种局面比喻为一盘棋,那么,延续千年的棋局上出现了朱元璋的新杀招。除了皇帝之外,对局者还有白员集团、百姓和官吏集团,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三、对局者的利害计算
知道了在衙门“钻营滥充”的法律风险,还应该理解钻营的实际好处。
《儒林外史》开篇就写到几位衙役,百姓尊称其为“老爹”,能和他们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荣。他们的真实收入,可参照《儒林外史》
第二回中对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绍:“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
这一回中还说到教书先生每年的馆金不过12两银子,与此对照之下,李老爹一年的进项顶教书先生的83年。这并非特例,据统计,清朝四川巴县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过1000两白银,巴县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1000两左右。按说,三班衙役的名义收入从六七两到12两不等,未必比得上教书先生,但他们有机会捞外快。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负责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来自役,却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员李榕曾经给父母官写信,详细地描绘差役(白役)是如何谋生的,信中说:“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英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入其中,横架大题,动轭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
这段文字介绍了三种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饭(无论有事无事,工作餐已经有着落了);二、市镇街道的首脑们支给的盘费(这是比较有保证的日常现金收入),三、讹诈酗酒、赌博和偷鸡摸狗者(除了抓赌外,其他轻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恰当,也可能出一笔小财)。
由此可见,凭借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温饱和小康之间。
有机会捞外快之外,差役还有权力合法伤害他人。百姓不敢对抗,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昨闻街坊菜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壶,撞击酒家翁,口称:‘台尊示禁(州县领导宣布禁令),天早粮贵,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径去。今日下寺业酒之户成来舍下,问讯煮酒究犯何法,我辈资本所关,讵能歇业?且闻查牌在乡已诈某家钱若干矣。”
“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就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确定的。差役们找上门去,口称奉领导之命,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行贿是很正常的。由此可知,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当白役的直接收益。
既然当白役直接收益如此丰厚,也就难怪会有人热心参与此事。因为他们反正没有正经事做,况且以收入而论,贫下中农难得吃一顿酒肉,挣钱也不如白役多。相比较起来,流氓无产者是白役的后备军。而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的伤害权,丰厚的直接收益,就好比是一个利薮,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
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削减白员有害,增添白员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上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基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诏书一经公布,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漕粮的负担,但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原来,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象,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14万余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
《明史》中记载,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竟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据《万历野获篇·大臣用禁卒》记载,明朝只有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人用过禁军。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长),他痛恨军官冒滥,斥去军营将校三十余人。结果怨恨者引弓射入他的家门,又搜罗了他的过失,飞书射入皇宫。皇帝只得赐给马文升锦衣卫士12人。
由此看来,裁员不仅有丧命危险,还有掉乌纱帽的危险。怨恨者搜罗裁员者的过失,写匿名信告状是常见的官场手段,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得住这种挑剔?
后退一步天地宽,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官员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更何况,白员的投资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是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谈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没有考虑上级和皇帝的要求,也没有考虑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假如官吏们执法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反之,如果执法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还得不到上级的奖赏,那么,皇上下达给官员的命令就近似一纸空文。
清朝人刘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坏,就把高官不肯真正执限制白员法说成首要原因,他说:“四川吏治之坏,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有多么邪恶,关键是官员太多。”为什么多呢?因为违例。大官中没有一人认真办事,明知其违例也不肯处理。
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五杂俎·事部二》中这样介绍这套通行策略:
上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这是通行的套路。大体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骗官员,官员假装震慑欺骗百姓。说什么禁止参谒、馈送、通关节,禁止私下攻讦、常例、迎送、奢华,禁止左右人役需索等,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朝令夕改。
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