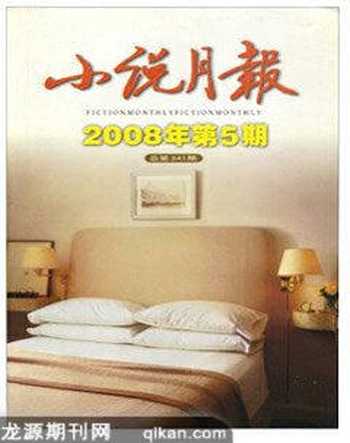西江月
人们以为他是傻子,其实他识得字,会搓绳,能编筐,还收集各种男女旧鞋,大概对鞋业有研究兴趣。他只是有点懒,对各种招工告示漠不关心,碰到有人雇他挖沙或者卸煤也只当耳边风,情愿守在街边晒太阳,玩蚂蚁,磨石子,放出一个个哈欠,把自己固定成一处街头风景。
他一双耳朵很灵,薄薄的肉片微微一颤,就能听见远方似有若无的锣鼓或鞭炮声,能辨出那是红喜事还是白喜事。他嗖的一下及时现身那里,一身万国装五颜六色大小不齐男女混杂又洋又土,浓浓馊臭还让人们掩鼻而退,呼吸困难,差一点作呕。
“这里没有龙贵,到别的地方找去!”主人知道他经常寻找一个叫龙贵的人。
他翻一白眼,嘴里嘟嘟哝哝。
“客人还没到,你倒抢了个先!”主人气不打一处来。
他搓搓手。
他再挨骂也不报复,甚至不生气,也并不靠近酒席强讨,更不会突然上桌抢夺,只是远远地坐在树下,一声不吭地吞咽口水,好像是来为酒宴义务站岗。但这样一个蓬头垢面的哨兵有点煞风景,一旦撞入客人的视野就如无形叮咬,让人心里发毛。万一起风了,不知来自何处的馊臭徐徐入席,与各种佳肴串味,给各种恭维与祝贺的话增鲜,更会大败客人们的兴致。想到这里,主人只能自认倒霉,盛一碗肉饭前去恭请哨兵撤岗,去柴房或墙角单独进餐。更好心一些的主人不但管饭,还会塞几角钱,让这颗毒气弹早一点乐颠颠离去。
对于他来说,酒宴当然不是天天有。有时候,他爬上小镇附近的山头,竖耳细听好一阵,也没听到远方的锣鼓或鞭炮声,只得怏怏地回到街上游荡,收缩一下鼻孔,在这家门口炖墨鱼的气味中坐一坐,在那家门口煎豆腐的气味中倚一倚,困了就蜷缩身子睡一觉。他还是不会开口乞讨,不会那样没皮没脸。如果无人施饭,他就会抹抹嘴巴往垃圾站而去,找一点菜根菜叶什么的入口。日子长了,他连活蛤蟆和死老鼠也能吃,有时口吸一条蚯蚓像吸面条,嚼一只蚱蜢如嚼花生。但他从来不生病,有时脸上还有两块鲜鲜红晕。
“哇——哇——”他气得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威胁那些把垃圾倒在站外的孩子。
如果发现有人倾倒霉变的香烟、腐烂的瓜果、过期的滋补品,他也必定冲着浪费者再次发飙,再次气得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哇——哇——臭屎屎——”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他的名字,见他龇着几颗龅牙,都叫他“龅牙仔”。他的年龄也难以确定,虽然已有抬头纹,但一张脸鲜嫩,嗓音很尖细,薄薄身子好像还没发育完全,看上去是老年与少年的随意组合。
比较熟悉他的是两个乞丐。一个外号铁拐李,是本地名丐,总是拄一钢管为杖,虽气象凶险,但每次只讨三分钱。你要是给他一分钱,他会坚决拒收。你要是给他一角钱,他追着喊着也要将七分钱找还给你,绝不占便宜,绝不乱规矩,让人们觉得特别有趣,也更愿意掏出钱来测试他的诚信。另一个外号变形金刚,是个大胡子,操四川口音。其绝活是在车站或码头占据最佳迎客位置,一屁股坐下来,三下五除二,让自己的左腿膝关节错位,来一个前后倒置,如同下身反接了一只脚,有点惨不忍睹。照他求助纸牌上的说法,东风浩荡,凯歌震天,红旗漫舞,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但建设祖国的无私奉献者们有苦何处说?无钱疗伤之苦可有人知?……他的动人说辞和志愿军、老劳模一类不知真假的身份,每次都为他赚了个盆盈钵满。但只要旅客们散去,他左右看看,咔嚓咔嚓两下,又能使膝关节复位,金刚再次变形,然后夹着纸牌从容回家。
据他们俩人说,小花子已来花桥镇三年多,与他们同宿镇西门桥下,平时不怎么言语,也不做什么有伤丐德的坏事,只是喜欢偷偷公家的招牌,曾先后把学校、獸医站、计划生育协会、革命历史教育基地等牌子,偷搬到桥洞里来挂了个琳琅满目。他连镇政府的牌子也敢偷来当床板,说政府干部连垃圾站都管不好,搞得那里臭水横流没法下脚,实在臭屎屎,太臭屎屎,根本不配挂牌子。至于他自己的事,他家里的事,谁都没听他说过,只是听到他常在深夜梦中大喊一个人名:“龙贵”,“龙贵”,“龙贵”……大概就是他常在街面上寻找的那个人。
“这里根本就没有姓龙的。”镇上有些人早对他宣告。
“你那个龙贵嘛,我认得。他到九江去了,江西九江,知道吗?”也曾有人这样打发他。
不知道他去过九江没有,去过人家胡乱说出的湘潭、永州、祁阳、安化、麻阳没有。不过他还是幽灵般地出没于小镇,似乎要死守这一个约会地点,深信他期待的人不可能失约,正在远处一步步朝他走来。龙贵是他什么人?给他许过什么愿呢?或者龙贵只是他梦中一位救苦救难的下凡仙人?……人们不得其解。每逢汽车喇叭或轮船汽笛鸣响,只见他应声而起,呼的一下蹿去车站或码头,在客流中穿插如梭,逢人便急急地掀起几颗龅牙:“有叫龙贵的吗?”……见对方茫然,便进一步唾沫喷飞:“龙马的龙,富贵的贵。”有时还在掌心上写给别人看。
人们总是对他摇头,或是被他油光光的衣衫片子吓住,慌慌地快步跳开,像避开一只硕大苍蝇。
这些旅客大多是来进香拜佛的。花桥镇是他们上山的必经之地。山上有一禅庙,近年来香火很旺,钟鼓常鸣,轻烟薄雾缭绕林间。穷人和富人都去那里祈福,特别是一些瘸子、瞎子、聋子、瘫子以及各等哎哎哟哟的重病者,不知道听了什么传言,都急着上山求医——据说那里有一位神僧颇得法力,不用针和药,只是撮土为丸,吐痰为汤,随便在来人脸上摸一摸,或者朝来人屁股拍两掌,就能包治百病。小镇因此越来越热闹了,不光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斋菜馆,还有各种卖鞭炮、香烛、佛经、雕像、供品、碑刻拓片及各种旅游产品的店面。有些非法游贩也出现在此,躲过警察与市场管理人员,偷偷向旅客兜售神僧的指甲、皮屑、胡须乃至干粪便,声称这些秽物均有医疗神效——只是不知他们的货品是真是假。
有一个鞭炮店老板姓陈,这一天站在店前东张西望,最后把目光落在龅牙仔身上。“你过来,过来!”
小花子懒懒地看他一眼。
“你是要找龙贵吧?我可以帮你找到。”
龅牙仔眼睛发亮,朝他走近了两步。
“我还骗你不成?龙马的龙,富贵的贵。没错吧?不过,我不能白帮你,你得给我信息费。”
龅牙仔听懂了,撒开两只赤脚就跑,不一会儿气喘吁吁又回到老板面前,扒开一个旧塑料编织袋,出示里面的各种宝贝:一盏旧台灯,一只旧公文包,一台可以发声的旧收音机,还有一大堆男式和女式的旧皮鞋,轰隆隆的脚臭味扑面而来。
“把这里当废品站啊?要熏死我呀?”老板捂着鼻子后退,“这样吧,你给我一百块钱,要不就给我打五天工。”
龅牙仔沉下脸,提着编织袋就走。不过龙贵对他还是有吸引力的,他没走出两步又折回,挠挠头,指着隔壁小店里卖的包子。
老板好笑,“看不出,你小子还会讨价还价?好吧,我就每天加你两个包子,算是你的加班费。”
龅牙仔咬着两个包子,跟着老板走了。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一天鞭炮厂有工人嫌工钱少,突然辞工而去,人手忙不过来,陈胖子只好临时拉龅牙仔顶班。老板哪里知道什么龙贵,只是以为小花子好哄,到时候胡编个说法就行。他没料到,五天过去以后,龅牙仔成天追在他屁股后头问:龙贵!龙贵!龙贵!……差一点在他耳朵里磨出茧子,还抢他的帽子。实在混不过去了,老板只好装模作样打了一个电话,回头说:“湖下村是有个龙贵,不过刚生出来,还差三天满月。东门外呢,有条癞皮狗也叫龙贵,大家都这么叫,你可以去找。第三嘛……”他还没有说完,龅牙仔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发出持久的尖叫,夺过电话机就往地上砸。老板当然早有防备,出手夺回电话机,仗着自己腰圆膀壮还把小花子一身骨头扭得咯咯响。“老子给了你三条信息,没加收你的信息费,就算便宜你了。你还要在这里行武?找死啊?老子一个指头把你捏到门缝里去!”
他把龅牙仔轰出店门:“滚远点,滚远点,要是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吊到井里去凉快凉快!”
老板的大洋狗也及时出阵,冲着龅牙仔一阵大吠。
小花子这才逃之夭夭。
陈老板财大气粗,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平时搬着肥大屁股随便往哪家一坐,主家就得笑脸相迎,又是敬茶又是敬烟,还得恭敬聆听各种教训。他说你家茶叶不好,你家茶叶就是不好。他说你家儿子太蠢,你家儿子就是太蠢。他说你家里有鸡屎臭,你即使从未养过鸡,即使在家里刚喷过三轮香水,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大家都把他当菩萨他爹供着。不过,陈老板接下来的日子有点不顺。比方每天早上开门,他店门前不是有一堆臭屎,就是有几堆五光十色的垃圾,气得他脑袋大。一个“良种猪仔基地”的牌子不知何时挂在他门前,更让他满脸猪肝色,操起一张板凳就砸。但刚砸了这块牌子,两天后门前又冒出一块“烈士陵园”的牌子,比良种猪仔还糟心十倍。他气歪了脸,令手下人把牌子火烧了,在店门前一连放了十挂万子鞭。在门槛上淋了三道公鸡血,还觉得店门前不干净。
陈老板不至于当烈士,不至于住陵园,但事情不能细想啊,一想就大病了一场。他重新出现在邻居面前时,头贴黑膏药,手脚僵硬,哼哼唧唧,还时不时胸闷欲吐。照他的说法,害他的不是别人,肯定是那个该千刀万剐的龅牙仔,真恨不得扒了那家伙的皮才好。他这次住医院、拜菩萨总共花了好几千块,算怎么回事?就算抓住了那个小杂种,把他剁成碎片卖上十次,也卖不出这么多钱吧?
“还是老班子说得对,花子惹不得,惹不得的。”陈胖子苦笑着直摇头,从此见了龅牙仔就躲,见了所有的乞丐都心虚气短。据说他后来花了一笔钱,买通一个黑工头,把龅牙仔骗到贵州去下井挖煤。
一个多月以后,一位赶郎猪的老头儿晚上回家,看见几条狗在水沟边嗅着什么。夜色昏暗,他看不大清楚,只觉得水沟里好像有动静,划燃火柴一看,发现那是一个人,面色苍白,嘴唇发黑,一条腿粗肿如桶,身上还有很多酱色的血渍和血痂——这不是龅牙仔吗?腿肿成这样,是不是被毒蛇咬了?
他是如何逃脱黑工头的魔掌,如何从千里以外的煤矿跑了回来,又如何不小心受到毒蛇攻击……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出现在街头一个拆走了轮子和机器的中巴车厢壳子里,颤抖在乱草丛中,鼻孔里气若游丝,一连昏迷了几天。一个卖瓜的九婆婆可怜他,每天驼着背送来米汤给他慢慢地喂下,还带来一罐浓浓的茶水,替他洗一洗身上伤口溃烂处的脓血。看见嗡嗡飞绕的蚊蝇,她还点燃了一支蚊烟。
“可憐可怜,你就没有个家吗?”九婆婆终于看见他醒了。
小花子两只眼睛里空空洞洞。
“你就没什么亲人了?”
死鱼般的眼睛还是直愣愣向天。
九婆婆撩起衣角擦擦眼睛,从怀里颤颤巍巍掏出一个小酒瓶。“苦命的伢,你活着为哪样呢?你爹妈把你生下来做什么呢?你的苦还没吃够哇?九婆婆今天给你做个主。你把它喝下去。”
小花子眼眸隐约一暗。
“你不要怕。这是快活汤,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你一喝下它,身上就不痛了,肚子也不饿了,心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往后就一心一意过好日子。”
龅牙仔嘟哝出一个字:“龙……”
九婆婆知道他要说什么,叹了口气:“伢啊伢,世界上没有你要找的人。你死了这条心吧。”
“龙……龙……”
“莫说是你那个龙贵,就是菩萨也救不了你呀。”
龅牙仔咬紧牙关,死死堵住瓶口,就是不张嘴。一滴泪水终于出现在他眼角。
“这是为了你好哩,你听话,听话,啊?”老人没法灌,收回小酒瓶,揩去对方的泪滴,哀哀地哭了一场。据知情人后来说,九婆婆那一段是觉得自己气虚和腿重,看来是大限在即,哪一天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她担心自己一旦撒手西去,哪一个来给龅牙仔送米汤?如果没有她的米汤,龅牙仔嗷嗷地如何活下去?
九婆婆一失足跌倒下去,确实再也没有起来。大概是感念九婆婆的善德,一些好心人东一碗汤,西一碗粥,把九婆婆的好事做到底,还叫来一位医生,抓了几帖药,竟使龅牙仔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虽然脸部多了一块暗疤,拉扯得表情有几分狰狞,虽然一条腿有些瘸,使他走路时尖尖屁股一撅一撅,但他还是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街边晒太阳,玩蚂蚁,磨石子,放出一个个哈欠。他还去河边九婆婆的坟前叩了几个头,在那里立了好几块牌子,有“先进幼儿园”、“商品质量信得过单位”,以及他曾经拿来垫床的“花桥镇人民政府”。
经过一个多月的贵州行,他甚至更长本事了,伸出的指头不怕火烧,铁硬的脑袋扛得住棒打,还学会了吃土——随手捡起一块黄泥或黑泥,嚼巴嚼巴就能往下咽,令围观的小孩儿们十分好奇。有一次他没找到合适的泥巴,甚至还吃起了沥青和煤渣,嚼出了杏仁或蚕豆的声响。一位过路的电视台记者发现了这一点,想拍个奇人花絮之类的节目,曾给他三十块钱,想让他在镜头前表演吃土,只因他哇哇怒吼,捡起一个石头相威胁,才遗憾地作罢。
铁拐李想当他的经纪人,追着对记者说:“加一点,给两百,给两百他就吃土。”
他在记者那里点了钱,回转身来,却发现龅牙仔不见了。
这一天,又一批外地旅客来到了小镇,停车场里大车小车很是热闹,到处是人头攒动和大呼小叫。有一中年鬈发男子戴着太阳镜,走出一辆白色轿车,刚好被龅牙仔远远地看见。“你认不认识龙贵?”瘸子拄着竹杖照例上前搭一腔。“龙马的龙,富贵的贵。”
对方正在锁后备箱,随口回了一句:“我就是,什么事?”
好一阵没有声音。
还是好一阵没有声音。
事情似乎已经完了。对方回过头来,显然看见了龅牙仔呆若木鸡,脸色发白,全身颤抖,还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差不多就是一个将要虚脱的病人。对方肯定以为自己倒霉,碰上了疯子,赶忙跳开一步,朝车那边的两个女人挥挥手,朝山上快步而去,一边走还一边回头。
龅牙仔终于发出呜呜呜的哭声,或者是笑声,追上去问:“你……你……真的是龙贵?”
“一边去!我不认识你。”
“你肯定认识我姐。”
“我要喊警察啦。”
“你不就是在黄沙桥的人……”
“你……”
“你不就是龙天祥他二弟?”
对方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全身僵住,忍不住将小花子上下打量。“你是……”他没说下去,只是乘人不备撒腿就跑,差一点撞倒身边的一个老头儿。但这已经足够,足以让龅牙仔完成认证并锁定目标。他大叫一声,旋起一阵风,啪啪两脚翻飞追了上去。后来有目击者说,那一刻他根本不像个瘸子,只见一道黑光闪过,飞向天空的竹杖还未落地,他已突然放大,像一只巨大蜘蛛缠住了前面的背影。
两个女人发出尖叫,吓得周围的人毛发倒竖引颈张望。他们终于看见两个黑影在河边的西门桥上扭成一团,像是拥抱,又像是厮打。他们来不及打听是怎么回事,就听见那里一声声大叫震天。“龙贵!”“龙贵!”“龙贵——”这叫声像是欢呼,又像是叫骂,怎么也让人听不明白。一切都来得这么快,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直到两个时分时合的黑影在桥上一晃,翻过栏杆,双双掉入河里,激起沉闷的扑通一声,他们这才大致明白,刚才不是拥抱,也没有欢呼。事情似乎有点不妙。
“杀人啦——”
“救命啊——”
两个警察终于从派出所那边赶过来。
他们来到西门桥,朝桥下看了看,只见水面一圈圈波纹渐息,没有什么东西冒出水面。他们见河边有几条船,忙上前交涉,请船老板把船划到刚才溅起水波处,用船篙探入水中搜索。但他们来来回回戳了好几轮,没有戳到什么。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警察从中发现了几个熟面孔,大概是水性比较好的,要他们下水帮着寻找。加上哭哭啼啼的两个女人当场拍出一沓钱,那几个后生就脱了衣服,在腰间系上安全绳,一个接一个跳下水去。不过,直到入夜,直到东门那边升起一轮月亮,他们在水下捞出两只皮鞋。一只铁油桶,一个摩托车头盔,一头半腐的死猪,还有一张糊满泥巴的渔网,就是没有找到人。只有一只出水的男式皮鞋,由两位哆哆嗦嗦的女人辨认,是当事人的,由警察提到派出所去了。
“龙贵——”
“龙贵——”
“龙总,你在哪里啊——”
夜色降临,西垂的一轮明月下,苍茫远山垫在树林剪影的后面,河面上飘摇着一道闪闪烁烁的光斑。两个女人在河边一直哭喊到深夜,在码头的石阶上拍出更多钱,还有当场解下的金戒指、金项链以及金耳环,算是对救人有功者的重重悬赏。更多的船出动了,搅出了更多月光。更多的小镇居民聚集在河边交头接耳,惊得两岸狗吠声久久不息。一些手电筒、灯笼以及火把闪烁不定,沿着河岸向下游摇曳而去。
龙贵的尸体三天以后才浮出水面,漂到下游的一片芦苇边。据说他已全身浮肿,肚子胀大如鼓,虽然四肢还在,但鼻子没有了,耳朵没有了,上下嘴唇也没有了,整个脸盘似乎被木匠刨子刨去一层,刨去了毛边和棱角,只剩下一团圆嘟嘟血糊糊的肉瓤,暴露出多处白骨。法医从他脸上发现好几道深深肉沟,相信那是牙齿啃刨的痕迹。至于龅牙仔,当然也没活下来,据说他满嘴肉泥,身上至少有四处骨折。
这真是一桩离奇而惨烈的命案。
因为没找到身份证,也没法给中年男客恢复容貌,加上两个涉案女人失约,未去派出所留下笔录,驾着白色轿车不知去向,警察手里的破案线索实在有限。他们不知道死者是什么人。从龅牙仔寻找龙贵这一点看,他并不认识后者,与后者应无直接的过節,那么他是为谁张开利嘴?为他父亲?母亲?姐妹?兄弟?师友或者乡亲?同样令人迷惑的是,这食肉之恨何来?是关乎钱财?关乎性命?关乎情爱或尊荣?……警察遍访小镇居民也没问出个所以然。九婆婆的儿子说,他听龅牙仔昏睡时骂人。好像是骂自己没有用,但那是操一种奇怪方言,他没怎么听懂。铁拐李说,他发现龅牙仔每年六月初到河边烧纸,祭悼什么人,但不知与案情是否有关。
上级公安机关也派人来查过,只查出那个叫龙贵的身家不菲,是山上禅庙的大施主,至少有过三笔数目不小的捐赠记录。
事情到此,看来也只能不了了之。警察叫来几个农民,把两具尸体埋葬在西门桥外。
街市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山上的香烛气息和钟鼓声响不时飘下来,流散在墙基或者檐角,流散在外地旅客的擦肩而过和蓦然回首之际。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发现街上出现了一个少年,也是在找人,逢人便问:“你是不是王海?”如见对方迟疑,又急急地解释:“龙王的王,海洋的海。”甚至还要在掌心中写出字来给你看。
更严重的情况是,不久后街上又冒出两个陌生面孔。一个是黑脸大汉,见人就问:“你认识周华剑吗?”另一个是戴眼镜的妇人,见人就问:“你知道李子明住在哪里?”
街上闲人们一听这话就心惊,好像自己就姓周或者姓李,凉气从背脊一直升到后脑,纷纷作鸟兽散,包括赶快揪回自家的孩子,哗啦啦拉下铁闸店门,让寻人者不免有些诧异。
他们都面带微笑,甚至衣冠楚楚,不像是刺客。说不定他们只是来寻找情人或恩人的?或者是拾金不昧来寻找失主的?或者是受人之托来寻找什么故旧?
他们四处探头探脑东游西荡的时候,街上寂静了许多。
据闲人们说,这个小镇的居民后来都习惯于晚开门和早关门,习惯于养看家烈犬,而且多了一些流行口语。人们见到做了恶事的人就忍不住诅咒:“等着吧,总有人要长龅牙齿的。”或者是:“就算老天没长眼,他也不一定过得了西门桥。”喜欢恶作剧的人还曾这样吓唬朋友:“不得了,今天街上有个眼生的人到处打听你哩。”直到有一次,一个被吓唬的人当场晕倒,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差一点猝死,大家才知道这种玩笑不能乱开,往后的口舌才谨慎了许多。
【作者简介】韩少功,男,1953年生,1968年初中毕业赴汨罗插队,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任湖南省专业作家,1988年调入海南省文联。出版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小说集《月兰》、《诱惑》、《空城》、《爸爸爸》十余部,散文随笔集《面对广阔而神秘的空间》、《夜行者梦语》、《灵魂的声音》、《韩少功散文》等七部,《韩少功文库》(十卷),译著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多部。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小说《西望茅草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过蓝天》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奖,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等多种奖项。现在海南省作协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