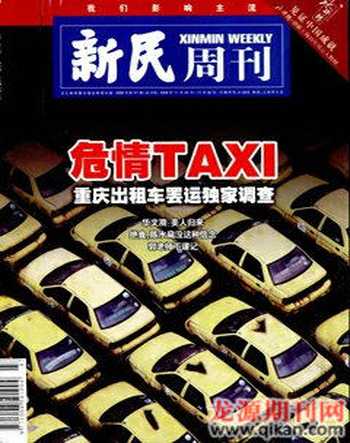一滴清水,不能吹泡泡
周立民
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他们都不是被吹起来的肥皂泡,但不能因为没有“吹”他们,我们就忘了这社会中的一滴滴清水。
我们的人物传记和纪实文学中往往只有两种角色:神和魔鬼——赞之者便是比圣人还圣的神,而贬之者就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唯独没有令人可喜可爱可敬或可气可恨的人。钱钟书和杨绛历来是传奇的主角,关于他们的文字都神神秘秘、玄而又玄,弄得这对老人在人们面前早已面目不清,只记得“大师”、“昆仑”、“巨擘”之类的空泛名词了,偏偏忘了他们也是生鲜的人。这本《听杨绛谈往事》如果说好,也恰恰在这里,你要找传奇、一气呵成的故事几乎没有,但“平淡”、“平常”恰恰是该书让人读来最有滋味之处。
虽然是杨绛的传记,但她的另一半钱钟书无疑也是本书的闪亮主角。这本书也有为公众传媒中钱钟书“去蔽”的作用,让他从大师的光环中解脱出来而还原为一个同大家一样吃着五谷杂粮的书生、丈夫、父亲。钱钟书是超级书虫,见了好书就买,偶尔听了杨绛的话没有买结果下次买不到了,只好“气愤”地在日记中记道:“妇言不可听”——这是钱钟书的专利故事。一般传奇中关于钱钟书恃才傲物似不通世故的才子行为演绎甚多,偏偏忽略了他也深谙“默存”之道,本书却毫不讳言。1950年8月奉调去英译毛选,在许多人眼里煞是风光,但钱钟书却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难做的事钱先生似乎很清楚该怎么做,哪怕遇到学术问题也不再去较真:“好在钟书最顺从,否了就改,他从无主见,完全被动,只好比作一架工具。”
书中的小儿女的情感也很真切、生动,不乏有趣的细节:钱钟书1941年从湖南回到上海,两年乡居生活,面色黑里透黄,胡子拉碴,年幼的女儿几乎不认得爸爸了,见爸爸把行李放到妈妈的床边,很是不放心,指着奶奶对爸爸说:“这是我的妈妈,你妈妈在那边。”钱钟书很窝囊地笑着问她:“到底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女儿理直气壮:“当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的。”
当然,即便琐碎的家長里短照样也可以让我们领悟很多东西,比如钱钟书的博学,除了天赋之外,我们更能从书中看到他的努力:在牛津读书时,钱钟书钻入书堆如蠹虫一般狂啃,法国文学从15世纪读起,一路读下来;然后读德文书,然后自学意大利文,并记下大量笔记。抗战时期在条件艰苦的蓝田,教书之余,钱钟书就躲在自己的小屋中埋头用功读书写作。钱钟书去世后,杨绛整理他留下来的笔记,各类外文笔记178册,共34000多页;日札23册2000多页,还有大量的中文笔记。这些笔记共计7万多页——我相信现在谁如果能下到这个功夫,哪怕赶不上钱钟书,也可以揪住大师的尾巴了。
《杨绛文集》出版时,出版社希望杨绛能够出席新书宣传活动,杨绛却说:“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这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自己而言或是自谦,或是人的自知之明。但对于传记的写作者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要求,澄明和平淡中更能识得真人面。《听杨绛谈往事》中虽然读不出传奇来,但更耐品。书中写到把一生心血献给振华女校的王季玉校长、一心为公又自杀身亡的化学教授王崇熙,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他们都不是被吹起来的肥皂泡,但不能因为没有“吹”他们,我们就忘了这社会中的一滴滴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