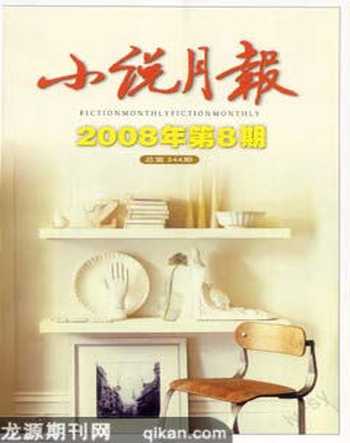会说话的南瓜
学堂不但小,名字也很土气,叫做核桃树学堂,坐落在豫西的一个深山沟里头。说是学堂,其实只是一间土坯子垒起来的小泥屋。屋顶呢,则是用秫秸、谷秆和着麦草苫起来的草厦子。天气晴暖的日子,一走进去就会嗅到一抹庄稼成熟后晒干的香甜,很是受用呢。老师不多,只有一个人,姓顾。不过,大家不叫他“顾老师”,而称他“顾三爷”。顾三爷年近七十,小时候念过几年书,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年岁大了,再加上瘸着一条腿,做不来别的活路,他就自愿做了孩子们的老师。
说是老师,其实也没教几个学生。学生呢,也是参差不齐、缺胳膊少腿的。通常只有五六个的样子,而且年龄相差悬殊。最大的十七岁,叫罗白,是邻村的,顾三爷赶集时偶然遇见他,便把他招进了自己的学堂。不过,大家都管他叫萝卜。他个头大,往小孩子们身边一站,真像一只大白萝卜似的。山里人的眼里,萝卜和白菜一样,都是上好的菜蔬,漫长的冬天里,全靠它下饭哩,这名字不带丝毫的贬义。萝卜虽然将近十七岁了,智力却跟五岁的孩子差不多,做顾三爷的学生倒是一点不屈才。
除了萝卜以外,其余的孩子都不傻,不过多多少少都有些残疾:一个因为发高烧耳朵聋掉了,听不见声音,成了哑巴;一个因为触电烧掉了一只胳膊;第三个因生瘤子锯掉了一只脚。还有一个孩子倒是胳膊腿儿齐全,然而,都十几岁了,个头还不到一米,是个天生的侏儒,大家叫他土豆。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来脊椎就严重变形,走起路来像虾一样弯着腰,名字自然就叫做“虾米”。
这些孩子们都没有办法进正常的学校念书,顾三爷看他们可怜,就把他们招集到一起,办了这个免费的小学堂。顾三爷不要工资,孩子们也不用课本,顾三爷肚子里装什么就教他们什么。村头有一棵老核桃树,遮天蔽日的,怕是有几百年的树龄了。树下有一间小泥屋,原来是生产队里作仓房用的,顾三爷领着孩子们把屋子打扫了一番,然后,搬进去几块石板、几只树墩,桌椅板凳就算是齐全了。
顾三爷的课堂没有严格的规程,天上的太阳就是他们的钟表。太阳爬出来一丈多高的时候,孩子们就来了。太阳打着呵欠回家睡觉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散了学。若是哪一天太阳躲在被窝里偷懒,他们就知道:天要下雨,不用去学堂里了。
虽然只有五六个学生,但,核桃树下的小学堂里却是热闹非常。孩子们来上学的时候,有的牵来一只半大牛犊子,有的带来两只小羊羔。没办法,山里的庄户人家过日子,莫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谁都不能闲着。到课堂念书的时候顺便把牛犊子羊羔羔带出来吃些草,在他们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核桃树下就往往出现这样的情景:孩子们在小泥屋里念书识字,哇哇哇,哇哇哇。牛犊子和大白鹅则在教室外头扯起喉咙唱长调,哞——嘎嘎嘎,哞——嘎嘎嘎,像比赛似的。羊羔羔一般来说比较乖,吃饱了肚子便安静地守在教室外头,不声也不响。实在忍不住好奇时,最多把小脑袋探进门缝里偷看两眼而已,等它们的小主人散了学,便亲昵地跟了他们一起回家。山路崎岖,回家时他们往往排成细长的一支队伍,边走边唱顾三爷教他们的歌:
两只老虎跑得快来跑得快
一只没有那个尾巴
一只没有那个脑袋
真奇怪呀真奇怪
孩子们唱歌的时候,走在他们身边的家伙们也不甘寂寞,不时地拖长了声音引吭高叫一曲来凑热闹。大家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就如同美妙而又和谐的交响乐了。
不过,顾三爷并不整天让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念书识字。根据季节和时令的变化,他也会适时地教孩子们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春天来的时候,他便教孩子们种南瓜。
南瓜是一种非常耐旱的作物,不娇贵、也不挑剔。只要有巴掌大的一抔土,再给它一碗水,它就能生根发芽,拖出长长的秧子,然后再结出一个或几个愣头愣脑的大南瓜来,喜人得很呢。庄稼歉收、口粮短缺的年景,能拿来当饭吃。还可以整年论月地放着都不坏,越放越甜,是乡下人的宝贝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种上一些。不过,在一些长不成庄稼的边角旮旯里才舍得种南瓜。有时候,主人把南瓜籽随手种下以后就忘了,南瓜呢,不抱怨也不偷懒,还是默默无闻地待在自己的角落里暗暗地长着个头,直长到像一头小肥猪那么大。某一日,主人出来打柴或是采药的时候,无意间与它们遭遇,就像邂逅了多日不曾见面的好朋友一样,欣喜地采摘了扛回家,它们才算登堂入室,在最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
顾三爷想,一个孩子无论多么没本事,只要学会了种南瓜,便不会再饿死。因此,种南瓜对孩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门功课呢。
孩子们遵照顾三爷的嘱托:有的从家里带来小铲子,有的带来小铁镐。萝卜力气大,挑来了满满两桶水。顾三爷一边讲解,一边手把手地教孩子。种子埯下去以后,过了几天,顾三爷带孩子来一看:那些小家伙们像调皮的马猴虫一样,从土里拱出来,生出嫩绿的苗芽来了。他们小心地给那苗芽浇了水,又捡来羊粪蛋蛋偎在根部,给它们一棵一棵地施了肥。那叶片不断地变化着,差不多一天一个模样。终于有一天,从嫩绿的藤蔓上开出了金黄色的、像小喇叭一样的花朵。那花朵的清香引得一群又一群的蜜蜂围了它们,一边打着转转舞蹈,一边嘤嘤嗡嗡地唱着歌儿。孩子们问顾三爷,蜜蜂们唱的是什么呢?顾三爷告诉他们,蜜蜂是在赞美南瓜花呢,那唱出来的歌儿就叫做《酿蜜歌》:
花儿花儿真漂亮。
赛过树上臭豆娘。
豆娘臭,花朵香,
酿成蜜儿作冬粮。
等蜜蜂采完了蜜,花朵慢慢地衰败以后,肥嘟嘟的小南瓜便像婴儿一样,张着小嘴儿嘻笑着探头探脑地长出来了。孩子们一个个兴奋得手舞足蹈,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似的。他们不断给南瓜浇水、施肥,南瓜就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有的长得长长的、弯弯的,像面包圈;有的长得圆滚滚、肥肥壮壮,像羊肚子。有的甚至有牛头那么大,重达二十多斤,一个人扛都扛不动,要放在箩筐里让两个人抬着,才会搬回家去。当孩子们扛着金黄肥壮的南瓜回家时,家长们都高兴得咧开嘴巴,笑得牙齿都快要跳出来了。
收获了南瓜,春天就慢慢地谢幕,日子转入另一乐章。
山里的日子不像城里那么稠密和刻板。城里人掀着日历、掐着钟表过,人活得像机器,日子过得如同一本账簿,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算计出来的数字。乡下的日子是一片一片或是一抹一抹地度过的,舒缓有致、抑扬顿挫,像是一幅写意的水墨画,又像是一首悠长而又古老的歌谣,时而浅浅淡淡、时而浓墨重彩,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当田野里一片嫩绿,脚下的土地变得潮润润、湿漉漉的,虫子开始鸣唱、燕子回来衔泥做窝的时候,是春天来了,于是开始播种。之后,他们合着季节的律动,由夏的热烈激荡,过渡到秋的极尽张扬,慢慢地把那悠长而又古老的曲子一步一步地推向高潮。一唱三叹、千回百转,那四季的韵味便被一点一点地吟咏出来了,日子也如同袅绕在树梢上的炊烟一样,不知不觉地随风掠过,如羚羊挂角、痕迹不着,又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顾三爷的课程也是按季节的变化编排的。春天的时候教孩子们种南瓜,到了秋天,他则带着孩子们漫山遍野地遛红薯。红薯在城里是粗食,在山里却是主粮。红薯像南瓜一样,成活率高、产量大,还耐干旱。到了秋天进到山里,放眼望去,遍野都是绿腾腾的红薯秧。霜降以前,把红薯从土里起出来收回家去,下到菜窖里储存起来,就是人畜一冬的嚼头。庄户人家过日子实在:囤里有粮,心里不慌;窖里有红薯,心里不发怵。“遛”是“寻觅”的意思,就是在收获了一遍的红薯地里再寻找一遭,把遗落在土里的红薯刨出来。这在乡下也是常见的活路,除了遛红薯以外,还有遛豆子,遛花生。遛一遍就会有一遍的收获呢。
孩子们拿了铲子、锄头还有小耙子,学着顾三爷的样子,在土里一边耧、一边耙,挖挖刨刨、翻翻寻寻,不定哪一下,就有一块胖乎乎的红薯被觅出来了。顾三爷对孩子们说:藏在土里没有被大人挖走的红薯,都是小淘气,它们故意躲起来,是为了跟孩子们捉迷藏。它们都有耳朵,能够听得见,只要唱着歌儿来唤它,它们就出来了。歌儿很好学,是这么唱的:
胖红薯,你出来,
我替你寻个花奶奶。
花奶奶,鼻子大,
张开嘴巴没有牙。
顾三爷解释说:那躲藏在地里的红薯一听说花奶奶没有牙齿,不会吃它们,就放心大胆地出来了。一出来,就被孩子们捉进篮子里去,想跑也跑不掉了。运气好的话,孩子们一晌就能遛出一满篮子来。在遛红薯的间隙里,顾三爷也教孩子们一些别的知识。比如,看到地垄间长的一棵药材,顾三爷就告诉孩子们:这药材叫什么名字,能派什么用场。要不了多少天的工夫,孩子们就认识了许许多多的药材:像毛枯丁、七七芽、猪毛尾、灰灰根、兔耳朵,还有驴混沌、头顶一颗珠。顾三爷一边教他们辨认,一边教他们采挖。一个季节下来,孩子们采挖的中草药就有一大竹篓子那么多了,顾三爷托人带到城里的药材店去卖了,拿钱再给孩子买来一些识字书、连环画,还有铅笔和本子什么的,如果剩下有富裕的钱,还会买一些孩子们爱吃的糖果。孩子们吃着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点心,甭提有多么开心了。
开心的日子过得总是特别的快。北风开始呜呜咽咽地歌唱时,冬天就来了。
冬月里天气冷,燕子飞到温暖的南方,兔子和松鼠们都藏进树洞里不肯出来,田里的庄稼已经全部收获回家,忙活了几个月的土地终于歇息下来,可以美美地睡个长觉了。这时候,顾三爷便把孩子们招集进小泥屋里,学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或是讲一些好听的故事。
小屋里暖烘烘的。屋角里生着炉子,炉子里燃着柴火或是牛粪,散发出一种草木才有的很好闻的味道来。在炉塘的灰烬里,埋着孩子们遛来的红薯。红薯一点一点地焙熟以后,焦甜的香味便丝丝缕缕地弥散出来,充满整个小屋。孩子们坐在自己的木墩上,眼睛瞪得溜溜圆,聚精会神地听顾三爷讲故事。顾三爷的肚子里装了许多好听的故事。有天河里牛郎和织女的故事,还有红毛仙狐的故事,孩子们怎么听都听不够呢。讲得累了,顾三爷也教孩子们念一些儿歌或是民曲,都是小时候先生教他的,也没什么意思,只是念着顺口而已。比如:
小西瓜,圆揪揪,
巴掌打来指甲抠。
抠出白仁我吃喽,
抠出红仁拜朋友,
一拜拜到米花楼。
米花楼有个小哥哥,
反穿皮袄大裹脚。
顾三爷每一天都把课程安排得丰富多样。讲完了故事学识字,识完了生字学算题,算完了题以后便带孩子们到野外捡拾山果子。山里人都懂得“靠山吃山”的道理。冬月里,虽然满目苍茫、万物萧条,但仔细寻觅的话就会发现,一些秋天里被遗落的果子还挂在枝头上,经历了风霜和寒露,它们的颜色更红,吃起来味道也更甜了。还有一些坚果之类的山货,也因熟透、风干而跌落到了地上。有的藏在草稞里面,有的躲在碎石头的缝隙里,被人捡回家的话,就会派上各自的用场,没有人捡,就变作一粒种子,悄悄钻进土里,等来年的春天,再开始生命的第二次轮回。
孩子们捡得最多的是橡籽。橡籽就是橡树上结出来的果实。橡籽成熟以后有指头肚那么大,坚硬饱满、圆润光滑,像算盘珠子一样。捡回家里可以用麻线穿起来,挂在脖子上当装饰品,也可以磨成面,做成橡子凉粉,或是烙成橡子饼,蒸成橡子糕。橡籽做出来的食物味道佳、口感好,稀罕得很呢。就是在捡橡籽的时候,孩子们捡到了那只獾仔。
那家伙像一只小猫娃一样,可怜巴巴地躺在崖壁下的草稞子里,一身灰毛,脑袋上还有三条白色的纵纹,看上去快要死了。它显然是不小心从崖壁上跌下来摔伤的。顾三爷让孩子们把獾仔抱回小泥屋里,挨着屋角的炉子给它垒起了一个小窝。獾仔跌伤了腿,不会走路,孩子们烤了红薯和野果子来给它吃。它像一个乖宝宝一样,吃饱了肚子便抱着脑袋,憨态可掬地躺在窝里睡觉。没过多少日子,它就成了孩子们的朋友,腿伤也慢慢痊愈,能够走路了。每一天孩子们来上学的时候,它总是走到路口,远远地迎着孩子们。
然而有一天,当孩子们从家里来到学校的时候,却发现小家伙不见了。他们寻遍了周围能够隐身的每一丛草窝,都没有找到它,便伤心得哭了起来。顾三爷告诉孩子们说:獾仔回家找它妈妈去了。孩子们听了顾三爷的话,才止住了眼泪。不过,每当到野外采果子或是捡牛粪的时候,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觅着,希望能够再次邂逅那只可爱的獾仔。可是,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他们没有再遇到过獾仔,却意外地结识了一位猴妈妈。孩子们看到它的时候,猴妈妈抱着一只小猴子,蹲在一棵柿树上,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红灯笼一样的柿子呢。孩子们都知道,那只小猴子是猴妈妈的宝宝。它看上去毛茸茸的,十分讨人喜欢。他们很想跟那只小猴子玩耍玩耍,可是,猴妈妈一直抱着它,不肯放它下来。
孩子们灵机一动,生出了一个主意。他们拿出猴子爱吃的坚果、野栗子还有橡籽,放在柿树下面,然后就走开躲起来。等了一阵子以后,猴妈妈经受不住美味的诱惑,终于从柿树上爬了下来。为了迅速地把那些野果子捡拾干净,猴妈妈放下孩子,顾自捡起来。可能是过于饥饿了吧,它一边捡一边吃,似乎完全忘记了小猴子的存在。孩子们趁它专心致志地吃着东西的时候,调皮地冲出来,抢走了它的孩子。然而,到了小泥屋里才发现,那只小猴子一动都不会动。它紧闭着眼睛,浑身冰冷而又僵硬。顾三爷看了看,原来那只小猴子是死的,而且死了有些日子了。这时猴妈妈已经追到门口,顾三爷命孩子们把小猴子抱出去,还给了猴妈妈。猴妈妈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怜爱地拍了拍,然后才离开了。
以后,孩子们又在林子里几次遇到猴妈妈,每一次猴妈妈都抱着自己那已经死去多日的孩子。猴子是很聪敏的,它应该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它那么固执地抱着,肯定是不舍得丢弃。不知道它要抱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手呢。天气越来越冷,猴子想要寻觅到果腹的食物也愈来愈难了。顾三爷看它可怜,便带着孩子们在它经常路过的地方悄悄放下一些坚果。猴妈妈吃饱了肚子,便会抱着孩子晒太阳。它默默地坐着,眼睛里满是忧伤和无奈,让人看了心酸难忍。顾三爷很想把它的孩子接过来,替它掩埋进土里,但,努力了几次都不成,只好随它去了。心想:也许它那么抱着心里会好受一些。顾三爷这么寻思着,不知不觉间,眼睛里面便蓄满了混浊的老泪。
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时候,顾三爷也领着孩子们像猴妈妈一样地晒太阳。他们坐在小泥屋附近的山坡坡上,一边吃着烤熟的坚果或是红薯,一边晒着太阳。太阳红润着一张圆圆的脸,像剖开的南瓜一样,悬挂在半天空。顾三爷坐在孩子们的身边,看看这一个,又瞅瞅那一个。他觉得哪一个都是他的小宝贝。他怎么爱都爱不足,怎么疼都疼不够呢。
由于瘸了一条腿的缘故,顾三爷一辈子都是单身一人过日子。现在,有这么多的孩子陪在他的身边,他幸福得胡子都在一抖一抖地笑呢,把一张核桃皮般的老脸笑成了盛开的山菊花。这一辈子,他吃够了身体残疾的苦头,对这些身有疾患的孩子,他便更多了几分的怜惜。他觉得这些孩子就像羊羔羔和獾仔仔一样,都是神的造物,要多多地疼爱他们呢。顾三爷原本想要多带孩子们几年的,他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教给孩子们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三年的初冬时节,顾三爷却突然离开了孩子们。
那时候,大雪还没有封山,顾三爷领着孩子们,想赶在下雪以前多采一些野果子,做孩子们课间的嚼头。有一天,他们在一道岩壁旁发现了一株红红的醉浆果。由于经了霜的缘故,那果子红得发紫,看了叫人馋涎欲滴。但,因为地处险要,采摘不便,很难近身,顾三爷只好眼睁睁地带着孩子们离开了。然而,孩子到底是孩子,一边走着,一边回头恋恋不舍地望着那红艳艳的果子。看着孩子们贪馋的眼神,顾三爷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于是,把孩子们安置到一个安全地带以后,他一个人回来采摘醉浆果。谁知,刚采了几颗,顾三爷就一脚踏空,毫不防备地跌到了崖壁下。
看着向崖壁下一路滚去的顾三爷,孩子们一下子全都吓傻了,继而本能地哭喊起来。萝卜虽然是个憨子,但到底身手敏捷,他一边喊着,一边第一个冲下山崖去。名叫土豆的小侏儒比别的孩子大几岁,首先灵醒过来,一路哭喊着飞奔回村子里叫人去了。剩下的几个孩子也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向山崖下奔去。当孩子们赶到顾三爷身边的时候,顾三爷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是微眯着一双眼睛,痴痴地望着围拢在他身边的孩子们。孩子们左一声右一声地叫着:顾三爷,顾三爷!听着孩子们急骤的呼唤声,顾三爷的嘴唇轻轻地嚅动了一下,脸上现出一抹慈爱的微笑,然后,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村里人赶到的时候,顾三爷的身子已经差不多僵硬了。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回村里,穿上寿衣,殓进棺材里,然后埋在了距村子十里开外的岭坡上,那里是顾家祖宗的老坟场。
顾三爷走了,再也没有人教孩子们识字念书唱儿歌,也再没有人给孩子们讲故事了。然而,孩子们牵了小牛犊或是羊羔羔出来吃草的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聚拢到核桃树下的小学堂里:他们用过的石板和木墩墩还在,屋角的炉塘还在,炉塘旁边那个为獾仔垒的小窝窝也还在。然而,他们的顾三爷却是不在了。好长一段时间里,孩子们都无法接受顾三爷的离去。他们下意识地到处寻找,天真地幻想着,顾三爷是躲起来跟他们捉迷藏哩。他们寻啊、觅啊,然而,哪里都没有顾三爷的影子。寻不到顾三爷,他们便日复一日地守候在核桃树下,迟迟地不肯离去,有时候一等就是一整天。
大人看孩子们可怜,只好一而再地直截了当告诉孩子们:顾三爷死了。以前孩子们对“死”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现在,他们渐渐地懂得:“死”就是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再也不回来了。这个事实虽然很残忍,然而,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慢慢接受了,不能接受的只剩下一个人:那个名叫“萝卜”的智力残障孩子。
萝卜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脑壳子就坏掉了。十几岁的时候,又父母双亡。一个傻孩子,四不沾、八不靠的,活得跟孤魂野鬼差不多。村里人这个给他一只馒头,那个给他一块地瓜,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地挨着,进了顾三爷的学堂,才算过了几天知冷知暖的好日子。别的孩子放学回家时,顾三爷总是把他留下来,和自己搭帮吃饭睡觉,就像爷孙俩一般,他对顾三爷更是特别地依恋,一时半刻都不舍得离开。现在,突然之间见不到顾三爷了,他着急得坐卧不宁,如同吃奶的孩子突然失去了娘亲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烦躁不安地四处走动,饭不肯吃、觉也不肯睡,失魂落魄地从村东游荡到村西,又从村西游荡到村东。像瞅地猫一样,这里瞅瞅,那里瞧瞧。村里人告诉他说:不用瞅了,顾三爷死了。他听了却是无动于衷。显然地,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死”。后来,他就突然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旮旯。一个傻子,又没有亲人,不见了也就不见了,大家也没怎么在意。以前他也走失过,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回来了。这时节,村人的注意力全被一个可怕的“鬼”吸引了去。
闹鬼的事情是从刘老四那里传出来的。刘老四是个老豆倌,专门收了豆子磨豆腐。黑下里把豆腐做好,白天里担到集镇上去卖。由于集镇在几十里以外的埠子上,他卖完了豆腐以后,往往要披星戴月地赶了夜路回家。有一天,他比往日里回来得更迟一些,走到村后的岭坡上,影影绰绰地看见一个黑漆漆的鬼影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顾三爷的坟头上。他吓得一路狂奔回村里,鞋子都跑丢了一只。
以后,又有几个人黑下里在村后的岭坡上见到了鬼。说那鬼披头散发、张牙舞爪,状如妖魔,时而在山林里狂奔,时而一动不动地蹲着,夜半时分还会发出凄厉的怪叫声。那叫声像悲伤的狼嗥一样:呜——噢噢噢,呜——噢噢噢,连山里的鸟兽听了都惊悚不已,纷纷飞逃。村里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草木皆兵,而且那鬼故事也越传越神奇。后来,实在闹得风声鹤唳、不可开交了,村长只好带了一些胆大的年轻人去捉鬼。半夜里,随着披肝沥胆、撕裂长空的一声哀号,鬼影子如期出现了:大家点着火把一看,那“鬼”村里人都认识。他不是别人,正是失踪了多日的萝卜。
萝卜显然是把顾三爷的坟头当作了自己的家。他弄来一些秫秸秆子堆在坟头旁,做成了自己的窝。在窝里还有他吃剩下来的红薯头和野果子。他白天里出没在山林里找吃的,夜晚便宿在坟头上陪伴顾三爷。实在情不自禁、想念得慌了,便扯开喉咙号叫几声,可能是在呼唤顾三爷回来吧。由于寒冷,他的手指和耳朵上都冻出了结疙瘩连片子的冻疮,有的还化了脓结了痂,看上去惨不忍睹。
一个大活人怎么可以睡在死人的坟头上呢?大家责骂了他一通,然后把他强行拖回了家。然而,没过两天,他就又不见了。不用说也知道,他还是去了顾三爷的坟头上。大家只好再一次地把他拖回家。时近腊月,天气一日比一日地寒冷,眼见得大雪就要封山了。顾三爷的坟头位于高高的岭坡上,在寒风肆虐下,无遮无挡的,不把他拖回来,夜里下了雪,他说不定会被冻死的。真冻死了,谁负责呢?
村长恼了,气急败坏地提着他的耳朵告诉他:顾三爷死了。你再怎么守着他也活不过来!妇女主任则语重心长地哄劝他:孩子,顾三爷早已经死掉,埋进土里,变成一只地瓜了。你就是守到猴年马月,他也不会出来跟你见面了。村治保主任是个急性子的年轻人,他早就对萝卜不耐烦了,恶狠狠地吓唬他道:你守在这里吧。到半夜里,顾三爷变作一个厉鬼出来,非掐死你不可。村里的小学女教师循循善诱地教导他:萝卜,你知道什么是死吗?死就是再也不会醒来,再也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了。人生在世,终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一个傻子,跟他讲什么鸿毛泰山,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没等女教师说完,村长就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直截了当告诉萝卜说:死就是钻进地里,再也不会爬出来了。
然而,事情却是出乎意料地棘手:萝卜由于是个傻子的缘故,无论人们讲什么道理给他听,怎样地威胁和恐吓他,他都油盐不进、刀枪不入,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死”。他固执己见地认定:顾三爷是躺在土里睡觉呢,睡醒了就会出来跟他说话了。兔子、松鼠还有蛇,到了冬天不是都要躲起来睡大觉吗?他一意孤行地守候在顾三爷的坟头上,寸步不肯挪窝。把他拖回来一次,他逃跑一次。拖了几回以后,大家就都不愿意再拖了。这么冷的天,待在屋子里还不受用哩,谁愿意老往深山野地里跑呢?顾三爷的坟头距离村子好几里远呢。再说,傻子又不是小孩,十七八岁的壮小伙子,不仅力气大得很,而且壮得如同一头牛,两三个人都拖不动他。
拖不动就不拖了。村长命人扛来了许多的秫秸秆子,就在顾三爷的坟头旁边替萝卜搭起了一个严严实实的窝棚。然后,又动员大家给他拿了一些吃的来,这样,萝卜就不至于冻饿而死,村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后来日子一久,人们便渐渐地把他忘了。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屋里屋外、远愁近忧的,各自都有一摊子的事务要忙活,谁会整天惦记着一个傻子哩?
冬去春来,仿佛只是一恍之间,几个月的光景就过去了。村长的老娘害有寒痨症,每到春天就要发作。有一天,村长偶然到村后的岗坡上去为老娘采挖药材,忽然心血来潮地想去顾三爷的坟头上看看。于是,便穿过几片山林走了过去。仔细一看,他吃了一大惊:只见顾三爷的坟头上结满了肥肥壮壮的南瓜。那些南瓜一个比一个大、一只比一只圆。有的像牛头,有的如同羊肚子。萝卜正弯着腰低声呢喃着跟南瓜们说话呢。他无限怜惜地抚摸着一个南瓜说:顾三爷,你渴了吗?不等南瓜回答,就给它浇上满满一碗水。浇完了,他又捧着另一只南瓜问:顾三爷,你饿了吗?然后,就拿一些羊粪蛋子埋进南瓜的根部。
显然,这些南瓜全是萝卜种出来的,在他的眼里,坟头上结出来的这些南瓜就是顾三爷。顾三爷终于从土里钻出来,跟萝卜见面、跟萝卜说话了。这真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村长看看低头忙碌的萝卜,再看看那些圆滚滚胖乎乎的南瓜,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末了,低沉地叫了一声:孩子。眼睛就慢慢地湿润了。
【作者简介】傅爱毛,女,大学本科毕业,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课程进修班。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绿色女人》等,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近二百万字,其中有多篇作品被多种选刊转载,小说《私奔》被翻译到美国,小说《小豆倌的情书》入选2004年度小说年选,《嫁死》、《长在眼睛里的翅膀》等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现在郑州市文联创研室工作,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