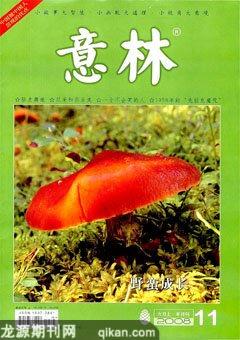卢克索,那个被祝福和诅咒的城
叶细细
经过十几个钟头的飞行,抵达卢克索机场。出了机场,我就直奔卢克索神庙。这里空气干燥,太阳极为热烈。从中国北方的一月一下子跳跃到埃及的炎炎烈日下,似乎一时无法适应。
也难怪。卢克索有个虚幻的名字:Thebs。意为被祝福和诅咒的城。如今的卢克索前身是底比斯,公元前27年的一场大地震让它变成一片废墟,而卢克索就建在这一片废墟之上。
卢克索神庙是底比斯主神阿蒙的妻子穆特的庙宇,高耸的方尖碑,纺锤形巨大石柱,散落的石雕和壁画,让生命在它面前如此渺小。
在历史留下的遗址里,偶尔可以闪现一两个穿着长袍包着头巾的埃及“法老”。他们皮肤晒成黑褐色,眼睛大而深幽,睫毛浓密。我举着相机,一阵狂拍。拍完每一处场景,才想到还没人给自己拍照。举目四望,正寻觅中,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要我帮你拍照吗。
眼前的男子。穿牛仔裤和运动服,但长相分明是当地人。20出头的样子,很黑的皮肤,眼睛大而明亮。
四目相视,觉得这个人好像认识?他只是看着我笑,牙齿很白。很放心地将相机交给他,心想,他是当地人吗?为什么不穿长袍子?
他举着相机,专注地为我拍照,拍完,递相机给我时说:平日不来这儿的,帮一个生病的导游朋友临时带团。说完指指他的团队,又指指手表说:只有15分钟就集合。
我问了他一个傻问题:你们守着卡纳克神庙、卢克索神庙,会不会在这样的文化里找不到现今的生活?
他看我一眼间:你是中国哪里的?
西安。
如果我没记错,那里有兵马俑。那你们是不是每天抱着兵马俑过着唐朝的生活呢?
他说,其实,卢克索人过着半是古代历史半是现代文明的日子,守望着漫长的文化遗址却也想穿西装。
简短的交谈,感觉他知识渊博,如果此行能多与他聊天,定然会对埃及有更深刻的了解。但贸然相约又不是他带的团,显然欠妥。这时,他看看表,说集合时间到了,道了再见,转身离去。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和他还会有下文。果然,像是听到我内心的想法,他走了几步忽然扭头问我:你住在哪里?
我不知为何会信任他,也或者在异国他乡,孤独变得很强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声地告诉他旅店的名字。他听我说完,笑笑。转身走了。
卢克索的黄昏来得晚。俯在阳台上望过去,异域感觉很强烈。窄小的街道曲径幽长,一队马车从远处嗒嗒而来,突然就想起郑愁予的诗句:“我嗒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马车上,坐的是西方来的观光客,他们在马车上兴高采烈,大声说笑,看起来如此快乐。我被这样的情绪感染,很想立刻奔下楼去,搭乘上马车,将卢克索的街巷尽收眼底。
奔进浴室,洗了个热水澡,换了清爽的水蓝衬衣,牛仔裤,重新梳好发辫,一天的劳顿也暂时消失。
奔出旅店时,夜色就要降临的样子。没想到,一出门,白日交谈的卢克索男子就在门口。我还是有些意外。他看见我。两眼闪亮,对我说,正考虑要不要进去查你住哪间房子。怎么,要出去吗?
想去哪儿?
我心内喜悦,说,我想坐马车。
他听我说完,急忙转身招呼一辆马车过来。马车夫是十几岁的大男孩,一边招呼我们上车。一边问:要不要去巴扎?
卢克索男子知道我不懂,为我解释,说巴扎是他们这里的集市,我们随便看看街景如何?
也正合我意。于是他用阿拉伯语对马车夫说了一句话,车夫便扬起马鞭载我们穿行在卢克索的街巷上。
聊天中知道他的本国名叫阿巴,还是个单身汉。
马车跑了20分钟后,阿巴就高兴地哼起歌。我听不出歌的名字,但异国情调很足,欢快中带着绵长的忧份。歌唱到一半,阿巴忽然抓起我的手,说让我与他坐在前面一起看街景。
阿巴问我中国的生活,我答得琐碎,也问他当地的生活情况。他说自己有个纸莎草纸店,主要靠卖画为生。说到这里,他提议去看看他的店铺和那些美丽的画。
我见答应了。
推开玻璃店门,那一墙的纸莎草纸画让我心内震动。颜色绚丽,绘工细致,仿佛那五千年的时光都被一笔笔绘在草纸画里,让我怎么也舍不得移开目光。
阿巴在灯光下,仿佛注入一种魔力,他给我讲纸莎草纸画的制作:很繁琐的。将纸莎草用刀切成细薄的片,浸在清水里6天后去除里面的糖分,然后将泡好的纸莎草薄片压在机器下6天,排干水分晒干可用来作画。
他拿起一张纸莎草纸画,让我看上面的彩绘画,说,都是一笔笔手工绘的,很珍贵。那一刻,我想起中国古老的戏衣,低调的奢华。
我在阿巴的店里待到很晚,走时,要买一幅。他却将一款绘有伊茜丝神话的纸莎草纸画取下来。
在那一刻,阿巴的眼睛特别明亮。我太明白这明亮的眼神意味着什么,但也是有些不肯相信。
从阿巴的店铺里出来,我们都变得沉默。已过了午夜11点钟,白日喧嚷的店铺都已关门,四周静谧。走到一半路,阿巴忽然拉起我的手,我没有挣扎,任他拉着。
阿巴的手如此温暖,也许我们的灵魂在前世就已相识。有些_人一天相见,胜似一生。想到这,不知为何,我心里忽然异常伤感。
阿巴感觉出了,将我的手拽得更紧。
几分钟的路途异常短暂又异常漫长。在旅店门口,他止步并没有要求上去,只问我:明天去哪里?
我说,不约看能不能见到。他笑,看着我进旅店。我飞快地跑上楼,开门进房间,跑到阳台上,往下看,阿巴还没走。他抬头看见我,对我招招手,在夜色里大声说,明天见,明天我们一定还会见到。
隔日一大早,我去了帝王谷,
64座墓穴,我看了3处。太阳比昨日还大,皮肤在烈日里显得异常干燥。在这荒芜又逼仄的墓穴里,我没有见到阿巴。
最后一站去了帝王谷不远处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神殿,不可思议的是在这里又遇见阿巴,阿巴说,我有预感,你最后一站会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伊奈纳,他为哈特谢普苏特女王造了一座最华美的宫殿。这里也是情人的宫殿。
我听着阿巴的话,眼睛蓦然潮湿,但内心漫溢着欢快。阿巴走过来,再次拉着我的手。我与他十指交缠,往前走着,心里还是有着小小的震动,身上冒出汗来。他是喜欢我的,我也是。可是我们没有未来,所以心里会有悲伤。旅途中,我们只是彼此的过客,我回中国后,一切都不复存在。
那晚临别,很久我都不能入睡。恍惚中我在梅农神像前。周身一片荒漠,我听见了梅农神像的哭泣声,我看见阿巴闪亮的微笑。忽然就醒了,原来不是梅农神像,而是邻街传来的夜半歌声,缓慢悠长的卢克索歌,喑哑地飘荡着。黎明初醒。我起身收拾行李,我要赶往去罗马的大巴,自此与阿巴不再相见。我们留给对方的,这一世只有两岸莲花的纸莎草纸画,和宝黛内画的中国鼻烟壶。来生凭着这点仅存的记忆,不知是否还会记得对方。
此时,卢克索在我眼中如此不真切,想起初见它时的感觉,就如海市蜃楼的一个小镇,阿巴消失在天亮之后。
(归雁生摘自《爱人》2008年4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