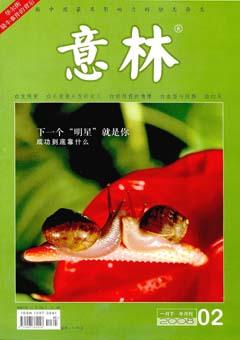杀生
薛喜君
去年冬天,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让我置身到菜市场的那个角落。角落里有些窝风,风就像刀子一样肆意地剐割着我的脸,我就鬼使神差般地退到那间杀鸡宰鸭的作坊里。我谦卑地向正在给鸡煺毛的胖女人点点头,“外面太冷,我避一会儿风。”女人宽怀地笑了。一口大铁锅里热气氤氲,一个穿着胶皮背心的男人手里掐着一只鸡的翅膀,只一刀就让还咕咕直叫的鸡哑了声音,生命瞬间就消失了。啪的一声,男人把失了生命的鸡摔给胖女人。胖女人也是掐着鸡的翅膀在热水盆里均匀地浸了几下,只三五下就把一只毛乎乎的鸡撸干净了。又是啪的一声扔到另一个角落里。那里已经有好几只煺过毛的裸鸡,也许是刚结束生命,或许是刚从热水里捞上来,反正鸡的身上还冒着热气。从袅袅的热气中,我似乎看到了还残存的生命的气息。屋子里充满了血腥,地上的鸡毛和水掺和在一起,黏糊糊的,像踩在一堆烂树叶上。大概男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屠宰生命,他和女人有说有笑。他们谈话的内容大体是今年的鸡涨价了,一只鸡要比去年多卖十几元钱。他们脸上的褶儿被笑容堆积在一起,厚厚的。
杀生,男屠手和胖女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的胃不听话地翻腾起来,就往外走了几步,只借助一个用胶合板搭的“门脸”挡一下外面的风寒。顺着咕咕的声音我看见铁笼子里关了一只灰色的鸽子。于是,我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鸽子的眼神儿。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久久地凝望着,我突然发现鸽子具备贵族气质。和我对视的时候,它只轻轻地咕了一声,那样子像是怕吓着我。它的眼神儿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无辜,还有些许的哀怨——像一个婴孩,不,更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少女。它在跟我诉说什么?说前生?说今世?还是告诉我它面临死亡的心情?它一会儿可能就成为屋里那个男人刀下的死物,就会成为女人手里赤裸的怪物,也会被啪的一声扔到那堆肉里,然后和那些鸡一样,或红烧、或煮汤,成为饕餮者的下酒菜——我的心脏顿时像一匹奔腾的烈马,不由自主地出了一层细汗。我被那眼神儿打动了。我极想把它抱在怀中逃离这里。我试探着挪了一下脚步,接着我就放开脚步置身到寒风中——我是在逃离生命还是在逃离死亡?可我并没有解救那只面临死亡高贵且优雅的鸽子。难道鸽子的生命卑微,不值得我解救吗?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逃离。此后,无论多鲜美的鸽子汤,我都拒绝。而且一想到鸽子,我就充满了犯罪感,觉得自己比那个屠夫还恶劣,是对生命的亵渎。
据说,那些专门从事杀生的人,他在杀鸡的时候就说:鸡啊,鸡啊,你别怪,你是人间一盘菜。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在解脱自己还是在安慰鸡。也有人说,杀鸡其实是件善事,鸡会非常感激你。如果你不杀它,来生它就不能托生为鸡了。
鸡的生命真的如此卑微吗?有人杀它还要感激?
(尘中塑摘自《岁月》2007年第10期图/迟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