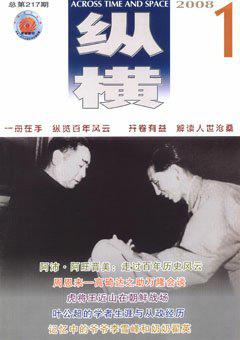悲剧的主角
方继孝
一
叶公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大藏书家叶恭绰的侄子,叶恭绰也以诗、书、画闻名于世。叶公超自幼失怙,由叔父叶恭绰抚育成人。受叔父的影响和熏陶,叶公超亦擅书法、绘画,长于墨竹,其所画兰蕙,潇洒如其行草书。
由于叶公超跟随国民党政府赴台,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后任“驻美大使”等职。在他去台后,祖国大陆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就很少了,其书画作品在大陆更是难得一见。近些年来,随着两岸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多,从大陆去往台湾的文人、政客的手迹在大陆的拍场上不断出现。这几年,我收藏的诸如梁实秋、台静农、谢冰莹、陈雪屏等信札、书法等皆得自于拍场。叶公超的墨迹,鄙寓入藏两件,其中一件是他写给梦谷、退村先生的信函二页。函云:
梦谷、退村道兄大鉴:关于省立博物馆租金事,弟昨函光夏厅长请其通知该馆将租金三千元及木架租金贰千元免去,由本金致送该馆员工茶水(费)一千元。顷已得光夏厅长复函照办。前收复函夹上,希与陈馆长洽说清楚,以便弟去函阎厅长道谢也。手此并颂艺祺。
弟叶公超顿首
十二月廿日
笺纸为黄维琩先生抚汉长乐未央瓦图,极素美。信中所云,我没有进行考证。不过关于入藏叶公超这通信札的经过,倒是值得说说的。这通书札是几年前在北京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的,或许是因叶公超的信札首次在北京拍场上登台亮相,加上叶公超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特殊地位致使,拍场上藏家对此进行的激烈角逐。最终这件藏品以高价被一买家竞得。我是参与竞争者之一,而且我的收藏专题也非常需要叶氏的手迹,但终因价格原因,中途放弃了。一年后,那位拍到叶公超书札的人因更需要我的某件藏品,主动提出与我交换。最终叶公超的书札入藏寒斋。之后,还是在这家拍卖公司,我又竞得叶公超所绘墨竹立轴一件。巧的是,前者书写时间为甲午年。而后者所绘时间为丙午年(正月初三所写)。都是马年所为,只是相隔了一轮12年。按农历推算,这个“甲午”年,是公元1954年,这年的5月叶公超始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正是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之时;而“丙午”年,是公元1966年,这时叶公超已从美国大使任上卸职五个年头了。
我们来看一看叶公超的人生经历,让我们感叹的是,叶公超曾经是一位具有多姿多彩生涯的学人。
二
叶公超,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叶公超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五四”运动时,他是“南开救国十人团”的核心人物。“五四”过后,家人怕他耽误学业,于第二年将他送往美国。在美国读完高中、大学后,他转入英国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深造,并于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叶公超离开英国,在巴黎大学作短期研究。
在英国期间,由于酷爱诗歌,他认识了著名诗人艾略特,并深受其影响。这也使他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艾略特的人,而他的学生赵萝蕤是第一个把艾略特的名作《荒原》翻译出版的学者,她在谈到叶公超时无不表示自己的敬意:“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只是凭自己的才华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10辆卡车也装不完的。”
1926年秋天,叶公超回国。一开始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兼任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编辑。由于时局动荡,叶公超于1927年春天南下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第二年又应胡适聘请,兼任中国公学西洋文学系教授。
1929年叶公超离沪北上,担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兼北京大学讲师。在清华和北大先后开设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范围之广已属少见,而其精湛的英文和文学修养在半个世纪之后还为学生所钦佩不已。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史上卓有建树、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季羡林、杨联升、吴世昌、王岷源、卞之琳、王辛笛、曹葆华、常风、赵萝蕤、张骏祥等,都是受到叶公超的赏识、关注和指点,从而在治学、创作或翻译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的。西南联大时期的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等都是叶公超的高足。
叶公超还是著名新月派作家。1928年,《新月》杂志创刊时叶公超还在上海,他是《新月》杂志主要发起人之一。《新月》的问世让他的研究创作进入黄金时代,许多文章就是这时候写的。他除了单独撰稿外,还主持编写《海外出版界》专栏。这一时期,他与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沈从文、林徽因等过从甚密。在《新月》后期,遇到杂志困难无人负责时,他临危受命,多次出任编辑(其实是主编),竭尽全力维护自由知识分子的这个文化阵地。这时期,作者有葆华(曹宝华)、中书君(钱钟书)、常风、灌婴(余冠英)、长之(李长之)、曦晨(李广田)、孙毓棠、卞之琳、杨季康(杨绛)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有人认为他们“大抵因投稿《新月》而成名”,这是实情。《新月》停刊后,叶公超与闻一多、林徽因、余上沅创办《学文》月刊。这个刊物的作者队伍基本上是《新月》的原班人马,也吸收了一批清华、北大的高才生,其中有钱钟书、季羡林、杨联升等人。该杂志出版到第四期,就因为经费问题和叶公超出国休假而停刊了。1937年5月,他又与朱光潜、杨振声、朱自清等推出了卓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他发表的《论新诗》一文,被誉为“中国新诗论的经典之作”。显然,与叶公超声应气求者,大多是新月派文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理想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或探讨学问,或携手办刊,其所作所为,堪称一帧帧五彩斑斓的文化图景。
叶公超也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令人刮目的是,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叶公超当时就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他认为:“我们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他在徐志摩死后撰文,认为徐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作。尽管他对左翼作家无好感,但在鲁迅刚故去时,他便写了《鲁迅》和《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两篇文章,肯定鲁迅的价值,肯定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称赞鲁迅的文字功力,认为“中国大环境未能让鲁迅静下心来,写几部有分量的书,如中国文学史之类,是十分可惜的”,并断言“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经长沙抵达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谈白话散文》、《文艺与经
验》等文,均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
1940年,叶公超弃学从政,步入外交界。自此,他告别了14年的教学生涯。他成就卓著的学者生涯也由此告一段落。
三
叶公超之所以弃学从政,这还与举世闻名的毛公鼎有关。
毛公鼎是中国2800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500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7000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时,其铭文价值可凌驾于《尚书》,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毛公鼎于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为代价购藏。
陈介祺,山东潍县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他的“万印楼”现为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陈列馆在其180周年诞辰时开放。陈介祺被公推为20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之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21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端方之女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陪嫁,而袁家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
1919至1920年间,一美商欲出资5万美元将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民国间曾任广东政府财政部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恭绰本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恭绰想在内中捞取好处。叶恭绰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待又是十几年。叶恭绰先是把毛公鼎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叶恭绰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恭绰寓所懿园。抗战中叶恭绰避之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他称病予以拒绝,足不出户。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生活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原来叶恭绰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闹得日方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恭绰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方的拘捕,在狱中受刑7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叶恭绰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经济实力已大不如前。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侄在外国留学,叶恭绰逐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商人陈咏仁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抗战胜利后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至陈咏仁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咏仁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历此风波的叶公超回到重庆后已无意并无法再回西南联大。不久,他被董显光邀到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由此而踏上仕途。
四
叶公超走下教坛走上政坛为许多人所不理解。王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13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
1949年叶公超到台湾,先后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和“资政”等职。1961年10月,叶公超被蒋介石政权从“驻美大使”任上召回台湾,起因是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入会案,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审度情势,认为“不能再坚持否决立场”,故投了弃权票。蒋介石认为应投反对票,为此叶公超即被召回“述职”。
被逐出政坛以后,叶公超的生活趋于平淡,他一度被梁实秋拖到台大讲课,但不久作罢。渐次他失去了当日的风流倜傥,到晚年更显老态龙钟。赋闲后他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且有许多独到见解。他喜画竹,友人多向他求画。他曾自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他又说:“书画不会得罪人,又无损自己,是好的养性方法。当一个人手执画笔的时候,世俗杂事都在九霄云外,宠辱皆忘。”在解嘲中显出豁达来。1975年,他辑《叶遐庵先生书画集》,请张大干先生为其作序。
叶公超晚年缠绵病榻,他在绝笔《病中琐记》中不胜喟叹:“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1981年叶公超逝世,享年78岁。
责任编辑韩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