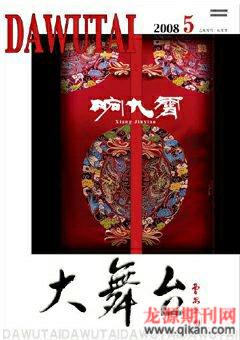《血色湘西》的叙事艺术
傅秀政
【摘要】《血色湘西》作为一部多题材的大片,可以从电视艺术的多个侧面研究它。本文试从文学的叙事理论角度,把影视剧作为一个文本来分析。认为,湘西叙事是美丽的传奇的,他们的世代纠葛、爱恨情仇,大有戏头可作,一旦将地域情结、家族叙事融入到时代背景里,以抗战这个大叙事来营构整个剧本,无疑提升了电视的文化层次,尤其提升了民族叙事的视野与高度,传达出湘西人民在民族大难来临之际,放下世代恩怨,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大主题。湘西的家族叙事与时代的抗日叙事共同构成了《血色湘西》的故事板块。
【关键词】湘西叙事 抗日叙事 人物结构 湘西味
一部《血色湘西》使向来以制造娱乐为看点的湖南电视一下子成为了文化提供商,成为了新型的媒体领先者。许多观众观看电视之后,说前面的爱情太好看了,后面的抗日不好。我在认真观看电视之后,觉得只有湘西叙事自然也是美丽的传奇的,他们的世代纠葛、爱恨情仇,大有戏头可作,很多观众可能就是受其影响而对前面有所偏爱。一旦将地域情结、家族叙事融入到时代背景里,以抗战这个大叙事来营构整个剧本,无疑提升了电视的文化层次,尤其提升了民族叙事的视野与高度。抗日叙事的加入使得人物的命运产生了转折,性格获得提升,放下家族的恩怨情仇,全民抗战,使剧本的核心从世代冤冤相报的复仇主题中抽身出来,专门着力于描绘湘西山民是怎样融入大时代潮流的,人性在面临历史的选择与责任时是如何升华的,这样的处理更有历史感、文化感。两个叙事一交织,就非常形象的传达出湘西人民在民族大难来临之际,放下世代恩怨,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大主题。于是,湘西的家族叙事与时代的抗日叙事共同构成了《血色湘西》的故事板块。
一、湘西叙事
《血色湘西》最大的看点有两个,一个是爱情,另一个就是湘西两大帮派“排帮”与“竿子军”从相互排斥到联手抗日的曲折故事。与《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湘西往事》以来的“湘西剧”相比,《血色湘西》没有花任何笔墨来描绘被大家所熟悉的“湘西土匪”,而是将着力点放在湘西人民的血性和慓悍上,把政治话语“剿匪”改变成生死爱情,把“抗日”这个政治话语改造成人性、人情。这是《血色湘西》叙事的总策略。
根据法国叙事学研究者热奈特的叙事理论,认为“叙述”(即叙事)一词实际上包括三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叙的是什么事,即所讲述的故事内容,二是用什么方式来叙事,即讲述故事的话语组织,还有一个是怎样叙事,即叙述行为。其中叙述内容包括故事(事件、情节、人物)、结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叙述话语包括文本时间、叙述视角(第几人称)、角色语言,叙述动作包括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预叙)。本文试从人物结构、叙述话语、爱情叙事几方面来分析湘西叙事。
1.湘西人物结构图:
湘西人物阵营里,以冲突来看,分两个系列,一是竿民,一是排帮;以年龄结构来看,分老中青三代,龙十四、五叔公代表老一辈,田大有、瞿先生、麻大扛把子作为中年一辈,穗穗、月月、石三怒、龙耀武、龙耀文作为年轻一辈,共同组成了湘西人物的阵营图。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这些人物的个性都很鲜明具有差异性,合起来又有同构效应;更有意义的处理还在于,人物的符号性特别强,每一个人既代表一种角色功能,又代表一种文化功能,都带有角色的文化倾向和文化符号,把戏剧性的需要与文化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成为2007年度影视剧中的文化大餐。
龙十四爷,继承祖训家法,维护着龙家的权威和竿子营的秩序,操纵着湘西的乡村政治文化,霸道、狡诈、冥顽不化,挑起事端坐收渔利,体现出湘西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劣根,然而观众却恨不起来,剧本在矛盾冲突中也刻画了他料事如神、重情仗义、明大理识大局的一面。最后在天坑岭这个祖宗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人物性格自身的逻辑实现了对日本的反抗。湘西人就是这样子的。田大有、瞿先生、麻大扛把子三人,一个是侠胆义士,一个是明理书生,一个是排帮头领,构成了湘西文化中的一武一文一邪,其中的武与邪,都是“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的勇者形象,却陷入世代仇怨之中,被乡村政治势力所利用而命丧黄泉,也许,只有文化才能成为乱局中的精神支撑。
穗穗与月月表层是舅妈姐妹,亲密知音,深层里却构成命运的对立,同样都面临磨难,一个豪爽刚劲,把握好了自己的爱情与前途,在共产党员童莲的带领之下,成长为抗日英雄,一个则陷入婚姻的泥潭,忍受着湘西传统文化中的野蛮、残酷与无情,尤其是遭受长达五年的软禁惩处,显现出这个封闭山区极端的落后性,成为妇女悲惨命运的典型化身,剧本给她身边安排一个憨憨的六伢仔,默默的关爱着她,成为审美效应中的一丝暖意。龙耀武与龙耀文两弟兄,从武与文的取名来看,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文化走向,在与穗穗的关系处理上,有点接近沈从文《边城》里翠翠与大佬、二佬。同是湘西优秀青年,而耀武更带有悲剧性,性情的冲动偏执招致命运的悲剧,初见穗穗时,让他在河里捞不着银锁、端午龙舟赛上急躁失败,到情仇报复致残、心理变态侮辱月月、伺机处理虎仔,烘托出湘西世界里的凄凉、冷酷、野蛮与荒僻。毕竟优秀片子是善于抖包袱、设悬念的,通过端午节上的信心威风、在瞿家和月月一起打桂花时的阳光可爱、天坑上主动请求走天坑的勇气担当、和穗穗一起打鱼嬉戏时的纯洁快乐,以及后来亲昵虎仔、炮轰日本鬼子、与月月最后的厮守与爱情哭诉等情节完成了他作为湘西硬扎汉子的壮烈与柔情,让那种有情无情的瓜葛在共同的民族抗战的前提下泯去恩仇,使爱情叙事与抗日叙事有机地整合起来。耀文呢,有文化有思想,对封建性的反抗代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立场,却显得些微脆弱,不被人理解,“天坑堵命”时,他说凡事不能用野蛮用武力来解决,却根本说服不了那根深蒂固的传统和规定。表面上让人觉得迂腐好笑,与湘西野蛮文化形成对立,背后却揭示了那个年代文化人的悲哀和无奈。走上抗战,成长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算是不错的出路。
2.叙述话语的湘西味:
电视剧的地域情结是浓郁的,在处理上,有意模糊了土家族、苗族、瑶族的区分,为的是强调“大湘西”概念,强调湘西的少数民族整体。可以说,湘西的汉语方言与土语是第一次在影视艺术里如此集中而浓郁的展现出来。有人评论说太粗野了,这部影视剧的特色之一就是将粗野之风上升到了审美的层面。“逮”字在文本中多次出现,以其形象传神一下子走红南北,成为了2008年的时尚语言。“逮”字起源于湘西少数民族的山林狩猎文化,然后拓展延伸到生活中的多个领域,作为动词不仅表示了动作与行为,而且还隐含着可期待的预见性结果。因此,对于比较开心、成功率比较高的那类事情,我们就说“逮”,“逮起”,“逮得”。人们发明言语活动就是为了叙事,这种话语结构是民族与地域文化的一种沉潜,作为历史的底蕴,这种话语结构为人物的相遇与碰撞提供了活动的场景,也就是说与场合是相宜的,是协调的。正如主角李桓(饰演石三怒)所说,那里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还要粗野。《血色湘西》打造的就是血性品格,就是粗野之美,与《恰同学少年》所追求的书生意气、雅致之美构成辉映,都是湖湘文化的风格体现。罗兰巴特说过:“不应该摘掉名词的语链,不应该拆开言语活动的语链:过分命名总是滑稽可笑的。”[1]因此,对于电视乡音,我们不是提出孩子式的问题:为什么?而是提出古希腊语的问题、意义的问题,就像所有的东西都多少带有意义那样:这意味着什么?想办法把文化、历史、观念的东西变成描述、变成画面、变成细节、变成话语,这就是电视所要做的事情。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里也论述到:“在英国,电视来临之后最非同寻常的发展动态之一,是地区方言的复兴。”“这一变化是我们时代最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之一”,“电视来临之后,方言被认为能提供深刻的社会纽带。”[2]这种纽带不是靠规范语言来建立的,恰恰相反是靠方言,而所连接起来的是本土与外面的现代化世界,是历史与当下。电视传媒的效果就是这么奇妙。
3.爱情叙事:
在湘西世界所叙的两大事件中,爱情比复仇更为抢眼。我们就以爱情叙事为例。
首先是爱情的传奇性。穗穗的身边安排三男,耀武与三怒的争斗构成显性冲突,似乎耀文的参入有些牵强,可细看来,穗穗与耀文构成了爱情的隐性叙事,以端午节女年满十六拜傩公戴银锁、男满十八行成人礼戴耳环的习俗为线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并处理为暗恋,由爱情升华为同志之情。尤其让观众称道的穗穗与三怒的爱情,两个相爱的年轻人隔着世仇和杀父之仇,其实有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味道,但表现得荡气回肠。石三怒,慓悍、尚武、多情,一身正气,做事光明磊落,不会使阴招,重情重义。编剧让他生得黑黑的牛牛的,让他唱那么多的“情歌子”,让他为爱情而绝食、为出帮而遭乱棍、下火海、跳刀坑,让他天坑赌命为情而败,穗穗离开湘西时,让他快马加鞭奔驰相送,只有眼神,只有那把牛角刀定情物,却没有一句台词,让他为穗穗千里送去抗战物资,远远地注视着心爱的人。那种单纯、热烈与柔情、执着,简直就是一个为情作使的“初恋情人”形象,这个定位把握得很好。而六伢仔作为爱情的配角,只晓得躲在角落偷偷的爱,忍看心爱之人遭受凌辱却无能为力的弱者形象,与这个敢作敢为的情人形象构成对照。
其次,爱情的悲剧性。穗穗与三怒的爱情热烈得成为不可能,与锁师长的爱情处理,虽说有些我们熟悉的林道静式的爱情模式,将爱情抉择与革命道路处于同构同步的状态,就是说以嫁给革命者的方式完成女人的革命,观看起来有些不顺。但穗穗从一个为情所使的山民女儿成长为忧患局势的革命者,剧本安排她的这次婚姻失败,而在内心情感的归属上始终是石三怒,应该是一个圆满。让这些深爱着她的人都命丧战场,剩下她一个活着,爱情的悲剧性为影视带来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其三,人性、人情、伦理的美感。《血色湘西》以人情见长,以人物性格丰满而受到好评,它不仅把兄弟情(耀文与耀武、石天保与麻大拐)、父子情(麻大拐与石三怒、田大有与穗穗、瞿先生与月月)的家庭伦理美渲染到极致,就是仇家之间(田大有与麻大拐斗疯牛、上刀梯时的相救)的义气、友家(龙十四的喜饼对田大有,汪老板的鸦片对童莲)之间的阴毒,也处理得富于张力,魅力十足。价值的弘扬通过形式的设计与处理来实现,这样,就把艺术理论家贝尔的理论假设“有意味的形式”成功地化成了艺术操作。
二、抗日叙事
1.抗日同盟战线的构建:
分两个系列,一个是湘西世界,就是前面讲述到的三代人,另一个是童莲、锁师长、美国保罗,分别代表共产党、国民党、国际友人三个层面,构成了湘西以外的抗日联盟,这样的设置体现了编导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认识和对它的历史把握,湘西战场上的雷达保卫战作为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人类反侵略战争的一个有机部分。童莲在文本里充当故事的叙述者与见证人,同时也代表文本所蕴含的政治主题与意向,这种处理在中国应该是比较容易通过检审的。作为故事叙事者,更多的展示她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别人”的故事,而不是过多的揭示这个人物的心理动态与性格的多面,因此,剧本在童莲的身世、家庭、性情诸多方面采取了模糊处理,这是对的。模糊了她一个,却敞开了许多人,通过她叙述了整个湘西世界,她是把时代的信息带进封闭的湘西世界的第一人。而锁师长这个“有血性,有个性”的东北汉子与湘西血性汉子有着相似之处,面对这样的异质同构现象,请允许试作这样的想象性发散:血性不仅是湘西儿女的宝贵品质,也是我中华的宝贵品格。在影视艺术史上,可以说,把国民党基层官员塑造得非常大胆、多面,富有人性,应该还不多见。保罗作为慈善机构的一员,在无情的战斗中亲历了日本的不人道,在轰炸与死亡面前,穿起空军制服,成长为保卫雪峰山雷达站的科技人才,也具有代表性。
当然,中心人物依然是湘西阵营,采用的也是“成长法”。人物原本均是按着自己的性格过着湘西竿民的简单而强悍的生活,追求着自己的爱情,恪守着竿子营的规矩。只有当石三怒在目睹了日寇的残暴、终于将自己的狭隘完全抛却,毅然跪却在曾被他视为情敌的锁师长遗体面前的时候,当他轰然起立将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去遮挡枪口射向穗穗的子弹的时候,我们才会为他的大义凛然、为他们壮丽的爱情而扼腕叹息;只有当月月不顾一切地推着龙耀武的轮椅和日寇搏命、而龙耀武却还在骂着她“骚货,快点”的时候,当龙耀武最后终于搂抱着月月、唱着甜美的山歌在大火中化为一炬的时候,我们才仿佛真正地理解了湘西竿民的性格;只有当龙十四太爷抱着心爱的重孙子虎崽,从容地将日寇引向了远离雷达站的红石林的时候,当他就像平日里哄其入睡似地跳入深不见底的天坑而虎崽也露出了安然的微笑的时候,他那曾经致使田大有丧命的奸诈、曾经使月月饱经苦难的顽固,似乎都已成为了可以原谅的瑕疵,电视观众记得的只是他那和先人一样的忠烈。[3]
纵观湘西系列与抗日系列,网上有人评论,说整部戏看下来,基本上没什么很坏的人,小日本除外。这也是这部戏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坏”的处理,我觉得,编剧把“坏”打造成了人物性情组合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本质,让“好”与“坏”在一个人物身上呈现出张力,如龙十四的奸诈顽固、耀武的偏执变态,但不影响整个人物的英雄血色,突破了惯常的好人与坏人的区分,应该说是比较人性化的“丑学”体现,是张力美学的成功实践。只有穗穗,是理想中的核心人物,被编剧打造成为中国的贞德,湘西的贞德。
2.爱情与爱国的水乳交融:
这部戏的爱情非常亮眼,以至很多观众说“好看”。当然,这部戏剧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抗战,主要写穗穗、耀文他们在战争中的成长,以及九弓十七寨的联合抗日。我们曾经愚昧过、封闭过、落后过,身居山林不知今夕何夕,是抗战使湘西明白了国家与中国人的概念。电视剧运用细节、场景将这套抽象的概念话语具象化了,以虎仔读书、虎仔与太阿公关于“中国人”的对话为线索,体现了瞿先生、龙十四为代表的湘西男人的爱国精神,发展到后面,瞿先生与日本军官关于德信的辩解、龙十四爷抱着心爱的重孙跳进天坑,完成了民族史上的忠烈。
爱国精神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叙事,一是正题抗日,另一个则是历史叙事——屈原、戚大帅、葛大帅的故事。屈原精神通过这些场景与细节来体现:端午节的请屈子、颂祭文、拜屈子,《橘颂》、《国殇》之文在青溪书院的吟诵以及战场上的配音;戚大帅、葛大帅也是中华民族危难史上湘西血性的体现,这些材料将地域风情与大中华的国家情结相结合,很好的与当下抗日主题衔接了起来。当年屈原的《国殇》是一出为国捐躯的将士祭歌,《血色湘西》承接了屈子精神,是为40年代抗日救亡战争湖南湘西一带为国捐躯的将士和民众,谱写的又一首祭歌。全民抗日,既是我湘西民族光荣传统的延续,又是时代局势的催发,为我民族长了气、提了神,并对惯来定势思维中的湘西土匪形象进行了颠覆,构建了另一个“想象性”的世界。穗穗与石三怒的血性爱情与全民的抗日爱国如此交融,用形象、画面、细节等手段做足了来揭示主题。
3.抗日的预叙:
所谓预叙,属于叙事策略中的一种,就是在情节发展中把将来发生的事预先描述出来,其实就是灰蛇长线、预埋伏笔的叙述手法,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事件的全部过程,维持影视剧情发展的流畅性。以十九集穗穗离开湘西为界,前十八集在爱情、复仇的主线里,就埋下了伏笔与预叙。在第一集里,从省城读书回来的耀文给瞿先生交流抗战两年来的情况,说快打到长沙,逼近湘西了;童莲为开辟雪峰山运输线,以旁白的形式将外面的血与火跟湘西的宁静、恬美相对比,不忘党的嘱托;与穗穗卧谈,宣传抗日,激起田大有“闻鸡起舞”;在寨主大会上展示图片,进行抗战宣传等等。因此,作为抗战叙事也是比较顺畅自然的,不至于“不好看”吧。
作为普通观众,可能对于爱情这个亘古的人性话题有所偏袒而造成对抗战这个历史、政治话语重视不够。通过分析,我依然坚持认为,湘西叙事自然是美丽的传奇的,他们的世代纠葛、爱恨情仇,大有戏头可作,一旦将地域情结、家族叙事融入到时代背景里,以抗战这个大叙事来营构整个剧本,无疑提升了电视的文化层次,尤其提升了民族叙事的视野与高度。
当然也存在一些缺陷,讲起来不是主题内容的范畴,依然是叙事的问题,艺术传达的问题,如田大有的自杀过于突兀,戏还没做足,龙耀文的死而复活,缺少伏笔,穗穗与耀文之间的情感定位、穗穗与锁师长的婚姻有些草草,一号男主角三怒在抗战中的戏过少等等。电视是一门综合艺术,包括文学、声音、舞美、动画、摄像等等各个方面,《血色湘西》在这些方面都打造得比较成功,为我国从事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如此多题材的一部大片,做到了历史的真实性、思想的深邃性与艺术的感染力,即史、思、诗的统一,不啻一部精品。
注释:
[1]【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2页。
[3] 魏威《壮哉,湘西竿民!——电视连续剧〈血色湘西〉观后》,《文学报》2008年02月21日,第7版。
另外,《血色湘西》研讨会实录,http:/www.sina.com.cn,2008年 01月 11日16:03,新浪娱乐。相关表述有所参照。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