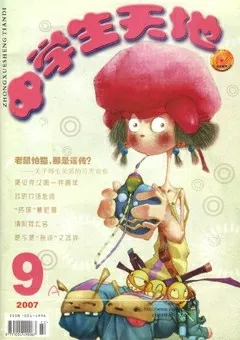西非两海岸
惊涛拍岸的大西洋边,非洲西部,有两个著名的海岸。因为出产象牙和黄金,它们分别叫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它们一个浪漫,热情洋溢;一个内敛,朴素深沉。它们紧邻着,碧玉一般,镶嵌在几内亚湾。
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现在叫科特迪瓦。曾经的首都、现在的经济中心阿比让是西非最繁华美丽的城市之一,人称“西非巴黎”。
但很多人还是只知道象牙海岸,虽然因为人类的猎杀,现在这里已经没什么象牙了,只有海岸。
游人常去的海滩有大巴萨姆和阿西旎。
大巴萨姆是殖民时代科特迪瓦的首都。法国人当年就是从这里登陆的,从此,那里开始繁华。后来瘟疫来了,这个城被毁。后来又重新成为旅游胜地。一家家旅馆,既富非洲特色,又很现代。我们在海滩上烧烤,踢足球。
阿西旎比大巴萨姆景色更丰富多彩。前面是蓝色的海,后面是青透的湖。乘着小舟或快艇,左一望,右一望,景色迥然不同。阿西旎海的颜色跟大巴萨姆那种湛蓝不同,蓝中透着翡翠般的碧绿色,有点像海南的亚龙湾。这里有一家著名的地中海俱乐部,其豪华堪比泰坦尼克号,但早关了。眼下,这里将近一半的俱乐部、酒店都已关门,因为这个国家的上空正笼罩着内战的阴云。
返回阿比让时途经一座军营,军营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几天前,它遭到了不明身份枪手的袭击。
望不到头的椰林坠着温暖夕阳,高大的木瓜树下,踢球的孩子正在散去,奔回各自的家,留下这热带寂静的街道。
在阿比让,我认识一位13岁的男孩子瓦勒。瓦勒父母双亡,在街头以擦鞋为生。我的朋友在阿比让开餐馆,卖的春卷很受当地人欢迎。瓦勒来过三次,每次都只买一个春卷。“一个?怎么给他炸呀?”朋友用中文跟我说,然后告诉瓦勒:“今天没有了。”
我托人给瓦勒送去一些春卷。瓦勒跑来找我:“送春卷的人说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小姐送的,那一定是你了。”银月闪烁下,瓦勒激动地说。
瓦勒后来又来找我,送菠萝给我。我回赠给他一支笔,这让非洲孩子普遍喜欢的礼物在让瓦勒欣喜的同时,也让他悲伤,他嗫嚅地说:“我不会写字。”
局势越来越紧张,街上到处是开来开去的军车。那天,我和朋友在街上匆匆行走,看到瓦勒在一辆军车上向我们挥手。我们走过去,他敏捷地跳下车。
“你不怕死?”朋友小心地摸了摸他身上的AK-47。
“这下我有饭吃,也有衣服穿了。”瓦勒高兴地笑着。车上还有几个童军。他们握枪的手,是孩子细滑的小手,不是军人粗糙的大手。他们黑黑的眼睛,是孩子纯真的眼睛,不是军人漠然而冷酷的眼睛。
椰子树的一抹阴影横在阳光下他的脸上。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瘦瘦的手腕。
“等你回来,免费给你吃春卷。”朋友说。
“那我一定回来。”瓦勒咧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
一定能回来吗?如果会,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会用满不在乎的语调讲述血腥的杀戮吗?会有驱不走的哀伤吗?在我们头顶上,两架运输直升机轰鸣着盘旋而过。
“瓦勒,该走了。”一个年纪比他稍大的穿军装的孩子喊道。“库迪奥越,我们的头儿。”瓦勒说完,跳上军车,向我们挥手。库迪奥越,还有那些童军,都向我们挥手。这是分别,还是永别?
科特迪瓦,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和出口国,“黑非洲的奇迹”,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比中国发达得多的美丽国家,因为内战,已经南北分治了。我在隆隆的坦克声中离开了科特迪瓦,我把我在这里所见到的和所经历的写进了我的新书《遗失象牙的海岸》。
黄金海岸
阳光打在白灰剥落的墙上。两个围着花布的黑人靠墙而坐。他们身体健壮,目光却略显呆滞。那是饱受灾难、忍受贫穷的目光,从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那儿传下来的目光。只有远处,那草地上玩耍的孩子,才有不谙世事的调皮,黑得发亮的脸上有阳光的灿烂。
海鸥舒展双翅优雅地飞过。它们是那么的自由。
脚下是蔚蓝色的大西洋。阳光下岸边卷起的浪花白得耀眼,而岸边的巨石城堡里,却是深深的黑暗。
加纳,因盛产黄金,为欧洲人所垂涎。1481年,葡萄牙人艾尔米纳率船队在这里登陆。次年,开始修建城堡。以此为基地,葡萄牙人大肆掠夺加纳的黄金。这个有古老历史的西非国家,开始成为“黄金海岸”。
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殖民者发现,贩卖奴隶比贩卖黄金更有利可图,于是万恶的奴隶贸易开始了。城堡成为奴隶市场和奴隶运往美洲的中转站。先是葡萄牙,后是荷兰、英国,在加纳5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一共建造了42座奴隶堡。
在奴隶堡深深的黑暗里,仅仅几十平方米的空间,往往同时关押着几百名奴隶,里面潮湿,充满恶臭。患病、受伤的奴隶被抛进大海。敢于反抗的,则被打入带有骷髅标志的“死牢”,被吊在大铁环上鞭挞,或在非洲的烈日下曝晒。专门关押女奴的牢房里,有一架楼梯直通总督房间,不难想象这背后有怎样的罪恶。
加纳一带的克罗曼丁人和弥纳人,体格好,能吃苦耐劳,因此售价最高,成为被捕捉和贩卖的主要对象。
被强行抓来的,被骗来的,被族人出卖的……反正,进来的就再也出不去了。
地牢有狭窄的通道通向大海。涨潮时,奴隶们爬着出来,然后被驱赶进奴隶船,在大西洋上开始漫长可怕的旅途。船舱低矮闷热,缺乏淡水,因为疾病、饥饿,死者十有六七。奴隶船在大西洋上浩荡前行,后面跟着食人的鲸鱼群。
奴隶市场,就在天井一端的教堂里。两瓶酒、一袋子弹就能换取一个奴隶。这教堂也是总督祷告的地方。不知道他会祷告些什么,更不清楚当他祷告时,那耶和华在不在听。当一个黑人的死去和一只小虫的死去根本没有区别时,还会不会有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从15世纪中叶到奴隶贸易被废除的1807年,非洲因奴隶贸易而损失的人口达1.5亿。他们之所以被捉,除了武器落后外,还因为他们的朴实。当入侵者到来时,他们就站在两侧,惊奇多于惊慌。他们实在不清楚这些人来干什么,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
加纳的奴隶堡,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奴隶堡脚下,城镇早已发展起来。这里有繁多的木船,困顿的人们。
沙地上、大船旁的孩子,光脚或穿拖鞋的孩子,他们仍是贫穷的。他们向世界各地来的游客讨要小礼物,他们最喜欢的礼物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