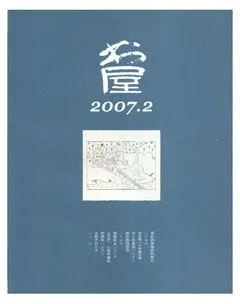一本旧书里的精神
书买得多了,有些也就永无出头之日。就如逝去的时光,不知道哪一刻灵光触动,才偶尔一念想起。
案头就有这么一本书,回想买书时光景,每有颇为自得之乐。书不厚,薄薄一小册,收录了殷海光、林毓生两位先生来往书信数十封,题为《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在我们的眼里,殷海光先生更多的是以一个锋芒毕露的斗士形象出现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他身上流淌着一股清明的理性潜流,而正是这一股潜流,成就了师生两代人的精神传递,实现了五四精神的历史传承与超越。
早在1955年,殷海光先生从哈佛大学访问归来,在台湾大学讲授逻辑课。作为学生,林毓生先生得以私下请益。殷海光先生坦诚相待:“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现在的水准,只能表达一些零碎的意见,系统性的、深入的理解,尚待将来。”这种判断是殷先生深信不疑的,在他后来给伍民雄的信上表达得更明了一点:“我所能够做到的,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引导大家打定基础,作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这种对时代的准确把握、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和对知识的尊重,使他变得坦然和豁达。他认为当下他所能做的是两项协助性的工作,即鉴别学术标准的能力和指明方向的能力。当林先生说他读历史的最大志趣是希望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时,殷先生指出需要做三项准备工作:求助于西方社会科学,反思五四,学好外语。
林先生说,这一番话影响了他的一生。正是在殷先生的指引下,他决定从自由主义入手反思近代中国历程。同时,他读了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萌发了异域求学,受教于哈氏门下的想法。这是他后来留学美国,求学于哈耶克先生门下的“远因”。
1960年,林毓生先生负笈留学美国,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博士学位,亲身受教于哈耶克、席尔斯、史华慈等著名学者。在他给殷海光先生的信中,那种激情洋溢的神情跃然纸上。然而,这种热烈的情绪很快转为探究的冲动和冷静的求知历程。林先生回忆:“在抵美以后最初写给殷先生的几封信中,对卓著成就的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动辄冠以‘大师’的头衔,这反映了当时颇受西方社会科学所提出的种种‘系统分析’之震慑的心情,而这种心情也意味着对当时国内支离破碎、迂腐而顽固的学术界的反抗。但随时间之流逝,心情也渐趋平静,我同时也逐渐研读了一些哲学、文学、神学与倾向人文的史学的典籍,发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因受其基本假定的限制,对人间事务的了解实在是有限的。”
这正是殷海光先生所要追寻而未实现的道路。在给林先生的信中,他说:“在两个多星期以前接到你的来信时,正好在午前,读了以后,兴奋得睡不着午觉。为什么呢?因为,从你的信中,我简直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在芝加哥大学搏动;你走的,正是我所要走的路子。怎么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呢?如果我迟生二十年,我简直要长一双翅膀来芝大求学呵!”
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这是林毓生先生是治学多年来的切身体悟和执著追求。不可否认,在这过程中,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呼声从未止息。但谁能否认,在冠冕堂皇的外壳下,隐藏着多少知性的傲慢。明白于此,才能体会殷、林师徒追寻历程的意义与价值。
当转于冷静之后,他们将承受着极大的寂寞,时代的和学术本身的,以及个人的。殷海光先生以沉郁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写照,写出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着自己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无疑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在寂寞与孤独中,他们捍卫着知识的尊严。
2006年3月2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上,一位白发苍苍的学者作了“学术是知识贵族的事业”的专题报告,在学术的领域里呼唤时代的知识贵族。他引用德国历史学家韦伯的观点阐明“贵族”二字的真义。在他看来,“贵族"二字不是指“远离群众”、“孤芳自赏”,而是一种不顾一切地遵循理智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是内化在血肉里面的一种切实信仰。这位学者就是林毓生先生。
林毓生先生曾说,哈耶克先生给他的是知识贵族的召唤。与哈耶克先生初次接触,林先生就感觉到了在其身上的那种贵族品质。“哈耶克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德奥贵族式的学者,货色甚硬,脑筋非常有力,上tutorial(导师课)课的时候,除了谈学问以外,一句闲话不讲,因此必须准备充分,否则几分钟就没有话可说了。”马克斯·韦伯曾说,如果大学不仅提供知识和方法,还提供信仰和理想的话,就超出了学术的界限,因为那是由个人来决定的事。这是对一个教师的最高赞誉,也是一项至高的要求。
学术是知识贵族的事业。在极大的寂寞中,两位先生捍卫着知识的尊严,以切身的践履使我们见证了现代中国两位真正的知识贵族。
他们视读书为神圣的使命,以身为读书人而充满无限的欢欣和自豪感。不屑于世俗的眼光,殷海光先生说:“不管我是否会成众矢之的,我依然认为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我既不赞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分子‘大量生产’的趋势。这是造乱!依此,我固然很穷,我认为在原则上书必须贵而且装潢高雅。这样方显知识尊严。这种想法真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但是,时宜是什么?我根本看不起时宜!”他满怀喜悦地宣示着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感谢上苍,我们居然是读书人,并且真爱读书,并且说到最后又是为读书而读书,真是有幸!”当一切成为一种信仰而深入骨髓的时候,寂寞、清贫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磨砺真金的火焰,升华了他们的生命。
求知的渴望对知性的追求使他们打破了身份和年龄的差别。先生让学生开书目,这也算是旷古奇观了。然而,发生在他们身上,只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敬意。寂寞与清贫中,他们自得地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的冒险”。
除了云集的大师学者外,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迷人之处,该是那种独特的教学培养模式了。由于只培养研究生和博士,每个学生都被视为未来的学者。在读书和研究领域的选择上,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有一项特殊的规定是必须完成的。在柏拉图《理想国》以降的西方经典著作中,委员会列出了一个书单,每一位学生必须在这个书单内选出自己的阅读书目。通常,这些书目都有十五六本。这些书必须为自己将来从事的专业领域之外的书籍。因为,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说,那是他的义务与责任所在。学生们将在一位一流的学者引导下逐一进行精读,并接受课堂上老师的发问和同学间的辩难。由于可选的书目有限,选的书基本都有几个人选,课堂上的辩难将是一道检验阅读质量的关口。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时除了严阵以待、如临大敌以外,实在别无选择。
这种训练,也许正是林先生后来主张的一种比慢的功夫。在他自己的书单上,就有柏拉图、修昔底德、莎士比亚、洛克、托克维尔、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名字。当时,系主任John Nef先生说:“Ours has always been an adventure in freedom.(我们的教育一向是在自由中的冒险。)”学术本身就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每个人都在求知的路途中。至于谁能达到一个完满的境域,那是一件无法预料的事。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更多的是一种本分。
从1960年入校,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林先生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从1963年准备选题,到1969年提交博士论文答辩,经过了六年时间。其间,冒险中的辛酸与寂寞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然而,那种冒险的渴望,却使他们沉浸在了知识的圣域中。林先生被殷先生称为是“小天窗”,每封信都要读上好几遍。“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当我收到你寄的书包,打开时,一阵一阵洋书的香味扑鼻而来。嘿!老弟,这种光景所给予这穷书生的快乐,你是不能想象的到的吧!”而异域求学,寂寞的学习生活中,殷先生的信也成了林先生的至宝。林先生能够“昂然保持原始的自我”,“表现着一种超越环境的气概”,这也可以说是一份重要的精神动力。
两位先生在通信中,热切的分享着新的发现和见解,互相印证和切磋。殷海光先生曾惊叹于西方人的认知能力,感慨“应该怎样急起直追才能探到世界学术和思想的高峰!”然而,最终他开辟出了一条“科际整合”的道路。以自己的行动,呼唤建立现代中国的“新史学”。旅途中,林先生既享受过莎士比亚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带来的知识的喜悦,也有徘徊于西方学理研究与中国历史的个人关怀之间的苦恼。然而,正是这种冒险使他提出了“有生机的创造性改革主义”,这一“开天辟地的创论”(殷海光先生语),走出五四并超越了五四。
一直以来,通与专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位读书人。许许多多的学者专家究心于此,试图做出自己的圆满解答。尤其是上个世纪,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和研究的细密化,两者的关系更成为学人们内心挥之不去的梦魇。林毓生先生以自己的体悟和在求学的经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Adventure in freedom[在自由中冒险]固然是一种冒险,但如在过程中随时conscious(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什么事,也不见得会弄得不知所云,况且任何一个新的discipline(学科)或new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一个学科新的分支)似乎都是由这样的冒险得来的。”
知识的探究本身就是一场知性的冒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先生的解读为这一探险之旅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
贵族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也不愿将这个称号妄加于两位先生身上。但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这样一种精神的涌动。殷先生认为读书是知识贵族的事,林先生宣扬学术是知识贵族的事。两字之差,反映了两代人的传承,但他们那种对知性神明的信仰是一致的。殷先生说哈耶克先生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林先生认为这是长期强烈的知性生活的结果,他的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在殷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另外一种体现。
林先生说:“与殷先生接触,无论过从如何紧密,彼此之间总有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感。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他欣赏或憎恶一个人,是与他觉得这个人对中国的前途是否已经或可能有所贡献有关。殷先生生活情趣高,道德想象深远,感情真挚而丰富,和他相处自然会感到浓郁的人情味与‘奇理斯玛的’(charismatic)震撼。不过,这一切皆因志同道合之故,极少有个人‘私’的成分。”他又秉承了传统中国士人精神,保持着“在公共领域之内的道德完整性”,作为一位“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是经过了转化的。正如殷海光先生自己所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把尊重‘群己权界’作为基本的原则。我同业师金岳霖先生相处七年,除了谈学问外,从来不谈私事。除非对方提到,彼此没有问过对方的个人问题。”这中间没有知性生活的陶冶,没有对知性神祇的敬奉,是很难做到的。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说,发乎情,止于礼,这庶几可以近之吧。
一直以来,我们把希望的眼神放在了知识分子的身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也沉浸在知识分子制造的幻象内。可有一天,当我们厌倦了知识分子的浮躁与喧嚣,看惯了他们自以为是的傲慢与霸道,无法忍受他们毫无作为的犬儒行为时,我们确实应该适时地选择放手。知识分子自身的堕落,大众化时代的来临,注定了这是迟早的结果。知识界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努力,各种自救措施扑面而来。公共知识分子,介入的旁观者,等等,不一而足。但与其沉溺于往日的繁华,流连于记忆中搜寻涅槃的幻影,为何不向前看,寻找新的立足点呢?与其在纠缠于过去时顾此失彼,为何不反求诸己呢?其实,知识本身是自足的,无假外求。
(殷海光、林毓生著:《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