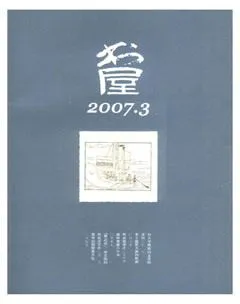浦江清日记中的吴宓先生
浦江清(1904~1957),江苏松江人。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遗著出版有《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录》等。浦江清1926年秋到北京,初进清华,经吴宓引荐,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为陈寅恪教授当助教。两年时间内读了不少书,受益良多。1928年夏,研究院国学门取消,并入中国文学系,浦江清担任大一国文教员。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浦江清日记》分为“清华园日记(上)”“西行日记”和“清华园日记(下)”三部分,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49年,中间有多年缺失或未记。若欲一睹吴宓先生的言行风神,则主要可于清华园日记(上)中搜寻,即1928年~1933年和1936年这两段。从浦江清记录与吴宓先生相过从的内容来看,载吴宓先生之事主要有两大部分,颇具史料价值。
其一为浦江清协助吴宓先生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1926年底,《学衡》停办后,吴宓认为文学事业不能中断,于是想到老友兼老乡的张季鸾,张时任《大公报》主笔。吴宓给张季鸾寄去《文学副刊》编辑计划书,毛遂自荐,要主持副刊,并声明不领薪金。张季鸾同意让其改良《大公报》。吴宓遂邀请赵万里、张荫麟、浦江清等加盟。1928年1月17日,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吴雨僧先生(宓)招饮小桥食社,自今年起天津《大公报》增几种副刊,其中《文学》副刊,报馆中人聘吴先生总撰,吴先生复请赵斐云君(万里)、张荫麟君、王以中君(庸)及余四人为助。每星期一出一张,故亦定每星期二聚餐一次。盖五人除赵、王与余三人在研究院外,余各有事牵,不相谋面,非借聚餐以聚谈不可也。”
吴宓胆小、怕得罪人的性格在编辑《文学副刊》时也体现了出来,浦江清日记中多有反映。这主要是因为张荫麟的一些批评性文稿而起。浦江清记录了类似的三次事例。一是张荫麟评清华研究院所出《国学论丛》。“吴雨僧先生谓其骂得太过火,嘱余于其文后续一段,将《国学论丛》较好数篇略推誉之。因将二期《国学论丛》细看过。与张君文后删去一段,续上一大段。原文骂得极痛快,气势极盛,我的‘续貂’文笔乃大不类。弄得筋疲力尽,终究有晴雯‘补虽补了,终究不像’之慨。”从这段1928年3月7日的日记来看,浦江清年轻气盛,是赞同张文的,无奈师命难违才改之,心里却不痛快,即便如此,此文亦未刊出,次日日记中写道:“吴先生终究怕研究院先生和他‘捣蛋’,张君之文决定不登了,因此我又得闲。”二是张荫麟与朱逖先的辩论文字,吴先生“颇不以为然”。1928年暑假,吴宓与浦江清俱往南方,张荫麟一人维持《文学》副刊,积极与朱逖先辩论。张荫麟驳朱逖先在《清华学报》上所发表之《古代铁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之无据。两人遂打笔仗。浦江清返校后,8月28日从吴宓仆人处索最近几期《文学》副刊,归读后在当日日记中表露了对张的同情:“大体真理属张,特朱地位高,负盛名于国学界,一朝被批,岂有不强辩之理。长此辩论,恐无已时,然而《文学副刊》则不愁乏稿也。”他同时还为自己及同事进行了辩护。而吴宓又持何种态度呢?在9月20日的日记中,浦江清记得很清楚:“张荫麟君在《文学副刊》上为文与朱希祖(字逖先)辩论,吴甚怕得罪人,颇不以此为然。张声明再不做批评文字矣。”可见张荫麟此举是负气而为的。三是张荫麟作两千字的《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张表面上虽声明不写批评文字,但其性格使然,终不能停。1929年2月间,趁吴宓再度南游,他撰此文,“嘲讽《真善美》杂志‘女作家专号’者,对于冰心嘲讽尤甚”。在2月19日日记中,浦江清认为:“文并不佳,但此种文字较有生气,适宜于副刊。”但同时他又说:“倘吴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因为个性和阅历的差异,吴宓和张荫麟、浦江清等在编辑思路、文稿选题上是有矛盾的,因为文稿署真名问题,浦江清和吴宓还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1928年9月20日的日记中有详尽记录:“与吴先生争《文学副刊》署名不署名的问题。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由此可见,浦江清心中怨气极大,一是由于工作量太大,日记中多有记载:“1929年1月3日:吴雨僧先生及张荫麟君来谈。谈及《大公报》(天津发行)《文学副刊》前途事。此数期稿件甚缺乏,缘《大公报》纸张加宽,每期需九千字,而负责撰稿者仅四人。以后每人每月须担任七千余字方可对付。”1929年2月8日:“雨僧先生来谈,云明日将进城,即南下。荫麟适亦来,遂剧谈。荫麟以大考,又忙于作文,病吐血。余劝其休息数日。《文副稿》,此一、二期,当由余一人承当矣。”此后日记中还有“余甚焦急”、“甚以为苦”的字样,可见当时浦江清是把此事当作一件苦差来应付了。王季思先生追忆时谈到,当时为了编好《大公报·文学副刊》,(浦江清)每星期要写千几百字的评论文章,当时(浦)认为是吴雨僧先生派给他的苦差事,后来与我谈起,才说这是对他写理论文章的最好锻炼。二是付稿费与不署名问题,文人著书立说,向来耻谈金钱,只重虚名。但吴宓的编辑思路恰恰相反。起初《大公报》每月给吴宓二百大洋,稿费、书费和邮费都在内,完全由吴宓支配,吴即允给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每人四十大洋,后来因有所变故,张季鸾将二百大洋改为一百五十大洋,吴宓因此还曾与之辩论过。浦江清日记中记载稿费只有一句,见1929年2月日:“吴雨僧先生送来《文副》稿费二十元。”从浦江清需求来看,因年轻资历浅,要以博取名誉为重,吴宓“不署名”的不成文规矩自然令其大为不满,使其对成就的满足感受挫,积极性不太高涨,1932年2月9日的记载可谓真实心态的写照:“吴先生嘱撰《大公报》副刊文字数篇,允诺未动笔,甚以为苦,今日得暇颇是一了文债,而精神疲惫之至。”实事求是的说,这种“不署名”的制度为浦江清造成很大遗憾,也为其后人整理文稿增加了难度,只得从日记提供的线索中搜寻。浦汉明写道:“父亲早年的作品,发表时多用笔名,长时间来以为已不可考。所幸日记中有几处撰写文章的记载,据之于报刊对照,在确认笔名后,顺藤摸瓜,范围逐渐扩大,竟发现佚文四十二篇。《浦江清文史杂文集》(1993年清华版)便是选用其中二十九篇与另一些以前未曾结集的论文编辑而成的。仅就此而言,日记也是弥足珍贵的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浦江清日记的史料价值。
从浦江清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要内容有专论、中外新书评价、学术文化信息、中外古今文化名人诞辰或逝世若干周年纪念等,还刊发不少忧时感事的诗词作品。散见记录有:“浦江清为董作宾所编《新获卜辞写本及后记》写《殷墟甲骨之新发现》一文,充副刊之材料。”(1929年2月9日)“佩弦交来副刊稿件,为评老舍君之《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小说之文。文平平,无甚特见。《赵子曰》我曾读过,并在副刊上论《小说月报》十八卷时曾评及之。老舍君笔头甚酣畅,然少裁减,又多夸诞失实,非上等作家也。”(1929年2月5日)“发副刊稿至天津。稿共两篇,一即佩弦稿,一荫麟纪念梁任公之文。张文甚佳,颇能概括梁先生晚年思想上及学术上之贡献。”(1929年2月6日)。奇怪的是,日记中对吴宓文章几乎只字不提,吴宓自1928年1月2日起至1934年1月1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撰文甚多,重要者有:《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年纪念》、《论诗之创作》、《诗韵问题之我见》、《吴芳吉传》、《浪漫的与古典的》、《茅盾长篇小说〈子夜〉》等。在1930年8月至1931年9月,吴游学欧洲期间,委托浦江清代编,而浦江清1930年日记只有12月的五天,12月3日有“早上,发《文学副刊》第百一一期稿,因明日元旦邮局不办公,所以早发一日”的简略记载。1931年日记又只有1月份1~28天,1月15日记:“上下午都忙于发《文学副刊》稿,此期材料尚佳。主要文字为胡宛春的《评声越诗词录》,另外一篇评论瞿兑之的《方志考稿》的。晚上选抄胡宛春的词数首,预备为《文副》补白。”1月22日有“作短文数篇,《文学副刊》稿,今日竟来不及发”之语。浦江清记录颇多草草,或不记,盖因其正热恋燕京大学的女生蔡贞芳,多次到燕大的姊妹楼去看她,为她送参考书,陪她参加游艺晚会,晚上在昆明湖练习溜冰以取悦蔡贞芳,无暇述及。1930年9月12日,吴宓踏上欧洲征程时,浦江清的送别诗说:“人生难得是休息,万里俊游亦壮哉。”吴宓回赠道:“浦生学通博,大事久托付。”其中的大事即指委托浦代为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浦江清虽然未曾详说,但从寥寥数语中,亦可知他在追求爱情的状况下,还是如期完成了任务,不辱师命。其记述对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者不无帮助。
其二为浦江清耳闻目睹吴宓先生情事变迁及自己与周围人的态度。在浦江清协助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这段时间内,吴宓正在热烈追求毛彦文,而与发妻陈心一闹离婚。浦江清在对待老师情事上的态度主要有两方面,即起初不同意离婚,在吴宓与陈心一离婚已成事实后,又帮其试探燕大女生陈仰贤之态度。
1928年7至8月,吴宓暑假南游,与毛彦文相谈甚欢,爱潮高涨,已准备与陈心一离婚。此行作《南游杂诗》九十六首。浦江清在1928年8月30日日记中记道:“吴雨僧先生到校招余去谈,因观其《南游杂诗》百首,佳者甚少。吴先生天才不在诗,而努力不懈,可怪也。”对于惯以诗人自称的吴宓来说,浦江清可谓发人之未发,但浦江清或许没有猜到,这纯粹是吴宓心情好的缘故,所谓“诗言志”也,多应时之作,质量并不一定上乘。浦江清规劝吴宓说:“在中国,离婚是不明智的,如果实在斩不断情丝,则可以和毛彦文一起去美国,在那儿哪怕公然同居也没人管。”(见北塔著《情痴诗僧吴宓传》)吴宓口头上虽表示不能那样做,但心里也承认那至少是有效的权宜之计。对于人们的说法,吴宓曾自比哈姆雷特,要浦江清做霍拉旭,希望自己死后,浦江清能为他辩诬洗冤。
浦江清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周围一些人对吴毛之恋的看法。1930年12月26日,浦江清二十七岁生日,邀叶公超、朱自清、蔡贞芳、陈仰贤等在清华园前工字房吃饭,吃完饭后在西客厅闲聊,“仰贤批评吴先生的离婚,表同情于吴师母,并且说吴先生的最小的一个女孩在家里,一听外面门铃响,便说爸来了,最使她的母亲伤心。仰贤批评说,吴先生是最好的教授,但是没有资格做父亲,亦没有资格做丈夫。这使我们都寒心,因为在座诸人都知道,吴在英国,用电报快信与在美国的毛彦文女士来往交涉,他们的感情已决裂了,吴现在唯一希望在得到仰贤的爱,而仰贤的态度如此,恐怕将来要闹成悲剧。”浦江清的担心不无道理,为此他还去信试探。1931年1月7日,“近六点钟,仰贤来了。她一来便有话讲。吴先生寄给她一本书,托她去交给我,再转交给吴先生的表弟。我们讨论了吴先生与毛彦文的问题”。具体讨论了什么,没有说。1月18日“吴先生有信来”。1月19日晚,浦江清“又写一封信给仰贤,把吴先生的来信中关于毛彦文的事,摘抄几句,当然把关于她的去掉。先说明我的意见,觉的我们虽不认识,但照她(当指毛彦文)态度看来,似乎不值得吴先生的崇拜。我个人希望吴先生能超脱,问她‘有什么意见没有’?这封信是特地去探他对于吴先生的感情的”。1月24日,浦江清去燕京大学,“仰贤交给我吴先生寄给我们两人信一封,内中言及与毛女士的交涉失败,毛决不赴欧,吴亦决不赴美,故告决裂”。1月26日,“仰贤有电话叫我去,说吴先生有信来要交给我。下午到燕京,见仰贤。关于吴先生的事,并未多讨论”。浦江清却从陈仰贤处知道了蔡贞芳家已替蔡找了一个人,“我听后,默然者半分钟”。但浦江清并未埋怨贞芳,还希望与她保持永久的友谊,并认为脑海里长留下她的影子便是幸福。这态度是和吴宓一样善良的,但似乎比吴宓更理智些。这种变故令浦江清十分懊丧和痛苦,他在1月26日的日记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有重大的事情可记”。而吴宓与陈仰贤也未能结缘。陈仰贤当时热恋叶公超,叶却只给她冷面孔,比毛彦文还绝情,所以她和吴宓只是同病相怜罢了,吴宓在欧洲时,出于对毛彦文的愤怒和绝望,曾经在给陈仰贤与浦江清的信中,表达过对陈的情意,无奈陈仰贤在对叶公超绝望后,就匆匆嫁人了,致使吴宓的暧昧感情落空。
在事业与感情方面,浦江清的确受吴宓影响颇深。如1929年1月22日,“吴雨僧先生曾言,择妻并须择丈人”;1932年2月13日,“上午在吴先生处见厦大英文系主任罗文柏君。座间发一议论,颇有味……男女恋爱,成于多接触,无形中彼此妥协也。但最高之恋爱,则不待妥协而成于一见倾心,此方为纯粹的、理想的、崇高的”等等。浦江清游欧返国后,1936年4月26日与松江张企罗结婚,此前,吴宓获悉浦江清与张企罗通信后,还于1月30日晚“为企罗题英文名”,足见关怀之情。1942年11月21日,浦江清历尽磨难,自上海千里迢迢至昆明赴西南联大任教。次日,吴宓即邀其出去吃饭,为浦江清接风洗尘。浦后又与吴宓、汤用彤、贺麟等同居一所小洋房,村野风景甚美,师友常同游谈。等到1946年10月22日浦江清复返清华园时,吴宓在各地游学后,于解放初落脚西南,藤影荷声之馆里再也不见雨僧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