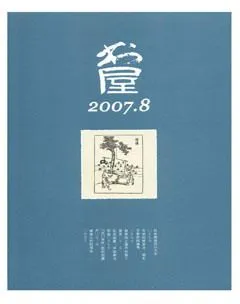“水门事件”的历史遗产
(一)
“水门事件”是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其影响极为深远。
“水门案”曝光之初,与此有牵连的总统高级幕僚相继中箭落马,致使主要依靠白宫幕僚而非内阁各部运作的尼克松政府陷入极度混乱,内政外交处于半瘫痪状态,一些至关重要的国内政策构想和外交承诺化为泡影。
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最昂贵的国家。尼克松出身贫寒,早年曾遭逢兄弟连续病故的创痛,深知平民百姓缺医少药之苦。他原打算在第二任总统任内,正式向国会提出议案,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当时,掌管联邦政府“钱袋权”、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地位,由共和党总统出面提出“福利化”法案,极有可能得到顺利通过。但是,因“水门事件”影响,这一计划胎死腹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旧案重提”,试图建立免费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结果遭到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无情封杀。时至今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仍然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公民生活在没有医疗保险的阴影之中。
在中美关系领域,基辛格曾多次向中国领导人秘密许诺,将于尼克松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前两年(1973-1974),遵循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原则与中国正式建交。但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干扰,美方的承诺沦为空头支票。当年中国领导人对“水门案”引发的政局动荡和危机缺乏深刻认识,认为美国言而无信,故意玩弄“中国牌”,挟中国压苏联在军备控制和全球战略要点争夺中让步。根据美方已解密的中美会谈档案,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拍着自己的肩膀,毫不留情地挖苦基辛格:“我们看到,美国踩着中国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了,现在这些肩膀已经没用了。”
“水门案”之前,尼克松总揽外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有实权而无名分,国务卿罗杰斯有名分而无实权,白宫幕僚与国务院行政主管明争暗斗,相互制衡,总统坐收渔人之利。这套微妙的“制衡”手腕,与中国帝王玩弄的“御臣术”如出一辙。可是,“水门案”闹大之后,尼克松焦头烂额,难以自保,在外交上不得不日益倚重基辛格。假如没有“水门事件”,在“权术总统”尼克松手下,“谋略大师”基辛格后来根本不可能当上国务卿。
美国学者格林斯登认为,“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总统面临的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包括权力意识觉醒的国会,软弱无力的政党系统,攻击性极强、积极挖掘坏消息的媒体,以及难以指挥的行政官僚系统。尽管总统仍然在宪政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和地位遭到极大削弱。
197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的战争权。1974年,国会通过了《预算和拦截控制法》,限制总统重组行政部门和拦截国会拨款的权力。1978年,国会通过了《政府部门道德准则法》,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授权独立检察官在不受总统控制的前提下,对政府行政部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此项立法为1986年“伊朗门”案和1998年“拉链门”案埋下了伏笔。
在国际舞台上,受“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影响,中美建交日程被迫推迟,台湾当局赢得了喘息和缓冲时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身心交瘁,放手交权。蒋经国临危受命,独撑全局,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不惜重金,对美国国会进行大规模院外游说,效益显著,成果惊人。1979年,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后,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限制行政部门与台湾当局调整关系的幅度,约束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节外生枝,使台湾当局有恃无恐。
因担心中国退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卡特总统曾一度考虑否决《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国会通过的立法,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总统不同意国会立法,可以予以否决。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否决权是总统拥有的最重要的宪法权力之一,是总统制衡国会、影响立法的尚方宝剑。国会若要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众两院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可是,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的票数比例极为悬殊(众议院339∶50,参议院85∶4),卡特总统的否决明显无济于事,最后他勉强同意签署《与台湾关系法》。
事后,卡特总统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将从宽解释此项法律,一定按照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原则和精神处理双边关系。中方埋怨美方出尔反尔,节外生枝,以国内立法的方式,蛮横地干扰和破坏中美建交文件《上海公报》。但是,由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以及美国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够认识和深刻了解,中方的埋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牛弹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外交只认总统,忽视国会,其教训极为深刻。
北越同样是“水门事件”的主要受益者之一。1975年,在苏联坦克大炮支持下,北越利用“水门后遗症”的千载难逢之机,向南越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反战情绪笼罩下,美国国会严格控制军援拨款,福特总统优柔寡断,未能及时履行巴黎停战协定中援助南越政权的秘密承诺,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以惨败彻底收场。福特和基辛格后来都把惨败的结局归咎于“水门事件”和美国国会。北越大军兵临西贡城下之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紧急议案,授权福特总统可以在撤退美国驻越人员时动用美军。当国会参议院吵吵闹闹、议而不决之时,南越阮文绍政权土崩瓦解,烟消灰飞。
想当年,在结束越战问题上,尼克松扮演了一个难度极大的角色。他既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又要通过艰难的外交谈判促成停战和撤军,同时还要应付国内的暴乱示威,新闻媒体的抨击,政府内部的严重泄密,还有坚决维护新闻自由的最高法院。一场由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肇始并最终弄得无法收场的战争,却使收拾烂摊子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陷入了孤家寡人、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处境。
尼克松认为,越战是卡在美国喉咙上的一块骨刺,对内政外交和全球战略影响极大。美国既要收缩战线,尽早从越南脱身,又不能轻举妄动,操之过急。一方面,美国应实行战争“越南化”计划,建立一支能够替代美军作战的南越军队。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美国在冷战对抗中的领导地位,避免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一垮皆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确保西方世界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决不能过分仓促地单方面停战和撤军。
为此,尼克松制定了“先打再谈,体面撤军”的战略,独断专行,铤而走险,未经国会宣战,悍然下令美军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彻底扫荡北越的后勤基地,甚至冒着可能与中、苏两国摊牌的风险,不但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而且还在北越领海布雷,企图釜底抽薪,彻底切断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致美国学者惊呼,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美国已出现了“帝王总统”。与此同时,尼克松手下为打击泄密和“堵漏”而组建的“管子工”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在“水门窃听案”中惹出了弥天大祸,最终导致尼克松丢失了白宫宝座。
(二)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写道:“在南北战争以来最为破碎分歧的国内环境中,尼克松挑起了结束越战这个锥心痛苦的重担。即使事隔二十多年,每一思及举国上下对越南战争的共识突然间冰消瓦解,仍然令人痛心震撼。”“面对各地暴乱示威,国会决议案渐渐地倾向于单方面撤军,再加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刻,尼克松本应在任期内,尽早向国会陈述其战略构想,要求国会毫不含糊地支持总统的外交战略。如果得不到国会的支持,他应当要求国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清理越南战争,使国会也承担起结束越战责任。”但是,“尼克松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放弃政府行政部门应有的领导职责之举,历史不会原谅他如此行事可能导致的骇人后果”。
基辛格认为:“尼克松的决定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是高度合乎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的正确决定。他一人承担了如此沉重的责任,在美国制衡与分权的制度中,这个千钧重担本来不应由尼克松一人独自承担。”
那么,尼克松为何特立独行,非要独自承担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重担呢?主要原因为,尼克松先后干过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等要职,精明老辣,独具匠心,深谋远虑,勇于担当,深谙美国政治内幕。显而易见,在战争决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战略问题上,如果通过宪政民主程序,让议程公开、极易泄密、议而不决、多谋无断的国会两院来主导战争决策,很可能导致一场外交和全球军事战略灾难。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在越战中一败涂地,尼克松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而且还招来了无数指责谩骂之声。
但是,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独树一帜,语惊四座,他在回忆录中认为:“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但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赢得了缓冲时间。1965年,就在美军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叛乱活动的内部威胁。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到了1975年,东盟各国都已经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越战,东南亚国家对抗共产党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东盟繁荣兴旺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越战期间孕育成形。”实际上,不仅新加坡和东盟各国,而且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内的整个“东亚资本主义”,从政局稳定、经济腾飞到民主改革和逐渐走上宪政法治之路,都与美国介入越战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军退出印支半岛、越南实现统一之后,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迅速恶化。苏联不费吹灰之力,在越南金兰湾获得了美军经营多年的现代化大型海、空军基地,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包围。1979fHzTOUJUK0Q1tucE74EPkA==年,中国毅然打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策应和援助柬埔寨战场的抗越战争,同时与美国携手合作,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越战结束短短数年,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环境、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回首往事,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堪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伤和国耻,深深地镌刻在美国人的心灵之中。从某种程度而言,因新闻自由和反战示威,美军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前打输了越战;因权力制衡和司法审查,尼克松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丢失了总统宝座。由此,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既可视为美国的创伤和国耻,亦可视为美国的自豪和骄傲!它既暴露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弱点,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宪政法治的强大和力量。这种令人惊异的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功能,正是美国兴盛强大的基本原因之一。
可是,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幸灾乐祸,把美国各界的痛苦反省和批评自责视为意志薄弱和畏惧退缩,把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新闻监督视为制度失败和自毁国脉,把美国在越战后的战略收缩视为军心涣散和战略崩溃,误以为时代潮流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误以为美国的衰落和全面溃败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据此,苏联咄咄逼人,积极进攻,从柬埔寨、也门、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到直接出兵入侵中亚要地阿富汗,四面出击,过度扩张,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强大的军事机器外强中干,是建筑在僵化脆弱的经济基础和极权的政治体制之上的。
里根总统执政后,当美国凭借高科技和体制优势,整军经武,强硬对抗,在西欧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宣布实行“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当美国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凭借先进的信息手段在苏联东欧地区自由传播之时,苏联应对失策,节节败退,自乱阵脚,土崩瓦解。一个高度集权、横跨欧亚、军力强大的巨大帝国,竟然未经一战便分崩离析,在数千年人类历史中,这种现象空前罕见!
在美国国内,“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媒体和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看法,带“门”(gate)字的英文词尾,从此成为政治丑闻的代名词。里根政府非法向伊朗秘密出售军火案被称为“伊朗门”(Irangate);克林顿政府解雇负责旅行事务的白宫雇员事件被称为“旅行门”(Travelgate);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被称为“拉链门”(Zippergate)。此外,为了限制白宫幕僚权力,福特和卡特总统曾一度取消了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白宫所属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任命改由经参议院批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亦不复拥有基辛格当年炙手可热的超级权势。
尼克松辞职下台后,毛泽东一直牵挂和惦记着这位老朋友,并多次在外交场合为其“打抱不平”。毛泽东曾对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1975年7月1日,毛泽东对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抱怨道:“‘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
1976年2月,新华社发布公告,宣布中国政府将正式邀请尼克松夫妇访华。公告宣布后,举世皆惊。国际观察家们猜测,只有向美国记者斯诺自称“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毛泽东才会如此特立独行,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更令世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以刚从美国进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波音707大型客机为专机,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为全权特使,不远万里,专程赴美,恭迎因“不光彩原因”下台的尼克松总统来华进行私人访问。礼遇之隆,情谊之重,出招之奇,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政府往往顾念旧谊,重义轻利,雪中送炭。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往往刻薄寡恩,精明冷酷,见死不救。前南越总统阮文绍曾哀叹:“做美国人的敌人易,做美国人的朋友难。”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伊朗国王巴列维等皆饱尝“见死不救”的滋味。其实,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相当为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国会、媒体、政党、民意、利益集团等全都是大爷,一个也惹不起,请客花钱和对外军援等事宜,必须看国会和纳税人的脸色行事,行政部门根本就做不了主。
尼克松抵达北京时,毛泽东不但重病缠身,而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但他仍然坚持与老朋友见面。两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战略问题交换了看法。尼克松在其名著《领袖们》一书中写道:“1976年,当我再次访华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都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却说不出来。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下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过。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
尼克松深谙人情世故,很可能是顾及礼貌,也可能是碍于情面,他故意没有把问题挑明。实际上,无论别人怎样看待,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缺乏程序性交替和制约制衡的高度集权体制中,毛泽东晚年在文革动乱的凄风苦雨中“战斗到最后一息”,对国家利益以及他本人领袖形象、历史地位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恐怕高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羞辱地辞职下台。
“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在政治和精神上遭到极大打击,但他并未颓废消沉。面对惨败和羞辱,尼克松坚韧地表示:“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人生的征途中既无胜利,也无失败。”下台之后,尼克松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潜心思考,总结经验,先后出版了《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领导人》、《真正的和平》、《不再有越战》、《1999——不战而胜》、《角斗场》、《只争朝夕》、《超越和平》等著作,几乎每一本都成为国际畅销书。
在外交领域,尼克松逐渐以外交战略权威的形象重新崛起,经常应邀为里根、老布什(George Bush)和克林顿总统出谋划策,指点迷津,提供富有创见的外交咨询和建议。1989年“六四风波”后不久,他肩负修复中美关系的重大使命,第五次访问中国大陆。1994年,临终前不到一个月,他抱病出访莫斯科,为美国调整对俄罗斯外交提供政策评估。尼克松“身败名裂”之后,仍然对美国外交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评。
1994年4月21日,尼克松因中风在纽约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当日,记者向当时已经深陷“白水案”风暴的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提问:“想想你目前经历的司法调查,你对当年尼克松可能经受的痛苦历程,是否有更深体会?”希拉里答非所问:“我觉得,我们现在应当为尼克松总统祈祷。”言罢,出乎记者们意料,大庭广众之下,作为当年参与弹劾尼克松的著名律师,希拉里突然情绪失控,热泪盈眶,话音哽咽,她伤感地向记者解释道:“你们知道,一年之前的四月,我的父亲也是在八十一岁过世,所以,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尼克松总统的女儿们。”
尼克松逝世后,现任总统克林顿和卸任总统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以及朝野政要、文武百官倾巢而出,出席了场面极为隆重的葬礼,并纷纷发表热情洋溢、有褒无贬的悼词。尼克松被赞誉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举世无双的战略家”、“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外交政策总统”。至于“水门事件”,仿佛重新变成一桩不起眼儿的“屁事”。
尼克松身后“平反昭雪”,哀荣甚隆,引起自由派阵营极度不满。1995年,好莱坞著名导演兼制片人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不惜重金,聘请前白宫高级幕僚为顾问,大量参考法律学者和“水门事件”专家的著述,编剧并执导了一部耗资四千三百万美元、长达三小时二十分钟的传记性巨片《尼克松》(Nixon),试图“重写历史”。斯通本人曾是尼克松的拥戴者,但是,亲历入侵柬埔寨之战并身负重伤后,他一转成为痛恨尼克松的激进自由派。尼克松“先打再谈、体面撤军”的战略,导致越、柬两国生灵涂炭,焦土遍野;美军部队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难以释怀。
在影片中,英国影星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尼克松一角,此公因在影片《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