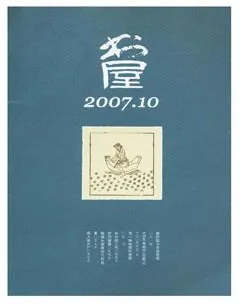因缘新旧意谁知
一
与许多人一样,因为吴宓而知道毛彦文,所以看到她的自传《往事》,首先想读的便是其中有关吴宓的回忆。让人失望的是,书中的正文部分根本没有提及,只是作为第三章的附录,收了一篇简短的《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那是因为萧公权在《传记文学》上刊文涉及此事,毛彦文认为“并非实情”而做的解释。
与《吴宓日记》里的相关内容对照,毛彦文的陈述角度不同,事实却没有多大出入。惟最后的一节文字,读来令人唏嘘:“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几分浪漫气息,……十余年前海伦(毛彦文英文名)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时,曾看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翻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登载许多大陆有名学者的坦白书。内有吴的一篇,大意说:他教莎士比亚戏剧,一向用纯文学的观点教,现在知道是错了,应该用□□□观点教才正确。当时海伦气得为之发指!人间何时,文人竟被侮辱以致如此!吴君的痛苦,可想而知。传闻吴君已于数年前逝世,一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此文写于1970年,吴宓是八年后才离开人世的。由于当时境遇所限,他没有渠道读到这篇文章,否则又会在日记里写下怎样的感慨!
吴宓曾将毛彦文的感情生活分为三段:一与朱君毅,二与吴宓,三与熊希龄。然而,在《往事》结语中,毛彦文温习一生的遭遇,表示只受到两种潜力的推动:一是与朱君毅的恋爱,一是与熊希龄的结合。两次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又都留下刻骨铭心的悲痛。她晚年曾对一位来访者说,吴宓是“单方面的”,与她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吴宓有时也能认识到这一点。他在1946年的日记中写道:“宓自思一生爱彦,而彦之感情中,竟不予宓任何地位!”
二
毛彦文生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作为最早留学海外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归国后从教参政,主持香山慈幼院,出任国民大会代表,都是值得在现代妇女史上记下一笔的。但历来人们关注的,仍然是她的婚恋故事。早在她入学杭州女子师范之初,当地一家报纸便刊登过一篇《毛女逃婚记》,写她抗拒包办婚姻、与表哥朱君毅自由恋爱之事。朱君毅当时就读于清华学堂,与吴宓同学。《吴宓日记》中也有在朱君毅处见到该文剪报的记录。
毛彦文比朱君毅小四岁,从这位在北京读书的表哥那里,接触了新思想,同时也萌生了爱意。幼小时,家里就给她订过婚。当男方得知其外出求学,便前来催婚,这就有了那桩轰动乡里的逃婚事件。由于父母的迁就,结果却意外的圆满,对方同意退婚,两位表兄妹随即订了婚。之后,朱君毅去美国留学,两人书信来往长达六年。朱君毅是与吴宓一同去美国的,两人关系甚密,毛彦文的来信,都让吴宓看过。其间,有人给Yk304+AvIhGboTJ0rttvDw==吴宓介绍对象(即陈心一),因其也在杭州女子师范上过学,吴宓让朱君毅委托毛彦文代为相亲。毛彦文果真亲往调查,并写信详细汇报。她的结论是,如果吴先生要娶一位贤主妇,合适;如果欲求能对话、善交际者,不适。她建议吴宓先行通信,亲眼看过,再做决定。信中言道:“先为知己,后为伉俪,实至良之策。”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吴宓还是当即许诺了婚事。
朱君毅和吴宓先后回国,又一同受聘于东南大学。在他的要求下,毛彦文也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转学至金陵女子大学。课余期间,大家时常聚会宴游,甚为亲密。不想,有一天,朱君毅突然以性格不合为由,书面提出退婚。同事好友耐心规劝无效,双方家长也赶来调停。最终,由时任东南大学教务长的陶行知出面,才达成表面上的和解。朱君毅当众向毛彦文道歉,将退婚信烧掉。为此,吴宓还与人合伙作东,请到场的各位在东南大学农场餐厅午宴,庆贺两人重归于好。《往事》中也提到这次宴会,只是毛彦文误记为吴宓一人出的钱。
朱君毅与毛彦文虽当众达成谅解,事后却是形同陌路。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正式举行了解除婚约的仪式。这回是毛彦文主动提出来的,由正在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的该会副会长朱其慧(TVp2GV7WEb38RUPxRiTfaA==即熊希龄夫人)主持,邀请了不少教育界的名流,并律师、记者、照相师、记录员,仪式十分隆重。双方协议草拟解除婚约的条文,当事人和证人都签名盖章,还成立了一个“善后委员会”监督执行。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熊朱其慧夫人兼任委员会主席,吴宓教授兼任委员会秘书。”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两位负责“善后”的人,真的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毛彦文后来的生活。
三
《往事》中详细记录了与朱君毅的情变,两人分手具体有哪些协议则未加言明。据吴宓所记,有一项是朱君毅赔偿毛彦文的“损失费”,按月分期支付,由吴宓转交,直至全数付清。吴宓正是在此过程中,与毛彦文频繁接触,而渐生感情。
吴宓后来去清华任教,毛彦文则到了杭州,在浙江省政府供职,两人一直保持联系。1928年8月,吴宓南下,与毛彦文有几次深谈,并向她讨要了她与朱君毅的来往信件,拟作小说之用。这计划中的小说,就是他屡屡提及的、自以为可以传世的《新旧因缘》。毛彦文取出旧函,一一重读,百感交集。时值朱君毅新婚期间,毛彦文当即草拟一封电报稿,写道:“苏州天赐庄八号成宅朱君毅鉴。须水永清,郎山安在?”所谓须水、郎山,是其老家的地名,当年表兄妹定情之际,朱君毅有誓言:“须水郎山,亘古不变。”毛彦文想起往事,泪落手颤,不能成书。吴宓为之续写:“……敬祝幸福。彦文。”然后让人拿去邮局发出。《往事》中叙及这封电报,可没有说明吴宓当时在场。
吴宓回到北京,向妻子坦言他对毛彦文的感情,并且又将此事写信告知毛彦文。吴宓的婚姻出现危机,各种传闻也随之四起。毛彦文却极其冷静、理智,她写信给一位友人,转达自己的意见。信中申明道:“1.请彼万勿再以彦为其小说中人物之一,令彦无辜受累。2.彦决不与之通信,请彼亦勿再来函。3.关于彼家庭间琐事,幸勿再向彦报告。彦当视为有意侮辱,盖彦固绝不以其离婚为正当也。4.彦有力出洋则出去,无力出洋则仍在国内糊口。绝对不受彼之补助,即寄来亦必退还。5.彦系一独身女子,断不容任人误会。以前雨生先生因凭空臆造,至陷彦于嫌疑之中,被人诽谤一节,应请雨生先生及心一姊负责更正。否则无端毁坏他人名誉,法律有保护之道。6.心一姊与彦系同学又同乡,倘她因雨生先生之单面瞎想,信以为真,陷入误会,此不特彦之不幸,亦吾浙人女界之辱也。7.彦处世接物,自有主张,决不如雨生先生之推想,请彼勿再关怀。8.雨生先生之旧友,大半为朱君毅先生之旧友,亦即彦间接之朋友;若令各方误会,彦以孤独之身,何以处之?总之,彦对雨生先生,仅视为一平常较熟之朋友而已。”这几条说得有理有节,滴水不漏,可以想见她日后出任国大代表提案发言时的神采。
凭吴宓的性格,自然不会就此却步。他不顾众人的反对,断然与妻子离婚,继续追求毛彦文。毛彦文去美国留学后,两人又有通信往来。1930至1931年间,吴宓游学欧洲,邀请毛彦文前往。毛彦文正学成待返,便绕道欧洲。两人见面,却因意见不一,时常发生争吵。本来出现的转机,重又陷入僵局。归国后,两人南北异地,隔阂未见弥补,且日渐加深,终于没能走到一起。
四
应该说,毛彦文对吴宓的追求,一度有过犹豫,然而两人性格差异太大,权衡之后,还是果断地终止了哪怕是“平常较熟之朋友”的关系。她嫁给熊希龄,也是在一种被动的情势下,但综合各种因素,她最终答应了这桩婚事。熊希龄在婚礼上报告恋爱经过时说:“自朱夫人于四年前逝世后,深感内助无人。毛女士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爱儿童,可协助办香山慈幼院。毛女士以理想、职业相同乃允婚。”这一解释虽然显得冠冕堂皇,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熊希龄曾任国务总理,虽然已经离职,没有实权了,但势力仍然不小。婚礼来宾签名簿上,不仅可以看到沪上许多政府高官、商界巨头、学者名流,还有梅兰芳、杜月笙、张啸林的名字,方方面面的人物都很捧场。熊希龄当然很有钱,否则他如何能创办香山慈幼院,成为中国最早的慈善家之一。毛彦文决定嫁给熊希龄,利益上有自己的考虑,这本来无可厚非。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并不在此,而是集中在两人年龄的差距上。婚礼上有贺联:“老夫六六新妇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还有一联打趣道:“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至于小报上刊登的就有些不雅了,如:“熊希龄‘雄’心不老,毛彦文‘茅’塞顿开。”这样的老少恋,任何时候都是媒体热衷的话题。当时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断断续续,竟达数月。纵观毛彦文的一生,先是为反对父母包办而逃婚,后又与自由恋爱的对象协议解除婚约,再是这次老夫少妻的婚姻,每一回都可作为中国现代婚姻史的典型个案。
吴宓当时的感受,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惜那段时间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不过,他写的《吴宓先生之烦恼》、《空轩十二首》、《忏情诗三十八首》等组诗,都在第一时间公诸于世。他追求毛彦文未果之事,当即弄得沸沸扬扬。一次赴某军长宴时,主人介绍说:“此即与毛彦文……之诗人。”吴宓是失败者,心里自然很“烦恼”,但各种场合未见其恶言相加。对于别人有关熊、毛婚事的议论,他还不以为然。《忏情诗》有云:“花样翻新记艳闻,红颜白发语徒纷。有情私祝成良眷,安乐微酬半世勤。”
“吴宓苦爱毛彦文”一事,不仅被当作八卦消息四处传播,还有作家将之写成文学作品。陈慎言以之为素材,作小说《虚无夫人》,在《时报》上连载。吴宓阅后称“描写殊恶劣,而宓心情及彦之苦楚,实未写出”。关于李健吾的三幕讽刺剧《新学究》,吴宓认为“取材既太沾实,而叙事则又失真,皆与宓所行全然相反”。卢冀野撰《恼毛女峰曲》,周光午为之作笺注。曲中词句多取自《吴宓诗集》,而表达的是谴责毛彦文负心、后悔离婚之意。吴宓怒斥其“均与宓之情意正相反背”。各方的误会、曲解乃至诽谤,使吴宓伤心悲愤,痛不欲生。他深感受到侮辱,甚至比遭毛彦文的拒绝更加“烦恼”。
五
吴宓对毛彦文的感情,并没有因对方已名花有主而放弃。他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毛彦文的近况。熊、毛二人婚后,由上海回到北京西山的双清别墅,贺麟曾前去拜会,吴宓便让他详细讲述所见所闻。听了贺麟分析,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为完成宓对彦之真爱,应专诚独身,以俟熊公百年之后。”可转念一想,其时,“彦未必能幡然与宓为觉悟后之爱侣”,于是又“烦扰不安”。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吴宓随校迁至南岳。12月31日中午,贺麟给他看《大公报》电讯,上面载有熊希龄在香港病逝的消息。当天《吴宓日记》写道:“宓震惊,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第二天一大早,他拟定一份与贺麟联名的唁电:“香港电局探交熊希龄夫人礼鉴。惊悉秉老仙逝,无任悲悼。至祈节哀顺变,谨此唁慰。贺麟、吴宓。湖南南岳市临时大学。”随后又在日记中写道:“自觉我一生惟爱彦最为深至久长,熊公既殁,宓或可有机缘与彦重复旧好,终成眷属乎?”
吴宓有如此想法,便如此行动了。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毛彦文写信,希望重建联系。毛彦文自然不予回复。吴宓因事去香港,登门求见,不巧毛彦文已到上海去了。有一位叫毛仿梅的青年,自称其堂弟,与吴宓面谈,代为表示,今后拟继承熊公遗志,尽力于慈善教育事业,与一切朋友不欲往来,望吴宓勿再去函,更不可此时到沪过访。吴宓当面表态,绝不愿有一事而使熊夫人不快者;回去后,又忍不住不断写信寄到上海。毛彦文对此态度依旧,且一次比一次决绝。《吴宓日记》1940年3月20日有记:“接彦三月十日自沪复书。不着一字,仅剪取宓函中数语,粘贴信笺上,为复。略谓伊决为熊公守节终身,祈宓勿再接近云云。”5月22日又记:“拆视彦命其秘书挂号寄还宓至彦函,并未启视。原函外批云:熊夫人已于月前离沪,故退。熊宅附言。四月二十九日。”10月3日又有:“熊公馆航函:径启者,本宅于九月底退租,以后请勿来信。此致吴宓先生。”
毛彦文不仅拒看、退回吴宓的信函,后来还让沈从文、贺麟等人转达自己的意见。吴宓却一如既往,一意孤行。直到某一天,在报上看到毛彦文当选北平市参议员、国民大会代表的消息,他才终于明白,以前种种的推测以及心存的幻想都错了:“知彦方热心政治活动,对宓似毫无情意,不欲与宓接近,终当分道背驰以没世耳!”实际上,他也曾感觉到志趣不同,是两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怨情诗》有云:“两驿火车相对开,东行未必遇西来。情缘悟得原如此,百叩不鸣漫自哀。”
毛彦文则从始至终都很清醒。《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文中有言:“吴心目中有一不可捉摸的理想女子,不幸他离婚后将这理想错放在海伦身上。其实吴并不了解海伦,他们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纵令吴与海伦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说不定会再闹仳离。”
(毛彦文:《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