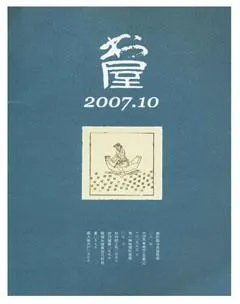补白的工作
最近《书屋》的编辑来信,恳请我将近期的研究成果写篇学术随笔介绍一下。接信后,我甚感踌躇,只怕这短小的篇幅难以周全。现在我尝试着去写,倒是想趁机回顾和总结一下近年来的研究心得。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美国汉学界做学问,一向都偏于专攻某个时代(例如专攻汉代文学、唐代文学、宋元文学、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等)或是某个特定的文体(如专攻古典诗词、元明清戏剧和小说、当代小说等)。当初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受的就是这种规范的汉学教育。但后来自己搞研究,越走越远,竟渐渐走出了旧有的设限。可以说,从1980年初以来,我的研究发展路线一直是曲折而多变的,有时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因为我喜欢从事文学“侦探”的工作,在研究中常有边走边发现的乐趣。这就像登山途中这山望着那山高,一个“新发现”会引来另一个新发现,峰回路转,又是柳暗花明的一个新村。比如我起初是研究十九世纪英美文学的,但后来却转而研究唐宋词(见拙作《词与文类》),之后又研究六朝文学(见拙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近年则转为明、清研究(见专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及有关吴伟业、钱谦益、王士祯、龚自珍等单篇文章)和性别研究(见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国女作家选集》等书)。
最近三四年来,由于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合编)的缘故,想不到爱上了填补文学史空白的工作。开始时,做这个别人不干我独干的工作,主要是出于自己任主编的责任感,干到最后,不但干出了热情,也得到了一定的收获。
传统的文学史存在着许多盲点。就拿有明一代的文学来说,至少在西方汉学界,就明显地存在着偏重晚明而忽视前中期的问题。这一失衡的文学史叙述通常多在强调1550年之后的明代文学多么重要,而在此前的近二百年间,似乎都无足称道,但事实远非如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明初和中叶的文学都很值得重新审视。而《剑桥中国文学史》本来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填补文学史上的空白,所以非得开辟有关明代前中期的一章不可。作为主编,筚路蓝缕的事当然应由自己挑头,就这样我接受了撰写这一章的挑战(该章也正好是《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的首章)。在撰写该章的过程中,我边纠偏边拾遗,努力设法把一段长期受忽视的文学史阶段如实地陈述出来。为叙述方便,我将明代早中期文学分为三期:1400-1450为第一期;1450-1520为第二期;1520-1570为第三期。
在第一期的五十年中(1400-1450),我描写士人为摆脱政治恐怖所做的努力。经过了数十年的文字狱迫害,风雅的官员们渐渐学会“台阁体”的赋诗属文,以颂扬新王朝的确立。之所以把1400年(而不是明朝的开国年代1368年)作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上卷和下卷的分水岭,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几乎所有目前的中国文学史都把文学史和朝代的政治史合而为一;但《剑桥中国文学史》要提出的一个新观念就是:文学史不必与朝代的政治史等同,虽然二者息息相关。当然分期法(periodization)经常是十分主观的,每个文学史都有其特定的目标。我和宇文所安之所以决定把1400当作上下卷的分水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几个主要欧洲国家的《剑桥文学史》也恰好大都从1400年左右开始的,如俄国、德国和意大利文学史等。这样可以让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更加有跨国界的比较视野(换言之,我们可以让西方读者们认识到,这些国家的文学史在时间上只相当于中国文学史的下卷,足见中国文学史之源远流长)。而且学习英国文学的人都知道,1400年是一个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时代,如著名的乔叟Chaucer在那年去世了;在1400年之前半世纪,薄伽丘写的《十日谈》大约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的,那时的欧洲也正好出现了类似于“非典”的瘟疫黑死病,所以大家把精力都放在说故事上,实际上是由于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才出现了《十日谈》这样一本书。1400年左右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那时明朝刚开始了三十多年,也逐渐由朱元璋的恐怖政策慢慢安定了下来,虽然高压政策还是不断。以1400年作为分水岭,就等于是以永乐皇帝的时代作为第二卷的开始,我认为这不但是在文化上和文学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水岭。此外,大约从永乐年间以后,中国文学就慢慢变得比较多元化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流行的字——diversity——表示其多样性。
第二期(1450-1520)始于著名的“土木之变”,在这个英宗被俘后的不幸年代,朝廷明显暴露出自己的弱势,随着压迫和控制衰减,第一期存在的恐怖与沉默日渐消除,文学创作相应地繁荣起来。在这七十年中,作家们不只得到了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机会,他们还敢于把批评的锋芒指向腐败的宦官和其他高级官员,指斥他们误导了皇上。基于这些变化,文学的权力中心逐渐从朝廷转向了个体写作者。这也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大多数皇帝,尽管不是特别有能力的统治者,却对文化与教育活动给予了极大支持。突出的例子就是复位的皇帝明英宗,他尽管人品上臭名昭著,却在学校体制上做了不少政策变动——特别是安排了学官,并扩大了学校规模。这一重要变化导致地方学校中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以至于到十六世纪初期,学校中的学生数已达到史无前例的二十四万四千三百人。这种大的文化氛围,也使得识字率有所增加。而这一时期尤其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皇帝推进了戏剧与民谣文化。大体上说,皇帝对歌唱文化的支持为明朝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音乐、口头与书面文学构成了共同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明代中叶许多士大夫形成了多种知识共存的观念,坚信文学家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这种观念或许受到永乐皇帝早期编永乐大典那种全才思想的影响,但直到明代中期全面的心智才在文学领域有所体现。毋庸置疑,这种观念改变了文学的方向。正因为此,1450年之后中国文学的成果异常丰富。
第三期(1520-1570)主要集中在嘉靖年间(1522-1566),世宗在位的四十五年中,不止沿海长期受倭寇骚扰,北京还再次遭蒙古进犯。为国家安全计,朝廷及时采取了通商议和的政策。在此期间,不断有正直的官员冒死进谏,批评昏乱的朝政,而拒不纳谏的世宗则对谏诤者严酷打击,致使不少大臣都倒毙在臭名昭著的廷杖之下。堂堂的朝廷命臣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情景常出现在通俗小说中,小说书写历史的时代由此开始了。与此同时,印刷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很多长篇小说和各种文体的作品由坊间大量推出,就某些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而言,明代中期文学的盛况并不比欧洲的文艺复兴逊色。
总之,我希望这个填补空白的尝试将来也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和兴趣,进而促成更加深入的探讨。同时,经过这一次重写文学史的实际操作,我终于走出了汉学界那种墨守成规的设限,踏入了跨国界文学的文化影响,而瞿佑(1347-1433)及其《剪灯新话》在明初乃至其后的遭遇正好给我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案例。有关瞿佑,我已经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英文,一篇中文),都牵涉到明初文人的命运及其作品的遭遇和政治涵义等。在文章里,我从接受史的角度来重新探讨瞿佑的《剪灯新话》。《剪灯新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被查禁的小说,也是最早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中国古典小说集。它从十五世纪开始就风行于韩国,后来也一直在日本和越南盛传,然而唯独在中国,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淹没。该书之所以长期在中国境内被遗忘,追根究底,实与它曾被明朝政府查禁有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瞿佑是一位懂得抓住大众读者、且具魅力的作家。虽然当他在世时,由于明初官方思想的严禁,他并未享受一个“名家”所应当享受的愉悦和满足,但在他身后,他的文学声音却传播到海外诸国,使得《剪灯新话》成为异国的经典,因而终于被典藏下来,足见命运还是公平的。文人虽然生前遭遇迫害,但在身后可以借着文学作品变得通达。据我的考证,《剪灯新话》的故事情节之所以特别受东亚诸国的读者的欢迎,乃是由于其叙事上的当代背景。由于他所写的故事多半发生在元末明初,故对战乱所造成的伤亡尤多纪实的描写。读这些故事,读者很容易读出作者瞿佑反对穷兵黩武的声音,以及那直率而生动的文字所传达的凛然正义。同时,由战乱而引起的人间悲剧也特别让读者感动。巧合的是,当《剪灯新话》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开始盛行的时候,也正是这些国家刚经变乱、还在动荡不安的期间。从研究瞿佑的过程中,我深深体验到,我们今日有必要把文学作品放在“过去”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考虑。就如美国叙事学学者渥拉斯·马丁(Wallace Martin) 所说,“叙事学”本来就是“一种了解过去的方法”(“a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the past”) 。我希望借着研究瞿佑《剪灯新话》的文学性与其时代性,能对“过去”又多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另外,由于对于“过去”的重新关注,我也庆幸自己能对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文学史作了一些“补白”的研究工作。例如,在最近一篇有关金天翮(1873-1947)的文章里(已译成中文,将在国内《中山大学学报》刊登),我曾讨论金如何发挥苏州人以诗证史的强烈抒情声音——那是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以降,苏州在世人心目中所代表的一种以诗歌见证人间苦难和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声音(另一方面,苏州则以自成格局的园林著称,被艺术家塑造为宁静悠远的梦幻境界)。在目前的学术界里,大多数的学者只记得金天翮那部鼓吹女权的先驱作品《女界钟》(初版于1903年),但却忘了在当时的时代里,金的革命思想和诗文创作曾风靡一时。而且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上,金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金是宫崎滔天(1870-1922)的著名自传《三十三年の梦》(孙中山序)的中译者。此外,金主要还是因为受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AtL6x61lupfV3wL8wqH+SQ==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