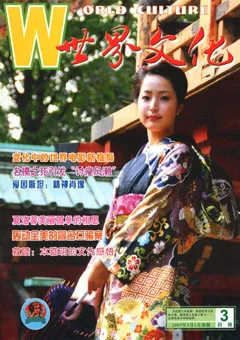彼得大帝的“东方使团”
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他力图使俄国融入欧洲文明社会,摆脱俄罗斯民族中野蛮、落后、保守的特征。彼得大帝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同时也把触角伸向了遥远的东方。欧亚大陆上一北一东两个民族,由于一个宗教使团的出现,发生了奇妙的联系。
一
自16世纪晚期起,一场堪与美国“西进运动”媲美的“东进大潮”轰轰烈烈地席卷了西伯利亚大陆。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俄国哥萨克骑兵的铁蹄已经踏入了中国黑龙江地区(即阿穆尔河流域),掠夺当地居民的毛皮制品和粮食作物。
面对咄咄逼人的沙俄入侵势力,清朝政府加强了东北边疆的防卫。1684年,中俄军队在雅克萨城爆发了战争。中国凭借强盛国力和康熙皇帝的坚定决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在1689年与俄国签署了划定边境的《尼布楚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战后一部分俄军战俘留在黑龙江,另一部分随清军来到了北京。清政府把他们编为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于北京城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还为他们专门设立了一所东正教教堂——圣尼古拉教堂(中国人称之为“罗刹庙”,又因与后来设立的俄罗斯使馆位置关系得名“北馆”)。为了使这些战俘牢记自己的信仰,俄国教会通过各种途径送来教堂用具和信函,鼓励随同战俘来到北京的神父马·列昂季耶夫将神圣的东正教事业发扬光大,争取更多的教徒。
由于俄国战俘的归化,东正教在北京意外地获得立足之地,沙俄政府对它寄予了很大希望。1698年,彼得大帝就如何精心经营东正教在北京这个惟一的据点向西伯利亚衙门长官维尼乌斯作出指示:“此事甚善,惟为上帝起见,行事宜谨慎,戒鲁莽,以免结怨于中国官员及在当地栖身多年的耶稣会士。为此所需要的,不是学有根底,而是谙于世故的神父,方免偶因傲慢而使上述神圣事业一败涂地,像在日本发生的那样。”
为了表示对远东传教事业的重视,彼得大帝于1700年6月18日亲自指示,在托博尔斯克设立主教区,“庶几上蒙天恩,逐步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愚妄无知、执迷不悟的生灵,皈依真正的上帝”。1712年俄方商队专员胡佳科夫向清朝理藩院请求派人接替年迈的马·列昂季耶夫,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准许。在彼得大帝的授意下,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约翰迅速确定了传教士团人选。直至1714年,清朝内阁中书兼侍读图理琛访问土尔扈特部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沙俄政府从托博尔斯克派神父等十余人与之随行。
二
公元1715年4月30日,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抵达北京,领班为伊拉里昂·列扎依斯基,成员包括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修士辅基菲利蒙以及教堂差役人员7人。领班和司祭分别被授予五品和七品官衔,每人得到了从600两到200两数量不等的补贴,此外每月还向他们发放俸禄。从传教士团享受的优厚待遇来看,清政府以“怀柔远人”政策对待远道而来的外国“喇嘛”,清朝官员不仅经常问候俄国传教士团和战俘的生活情况,还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
起初的俄国战俘及其后代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很快冷漠了自己的信仰,据《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记载,“这些阿尔巴津人除少数以外,其他人从在北京定居之日起就对基督教毫无诚意”。教团在发展中国教徒事业方面进展极为缓慢,1731年仅有25名中国人受洗,与西欧天主教的势力远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它又被称为“不传教的传教团”。在这种情况下,“传教”更像是执行其他任务的一个幌子。
自1720年彼得大帝对教会实行改革以来,俄国取消了牧首制,设立了“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作为东正教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一机构直接听命于沙皇。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实质上成了沙俄政府驻北京的一个官方代理机构,执行着沙俄政府的对华政策,它的工作内容已经转为“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沙俄政府要求传教团成员掌握中国语言,表面看是为了“允许北京的修士司祭可以使用汉语接受教徒的忏悔”,真正目的在于与中国的权势阶层拉拢关系,谋取有价值的信息。在“最高宗务会议”向第七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的训令中,已经明确地道出了这一点,“尔修士大司祭于驻北京期间,一有机会就应尽量把当地动态认真详细地写成材料上报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如果国家事务有什么必须保守秘密的事情,那么绝对不能在私人信件中提及”。
许多杰出的成员潜心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研究,客观上促进了中俄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活动。第三届传教士团学员列昂季耶夫是第一个将《易经》、《大学》、《中庸》、《三字经》等儒学经典译介到俄国的学者。列昂季耶夫在《雄蜂》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即《名臣奏议》中的《为太中上皇帝应召书》)译文,对俄国沙皇婉言劝喻。
几乎每一位成员来华之前都被委以收集中国典籍的任务。第二届传教团学员罗索欣向俄国皇家科学院图书馆贡献了107本汉满文书籍和两幅中国地图,比丘林回国携带的书籍超过了前几届传教士团的总和,总重量达到400普特(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而王西里在北京居留期间共为喀山大学收集了849种2737卷14447册珍贵的抄本和刻本图书。
1727年,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通过《恰克图条约》获得了合法地位,从而得以在中国永久地居留下去。此后,大约每隔10年教团成员就要更替一次。
三
彼得大帝去世以后,他的继承者继续推行“火枪与圣器并举”的扩张政策。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中,俄国通过在北京的关系维持并扩大着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通过加大对传教士团的投入不断赋予它更为重要的职能与责任。传教士团像是深谋远虑的彼得大帝在中国皇城根下安置的一匹“特洛伊木马”,每当关键时刻便能发挥出奇制胜的作用,令其他欧洲国家羡慕不已。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伊帕托娃所言:“北京传教士团的外交活动可以比作一座冰山,其看不到的水下部分要远远超过看得见的水上部分。”
与传教士团的政治功能相比,它的文化职能影响要更为深远。团员收集中国情报的活动虽然带有明确的政治色彩,体现出俄国政府的野心与阴谋,但它对于俄国汉学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传教团中涌现出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如19世纪上半期的比丘林以及下半期的王西里和巴拉第,被后人奉为俄国汉学的三大巨头,他们对中国哲学与宗教、历史与地理、语言与文学、社会与法律,甚至农业、天文和经济都有相当数量的专著传世。这些足以说明传教士团在中俄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交流的丰富内涵。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苏维埃政权下的莫斯科牧首区决裂,宣布接受流亡在塞尔维亚的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的领导。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彼得大帝开创的“东方使团”寿终正寝,它像历史长河里的一块巨礁,曾经引起滔天巨浪,此时被冲刷成为一粒尘埃,消失在滚滚波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