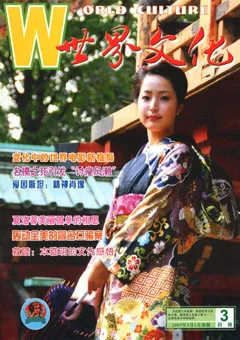非典型性励志电影——《时尚女魔头》
本来我最先想到的立意无非是时尚界的皮囊和灵魂、浮华和苍白、光鲜和落寞的种种辨证,但看了这部影片后却蓦然发现它其实还是个包含着关于寻找和迷失、失去和得到的励志故事,只是,话题的外壳太耀眼,太令人目眩,以致于显得并不怎么典型。
《时尚女魔头》是我觉得还算中肯的一个译名,“The Devil Wears Prada”,直译叫做“穿Prada的恶魔”,原著小说的题目就是如此的恶狠狠,充满着诅咒的味道,还有成语化的译名叫“衣冠禽兽”,更加的恶狠狠,我不喜欢。做人要厚道,每一个领域都有它的潜规则,同理,每一个领域的统治者也都会有各异的“君临天下”的方式。如果一个人选择了某个领域,负责任的话,惟有去迅速的适应,而不是抱怨,因为那是你的选择,有什么样的代价也是这份选择的寄生物或者说是附属品,就像在超市买洗发水,总有小瓶装捆绑销售,如果你觉得物有不值为其所困,就放开它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其他选项,如果又放不开,也不要再抱怨,无论如何,那是你做出的选择。
“成千上万个女孩都梦想着这份工作。”
自从安迪·萨克丝进入Runway杂志的那一天起,就有无数人无数次的对她重复着这句话。“梦想”是个表意多么美好的词汇啊,可英文原台词里用了这样一个词组:“die for”,有点削尖脑袋,头破血流的意思,中文太折中、太温和,但在世界顶尖时尚秀场的大舞台上,尽管云集着世界顶尖的优雅和气质,但一个“die for”,一样的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它杀人不见血,慢慢腐蚀人的灵魂,禁锢人的思维,迷失人的意志。也许我形容的有点过于残酷和夸张,但安迪·萨克丝第一天自信满满的走进那栋摩天大厦的时候,她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很多人说片中的Runway杂志其实是在影射著名的Vogue(《时尚》),这本全世界的女孩和女人都称之为“时尚圣经”的流行宝典。可是谁又能想象这样一本伟大杂志的操盘者——也许我们该加冕其为“时尚圣母”——却会有着一副穷奢极欲的“女魔头”的真实面目呢?
米兰达·普雷丝丽就是这个传说中的穿Prada的恶魔,还未亮相,先把逼人的气场带进了屏幕。当时年轻、纯洁、朝气蓬勃的安迪正紧张不安的等待着米兰达的面试,她学生气十足的毛衫和外衣刚被众人毫不遮掩的讽刺为“一场灾难”。这时米兰达的首席助理接到米兰达一个电话,只见这个冷若冰霜的漂亮女孩忽然从她四平八稳的烟熏装下迸发出一个惊恐无比的表情——老板提早15分钟到达——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像龙卷风般的忙乱起来,没人顾得上不知所措的安迪。然后我们看到了一双高跟鞋从车门迈出,一副墨镜映着阳光,我一下想到了剑刃上寒气逼人的光泽。她走进电梯,先于她一步进电梯的女孩立刻说声“抱歉”仓惶而逃,宁可花时间去等下一部。再然后,在办公室众人节奏混乱鸡飞狗跳的瞬间,大名鼎鼎的米兰达踩着冰冷的步伐,正式亮相。
她如此的典型,因为她如此的干练,安排工作时的讲话至少3分钟没有停顿,语调也没有丝毫起伏的发布着各种琐碎指令。安迪带着她漂亮的简历和讨巧微笑站在米兰达面前时,米兰达的表情却分明是三分玩味审视七分嘲笑,面对一个“时尚盲”,米兰达大概觉得很新鲜,被她炒掉的助理无数,那些纤瘦、漂亮的,大概总是野心勃勃,甚至有足够多资本去自负的女孩,却为了这一份工作尝到了人生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安迪是个异类,她不合时宜的着装和态度为她赢得了机会,这是多么的出人意料,我们能在烟熏装首席助理小姐——她叫爱丽丝——的脸上看到冰山一角。
再来说说安迪,基本上我可以认定她属于“文青”一类的人物:漫不经心的打扮,略有懒散的作息,偶尔为了讨好男友还会从性感内衣上做做学问。她有好的学历,不入俗流的理想,她来Runway的理由很简单,只是期待着一个跳板。因为江湖传言,只要能在这里工作一年,便可以在纽约任何一家杂志社谋到工作,而她的终极理想,是在另一个领域同样大名鼎鼎的《纽约客》。没有任何虚荣心目的的驱使,她为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单纯的开心。
安迪有她的朋友圈,经常聚餐的一千人看得出也属于“文青”。安迪的男友,长相酷似中东人,普通,不帅,似乎是个厨师,烹不出法式大餐,但他的居家式快餐却深受女友青睐。
安迪的工作也很不顺利,一切都无从适应。第一天上班,她还不知道D&G里Gabbana的拼写,而Runway显然也不是一个宽容的平台。这时安迪表现出了让人敬佩的韧性,她为了获得哪怕一点点的融入感而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只可惜效果不是很好。米兰达下达的命令几乎全是一些“碟中碟”级别的“Mission Impossible”,她时刻精神紧绷,手机铃声不定时催命,而穿着短裙,捧着数杯咖啡一路小跑的本事也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习得的。尽管如此,安迪也还是得不到一句来自老板的肯定和理解。米兰达就是一切的准则,哪怕她说“让足球变方,让煤球变白”,你做不到,那也纯粹是你的问题。想想自己,上班半年,很多事情从零学起,单位同事从未诘难于我,惟有为融入感笨拙投入的心力可惺惺相惜一下。
安迪做到了,她的表现甚至得到了爱丽丝酸溜溜的侧目;她变得漂亮了,唇红齿白,服装每日一换,小跑奔忙不变,形象却已是耳目一新。
“什么时候你的个人生活一团糟了,就意味着你晋升了。”
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在毫无觉察间竟然丢掉了自己非常珍贵的东西,比如一些记忆,一些感情。
有时候是这样,你目睹着它脱手了,破碎了,当面是一种心痛,但我更害怕在无知无觉间的丢失。就像有些东西你笃定就是自己的,反而会轻慢和不在意,甚至什么时候自己的记忆被擦抹了,事后想想都是惘然,也许你觉得丢掉的那样东西一直牢靠的待在身边不远的地方,某一日想起它,再去熟悉的地方找,它却没有了。我很害怕,因为这样的丢失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怎么丢的,是自己的疏忽吗?全都没有答案。懊悔也好,焦虑也罢,它离你而去了,永远找不回来,永远嫌自己的醒悟太迟。
我为什么说“The Devil Wears Prada”是部励志电影,原因就在于影片结束时安迪和米兰达的微笑。这两个微笑来自不同的面颊,牵动的肌肉有着不同的弧度和力度,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某种程度上讲,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米兰达是个坚定的女人,她明白自己的位置高处不胜寒,但能动用一切手段保卫它固若金汤;安迪也没有让那样回不了头的千古之谜成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在她所看重的人或事离她而去之前,她觉悟了、挽留了,于是生活还是她的,爱情还是她的,事业可以重新开始,一切回归正轨。
倒叙结束,先让我们回到安迪的晋升,和她一团糟的生活。
米兰达每日会以相同的方式向自己的助理道“早安”:她用咄咄逼人的力度和气势把她漂亮的Prada提包和昂贵的Prada大衣摔在助理的桌子上。动作虽然一成不变,但甩在桌子上的大衣和手包的样式却无一日重复。安迪就在这样独特的早安问候中慢慢轻车熟路,她得到了一些更重要、需要更熟络工作能力的任务,同时,这些任务的难度和变态指数也与日俱增。
她的“文青”情调没有了,穿衣打扮,馈赠礼品,甚至说话的腔调部沾染了很多物质女郎独有的特质,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副匆匆忙忙的表情:和朋友聚餐,和父亲团聚,和男友亲热……米兰达的电话可以让她推掉一切休闲时间,然而也就在这样的匆匆忙忙间,很多东西慢慢引退和疏远,她没有察觉。
这就是Runway教给她第二条终极教义:“什么时候你的个人生活一团糟了,就意味着你晋升了。”终于,安迪慢慢排挤掉爱丽丝“首席助理”的位置,直到有一天,几乎全权取而代之。爱丽丝很愤怒,她用歇斯底里的不雅吃相作为宣泄的途径。安迪的歉意是真诚的,但她也觉得自己很无辜,别无选择,成千上万个女孩情愿为之die for的工作,怎么不会优胜劣汰呢?这还是你教给我的。
然而刚刚和男友分手的安迪还来不及神伤和反思,就作为“精英团队”的陪同跟随米兰达来到巴黎出席时装周。巴黎时装周,即使是我们这些外行人,也知道它对时尚圈来说意味着什么,华服云鬓,觥筹交错,安迪在镁光灯闪烁的间歇偷偷的笑,面对这样的繁华,不是每个人都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
但繁华是短暂的,繁华的背后有什么,安迪并不知道。
在巴黎发生了很多事:米兰达离婚了,这是她第6次破裂婚姻的终点,在电影里我们惟一一次看到“时尚教母”脂粉不施的样子,憔悴黯淡得让人心悸;安迪遭到了风度翩翩的同行的勾引,一夜激情后,在这位同行的口中得知了一个残酷的内幕:有人将把米兰达在《Runway》的主编位置取而代之。安迪慌忙跑去通知米兰达,想先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但米兰达却对这个消息不屑一顾,而事实也证明,安迪的担心完全多余,米兰达之所以能在风口浪尖的主编位置上始终颐指气使,自然有她的信息网和手腕,她踩着多少人的头爬到了今天的位置,远远超出了安迪的想象。
当时尚界的酷寒真正侵入安迪内心深处的时候,她做出了令人佩服的决定:离开。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幡然醒悟是要建立在不怕放弃、不怕重新开始、不受功名利禄诱惑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安迪洒脱的把引诱自己的情人抛到一边、把米兰达正在呼入的电话丢进喷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后,她“文青”的个性终于还是占了上风。回到纽约后她开始着手重建差点迷失的心灵家园:辞职、和男友重新沟通、投简历去了《纽约客》。米兰达还是一贯的刻薄,她在安迪的档案里写道:“她是我见过的最差助理”,但也正是这个评语,帮安迪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工作,据《纽约客》负责面试的高端人物说:“能获得米兰达如此评价的人,一定是做了什么正义的事情。”
然后就是那两个微笑,安迪的微笑由衷而快乐,她一直微笑,在人流里,在大街上;米兰达的微笑带着一点点诡异,转瞬即逝。这是两个本不应该有交集的人,重新平行后,介入又撤出的一方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我来讲,这就是一部励志电影,虽然不典型,但也可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定位,追问自己到底何欲何求,结论慢慢会出现,在丢失那件珍贵的东西之前,权当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