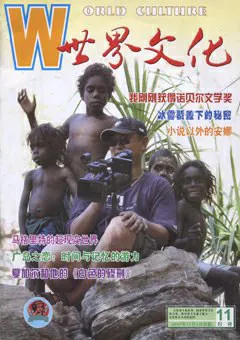植根于文化中的爱情观
爱情与等级
每个民族都有它千年传诵的神话爱情故事。在中国,最著名的有牛郎与织女、许仙与白娘子的传说;在西方,则有丘比特和普赛克、宙斯与欧罗巴等。这些爱情故事都发生在神与人之间,而它们的结局,它们所折射的对于人性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在中国,统治阶层似乎始终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权力的代表,他们于社会道德的维持责任要求他们以禁欲为美,因而对于爱情,往往麻木漠视甚至不屑一顾,他们维护的只有社会礼教秩序,一切有违于权力平衡的爱情和人性追求,都需抹煞消灭。因而,牛郎织女和许仙的爱情故事,最终毁于无边的法力。在电影《大话西游》中,我们也发现:至尊宝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他与紫霞仙子和白晶晶的爱情,便须服从于更大的权力压迫。白晶晶的选择便明显地解读了这种爱情的结局:要么选择退出以明哲保身,要么在爱情的灿烂中被压迫致死。因而中国传说故事中的人神(或人鬼)爱情,只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人们对于等级伦理压迫人性的无奈和微弱的抗争。
另一方面,这种等级制度对于爱情的扼杀,正体现了重社会平衡而轻个性发展的道德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和”,便须讲究“礼法”。这种礼法,在董仲舒那里,便成为了“三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可见,等级制度,是上天制订的伦理,由不得人们改变。荀子也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这种社会等级结构的平衡学说,使得超越等级的爱情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而最终夭折甚至胎死腹中。
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神与人的爱情故事却比比皆是,且大多圆满幸福。无论是丘比特与凡人普赛克的爱情也好,还是宙斯与欧罗巴公主的浪漫故事也好,最终都在人性的光环中结出了美丽的种子。在这里,人性并没有因为神性而消亡,人与神的爱情故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可以大胆的说,西方的神实质上是人化身的神,他们有神力,却经历着和人一样的情感,爱情在他们眼里和凡人一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神——有人性光芒的神。这也奠定了西方文化中爱情至上、爱情平等的地位。
在这样对爱情的看法和行为中,我们觉察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平民化传统:属于人性的爱情,并不是凡人的专利;权力和等级,在爱情面前,显得卑微软弱;维持社会平衡的,不是权力和等级,而是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情感素质。这也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一个伟大传统。
爱情与权力
虽然中西方文化中,爱情的地位不尽相同,但是无论何时,爱情都会遭遇权力政治的干涉,为权力所用。此时,在爱情和权力间作出不同的抉择,正体现了一个社会对于人的深刻思考。
名垂青史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分别与罗马将军恺撒以及马克·安东尼有过恋情,而且他们的恋情,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曾经影响了埃及和当时世界的历史。克娄巴特拉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美艳,让恺撒和安东尼为她的政治目标——保卫埃及的独立而前仆后继。勿庸置疑,她的爱情是美丽而崇高的;但是,不幸的是,她的爱情却附属给了政治需要:她利用了爱情,或者说,她的爱情被政治利用了。就她和她的时代看来,王朝的使命远远重于个人的情感。
在一个政治需要和国家意志被视作绝对价值的时代,以爱情的牺牲换取政治的利益,往往是未可厚非的,甚至会得到那个时代人民的认同;但如果为了爱情,置权力而不顾,则常常为人所不理解。
唐明皇早年勤政,创历史上的“开元盛世”。但晚年热恋上自己的儿媳妇杨贵妃,并宠幸有加,“君王从此不早朝”。勿庸置疑,他们的爱情刻骨铭心;可是我们似乎不肯承认唐杨之间的“爱情”,而宁愿说他生活“骄奢无度”、“沉湎女色”。或许皇帝确实不需要爱情,唐明皇的悲剧,正在于他的贪婪:他追求爱情,却企图以他的权力服膺爱情——这不仅违背了社会伦理,更使国家陷入动荡。他需要爱情,却来不及将政治放手。在人性和权力的关系中,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对他们而言,想要爱情,想要做一个完整而自由的人,便要懂得放弃。爱德华八世与沃利斯·辛普森的爱情故事正可以说明这点。1936年,当爱德华八世向王室宣布要和沃利斯结婚遭到强烈反对时,他毅然决定逊位来完成这桩亘古未有的婚姻,并于1937年在法国与沃利斯成婚。爱情与权利,仿佛是熊掌与鱼,断不可兼得!在政治面前,爱德华选择了爱情,放弃了地位,却同时也完成了人的意义。这或许是西方骑士文化中对爱情崇拜的体现,同时,也是西方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民主博爱平等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结果。
爱情与自由
爱情虽然时刻受到等级礼教和政治权力的干扰,但它的核心价值,却是自由。爱情的自由既包括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身体和行动的自由,更包括它对于人性解放所要求的心灵自由。就这一点而言,无论中西文化,人们对之的渴望是一致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文化所反映出的心态却不尽相同。
在中国,据《周礼·地宫·媒氏》记载:“仲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诗经》中也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描述。可见,先秦时代尚是一个两性关系自由开放的时代。而当两汉独尊儒术之后,封建礼教日益加强,两性间的交往逐渐变得严格起来,“男女授受不亲”,青年男女几乎没有机会可以自由地吐露爱情的心声。尤其在爱人的选择上,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可言。为了达到维持社会平衡的目的,婚姻(而且是他人包办的婚姻)替代了爱情,个人的情欲和对异性的审美需求被无限期搁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对于爱情的自由追求,首先表现在对爱人的自主选择之中。
这种选择精神,首先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中得到了体现。他们的故事,象征意义甚于实际意义:爱情虽或存在,但感动人的,则是他们对封建家庭等级观念的挑战。正因如此,“私奔”这一不无贬义的行为才能博得后人的同情与钦佩。
但是,这种反抗精神,并不能替代对爱情的追求和审视。事实上,即便是倒戈一击的青年男女,在他们获得婚姻选择的短暂胜利之后,仍会重新回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路,补上封建婚姻礼教的课。因此,我们可以说,封建的爱情观,已经作为一种奴性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之中了,偶尔的叛逆根本扭转不了观念的顽固。梁山伯与祝英台对爱情的誓死追求,固然引发人们对中国传统道德礼教的批判,但是主人公对待爱情所表现的清醒、理智和成熟,又何尝不是因为他们对封建礼教尚存有幻想,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得到道德社会的宽恕和成全?可见,封建爱情的悲剧,是一种依附人格的悲剧。“化蝶”的意象,便清楚地昭示着:真正的爱情自由,只是一种幻想,一种在虚拟的梦幻中才能实现的境界。
对西方而言,他们的爱情观往往是狂热、毫无顾忌的,从中引发的纷争也就更为激烈。纵观西方文学,我们发现,他们对于爱情的描写,无所顾忌,在勇敢地赞美外貌、表达爱慕,也同时无不包含着强烈的性爱因素。罗伯特·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
啊,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
在六月里苞放。
啊,我的爱人像一支乐曲,
乐声美妙、悠扬。
你那麽美,漂亮的姑娘,
我爱你那麽深切,
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涸竭。
这种直白,少了曲折的美,却将爱的意蕴推到了极致。在许多时候,爱情的至高无上,可以使人们为此作出一切,以致去和人决斗。相比中国的想象自由,西方的爱情更注重表达自由。为了表达自由,他们也会选择“私奔”,选择抗争。但那抗争,更多的是基于对自身独立人格的理解,而非简单的对权势压迫的反叛。
爱情与婚姻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都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搬到一个地方,即便四邻八舍对他的性情想法一无所知,但大家既抱有这样的真理,因而总将这样的单身汉看作是自己某个女儿应得的财产。
这是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的开篇一段话,它引出了一场关于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经典故事。小说中夏洛蒂和柯林斯尽管婚后过着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婚姻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形式存在的需要;而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结合,由于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因而幸福美满……这个故事似乎是对婚姻和爱情之关系的很好注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因此指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在实践中并非如此明了,尤其是将它们置于社会伦理价值之中时,孰重孰轻更成了千古难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礼轻爱、男尊女卑。婚姻只作为一种维持社会平衡的“礼数”而存在着。汉代郑玄说:“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诗·郑风丰笺》)因而,中国古代婚姻事实上是一种家族礼仪,而非个人行为;所有的形式,从择偶到成婚,都须由媒人与父母参预或做主,即古书所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诗·齐风·南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这种重视婚姻礼法的价值观,可能会造成婚姻中最本质的缺憾:即情感和性爱被忽视,婚姻脱离了爱情,成为了家族等级制度的附庸。之中原因,恐怕是中国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缺乏人文主义传统。朱光潜先生在《中西爱情诗》中便指出,西方人认为恋爱本身是一种价值,恋爱有一套宗教背景,还有一套哲学理论,最纯洁的是灵魂的契合……而中国人,却一向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他们将婚姻(礼仪)视作个人价值为社会所认可的重要途径,也在事实上将之视为维持父系权力关系的有效的符号手段。他们的实用主义思想,使他们很难将婚姻视作爱情的神圣归宿。
这种将爱情游离于婚姻之外的观念相当地根深蒂固,即便在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那里,也未见动摇。譬如胡适先生,在其婚姻生活上,便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从未谋面的江冬秀为妻;不仅如此,在《贞操问题》中,他甚至道,中国人的爱情是在“既定名分之上”才产生的。直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婚姻和爱情观才在事实上逐渐发生改变;同时,随着从表面的婚姻形式到深层的婚姻制度所发生的明显变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婚姻的基础应当是爱情。
相比之下,在爱情与婚姻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显得比较宽容,他们视爱情为至尊,即便这种爱情发生在同性之间。比如柏拉图就坚信“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能够让人得到升华的情感,而唯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唯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萨特与西蒙·波伏娃就是广为传颂的柏拉图式恋爱的精典,他们一方面保持亲近的、永不结婚的爱情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干预彼此的私生活。正是在这种理解与宽容的爱情中,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没有结婚,但却情投意合,并将这份情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
可以说,在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中,西方注重爱情的过程,而中国强调作为形式与结果的婚姻。就本质而言,婚姻签订的是道德责任义务,而爱情赋予的是精神动力。爱情张显的是个性,而婚姻标注的是社会性;爱情要求独立,而婚姻强调和谐;爱情追求自由,而婚姻注重契约。没有爱情的婚姻也会和睦,而仅有爱情的婚姻也不一定会美满。对爱情和婚姻的本质不同的理解必然决定爱情与婚姻的取舍不同。
爱情是不分时间和空间的,爱情给予的力量一直感动和震撼着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心灵。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爱情都是一种向往美丽的理想。但是当历史走到今天,物质条件的优越、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压力的增大,却使爱情愈来愈与现实绑定。许多人开始远离理想,更多的人愿意相信现实。当理性和科学侵占了人们的生活时,爱情正逐渐失去神性的光环。传统庄严的爱情观,正被轻松搞笑、务实自白的语言所描绘。或许爱情和婚姻的价值在分裂,但唯有这个时候,当我们审视爱情所带来的文化意义时,我们更觉得它的荡气回肠的力量!更发现爱情所带来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