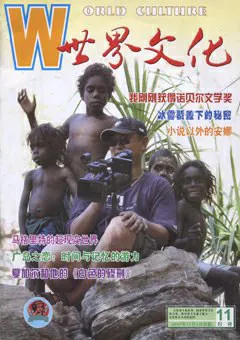安德鲁·魏斯的精神世界
安德鲁·魏斯十分静谧,静谧得像一个肃穆的梦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德鲁·魏斯可以被视为一个圣徒,他把绘画当成一种宗教仪式,虔诚地对待它。因此,在魏斯的画里就很少有尘世的喧嚣。有的画里无人,有的画里有很少的人(在我所见的两本画册里,只有一幅题为《约翰·奥森的葬礼》的水彩画中有8个影影绰绰的人影)。有人的画,有的是一名老人,或是一名妇女在屋子里、阁楼上或房门前、原野上静静地坐着或卧着,有的是一个青年或一个孩子在原野上怅惘地默立或忧郁地沉思。还有一幅画里有个不算美丽的女人很真切很羞怯的裸体。除了人之外,安德鲁·魏斯的画里就是原野:单调的长着青草和枯草的原野,长着稀落的树木的原野和敷着月光与白雪的原野,以及那两幢经常出现的木屋和牲口栅(那是典型的美国东部农场风景)。
在那个世界里,风很凉,阳光很清洁,没有灰尘去过滤它,原野也很辽阔,像古典音乐那样缓缓起伏的山岗和原野徘徊着十分辽远和寂寥的诗情。安德鲁·魏斯在那个世界里放牧着他宝贵的脆弱而刚强的灵魂。上帝就是这位美国艺术家亘古长存的独特的美感和爱。
一位中国评论家说安德鲁·魏斯是美国乡村生活的歌手,另一位中国评论家说他是美国心理写实主义和地方写实主义画家。这些都是套在安德鲁·魏斯的人生和艺术上的一堆僵硬而凋残的铁线蕨,安德鲁·魏斯应该什么主义者也不是,他就是一个真纯端庄的艺术家。一切人的艺术,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应该只有两个分类,一个是真,一个是假,衡量它们的唯一尺度应该是一个:抒情和爱。无论是提香和拉斐尔的绘画,还是兰波和马拉美的诗篇,抑或是德彪西和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它们都以同一种情意步向人类永恒之爱的大殿,并且发出通彻古今的感喟。在安德鲁·魏斯的画里,那几个宁静的若有所思的人,那宾夕法尼亚和缅因州的两个小农场,那淡淡的阳光,那安谧的静物(篷车、篮子、水桶、厨具、死鸡、古船等等),那土色、褐色和深绿色的色彩,都在召唤和呼喊出一片执拗的安德鲁·魏斯的爱情,那是真纯的人真纯的灵魂的告白。
安德鲁·魏斯的世界不存在恨(包括那张题为《巡视》的水彩画里那只孤独的狼)。他的画里那几位老人,无论是《爱国者》里的老人,抑或是《库尔勒人》里的老人,目光都一样宁静,恬然地承受着生命的余裕;还有《出神》里孩子那斜斜的凝视,颤动着湖水那般清冽的波光;那位金发的裸女在安德鲁·魏斯的笔下也分外纯正,灰褐色的眼睛默默地看着你,使你和画家一样心灵澄明,不起纤尘。当然,安德鲁·魏斯不免要表达忧郁和怅惘。那是上帝赐与人类的一种正当的情愫,因为人虽然被放逐了,但他一时一刻也忘不掉,永远都在怀恋着他心中的伊甸园,尽管那是很奢侈的情结。安德鲁·魏斯在孤独之中品味着浓醇的诗意,面对着那片寂静的土地和寂静的生活,他也面临着一种渴求。但他有效地抑制住了某些渴求。于是,在渴求失落之后他的精神世界便出现空白,那块空白就是他作品里的单纯而静谧的安德鲁·魏斯的原野风景。安德鲁·魏斯并不大肆渲染死亡,他的画幅里死亡也不阴森可怖,基里科和布莱克的那种恐惧与他无缘,他永远是在静穆地表述人生的感受,表述怅惘和对死亡的一种近乎敬慕地神秘地臆想和忖度。有两幅画,一幅叫做《漂》,一幅叫做《春》,画里的老人一个躺在平静大海上的一艘木船里,一个躺在黄色的草场的一堆渐渐消融的白雪中。没有风,没有惊涛,海是深沉的蓝色,草场的远处是无云的天空。它们代表了安德鲁·魏斯的一种玄想,那是把死亡当成一种状态来享受的人的邈远的灵魂。
一般来说,艺术家都是在制作感情,以便招引人们的响应,安德鲁·魏斯的艺术世界里没有这种拙笨的陷阱。他很淡漠,像个微带倦态的行者,走在他的那个农场的草地上,他似乎知道,自己不会碰上比他画幅里还多的人,也不会遇上在画幅之外刮来的世纪风,他只对那个孩子那个青年那个老人那个妇女和那个裸体模特儿微微颔首,另外,他还礼拜升起在那片草场之上的属于他安德鲁·魏斯自己的本命神。他用那个伟大的淡漠抗拒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艺术的不可救药的平庸与媚俗,同时也用它来勾画了他自己——艺术家安德鲁·魏斯的艺术和人。因此,可以这样断言:安德鲁·魏斯不属于曾经的20世纪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的各种主义的艺术史家的嘴巴,他只属于艺术。
安德鲁·魏斯是隐蔽在刚刚过去的喧闹的20世纪艺术史深处的一个肃穆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