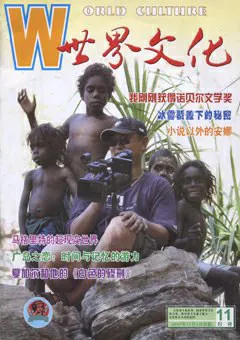体悟法国大革命真谛
悲惨、血腥、残暴,抑或疯狂?读罢《桑松-刽子手世家传奇(1688-1847)》一书,不由得人们要发出如此的感慨。历史的巧合或是机缘,使得桑松家族走上了以刽子手为职业的道路,而在七代人之后,又戏剧性地终结了这个家族的不幸命运。
作者贝尔纳·勒谢尔博尼埃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以桑松家族七代人的生活经历为主线,为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这个家族和刽子手这个职业的不幸,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作为历史见证人的目光,反映法国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这段历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王权的陨落,启蒙思想的酝酿和兴起,大革命的爆发,红色和白色恐怖时期,帝国的创立和灭亡…… 这段历史既跌宕复杂、波澜壮阔,又充满了激荡疯狂、腥风血雨,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课题和惨痛的历史教训。尤其是本书作者大量援引法国大革命前后及其进行过程中的重要人物的言论和同代当事人的佐证,再加上桑松本人的日记(他虽然不能算是个文人,但是,也许与他的职业有关,他的眼光和思考却往往超常的犀利和客观),这些第一手材料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真实可靠的信息。《桑松-刽子手世家传奇(1688-1847)》,它首先是一部史书,是以一种特殊视角反映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和真相。其次,它也是一部刑罚史,反映法国中世纪以来刑罚的演变和兴衰,尤其是断头铡作为执刑工具和刑罚的产生及兴衰。再其次,它也不啻为18世纪至19世纪活脱脱的巴黎市井图。本书跨越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本书第五章展现的18世纪末巴黎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全景,其中不乏诠释法国大革命暴发的方方面面的相关因素。巴黎特有的众多人口,成分的复杂,杂乱的生存环境,比较纵容的道德风尚,发达的商业,促使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奔忙于紧张的白天,也乐于享受活跃的夜生活。这一切构成了巴黎的魅力和诱惑。漫步巴黎城,“每走一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一种新的气氛,映入眼帘的要么是豪华的奢侈品,要么是最令人厌恶的污秽。这使得您不得不把巴黎称作是最神奇又最肮脏的、最芳香又最恶臭的城市。”今人只是知道“巴黎是香水和时尚之都,最具魅力的花花世界”,有谁会想到历史中的巴黎曾有这般不堪入目、不堪入耳、不堪入鼻的景致。此外,巴黎有多少个行业,就被各个特有的风尚和习俗划分成多少个小村落。城中有贵族和富人区,也有平民区。再走远一点,穿过一个小镇,就像到了另一个国家。如:蒙马特、圣-拉匝尔和圣-洛朗区,主要是纺织品生产地;夏佑区集中了铁匠铺和纱厂;鲁尔区聚集了拣破烂儿的;圣-安托万区集中了家具厂家;圣-马赛尔区则集中了染坊、鞣革厂和毛刷厂。巴黎的咖啡馆和酒馆是法国的特有文化,特有景观,它们不仅是人们休闲消遣的地方,更是各行各业、社会各阶层,政治家、哲学家、文人学者、知识分子、兵工学商乐于聚会、交谈、交友、评论时事、甚至是密谋策划的场所。且看法国大革命同代人费里埃侯爵给我们提供的生动写照:“我们无法想像在那里汇聚的各种各样的人,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舞台……那里,一个人在修改和矫正宪法;另一个人在高声朗读一篇抨击文章;在一张桌子上,一个人在指责部长们;所有的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有倾听他的听众……人们在咖啡馆里生活……”此外,巴黎酒馆分布广泛,都有古老的历史。1790年,有人估算,巴黎有4300个出售酒水的地方,即平均每200人有一个酒馆。最密集的地方是塞纳河附近的教区,其次是平民街区,圣-马赛尔镇平均每80个居民就有一个酒馆。大革命期间,每次重大事件的当天,咖啡馆和酒馆都会成为宣传站点。巴士底暴动就是在酒馆和咖啡馆里酝酿策划的。这些细节的巴黎场景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环境和气氛,也向我们提供了法国和法国人民彼时彼地的具有史料意义的生活侧面。
断头台、断头铡、绞刑架等等,都与刽子手的职业分不开,这些都不过是刽子手的工具而已。刽子手作为所谓的“最高司法执行人”,不过是按照司法当局的命令去执行罢了。而他们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却又十分矛盾。他们一方面接受最高司法当局,甚至是国王的亲自任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从事的应该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了,因此享受某些特权;另一方面,却又承担着世人的骂名而几乎与贱民为伍。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随着他们的那些行刑工具的演变,我们看到了各个时代人们对于死刑的某种心理需求的变化:从血腥报复、解恨,到人道主义影响的出现(减轻犯人的痛苦,缩短痛苦的时间等),再到死刑的废除,这也许是人性进化过程中所共有的普遍规律吧。
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对于全世界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自大革命以后,法国先后经历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年9月22日 - 1804年10月18日)、督政府(1799年12月13日 - 1804年5月18日)、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年5月18日 - 1814年4月6日)、第一次王朝复辟(1814年4月 - 1815年3月)、百日帝国(1815年)、第二次王朝复辟(1815年7月8日 - 1830年8月7日)、七月王朝(1830年8月9日 - 1848年2月24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年2月25日 - 1852年11月7日)、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年12月2日 - 1870年9月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9月4日 - 1940年9月13日)……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近150年的历史当中发生了如此多的政权更替和反复。在法国发生的这段错综复杂的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史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思考。纵观世界革命史, 英国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大革命(1642年)最终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但最重要的是奠定了议会高于国王的决策权,为此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打下了基础。美国的独立战争最终建立了一个全新而独立的宪政国家。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也处死了沙皇,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体制。人类近代历史上发生的这些革命,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都有相似之处,然而其发生在各个国家的前因后果却是不同的。它们都值得后人借鉴和思考。
就法国而言,对于本国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研究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并且不断有新观点出现。或许法国人骨子里面喜欢反思自己的过去,或许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政权更替之后,人们可以静下心来,仔细咀嚼那段既波澜壮阔,又充满血腥和残暴的历史。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革命的过程中往往产生非理性的行为。书中关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由“暴民们”发动的种种“暴行”的描述,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文字狱”,因为“出身不好”或者因为说错话而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包括近代史和现代史,也同样存在过,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恐怖时期”,甚至在革命派内部,人人自危,“为了不被害而害人”,人们为了自保性命,不惜去陷害他人、邻居甚至朋友,致使人性扭曲达到了极致。在国人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的人性不也是曾经被扭曲,而做出了许多令今人看来都难以理解的事情吗?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有些法国人认为,当初如果不砍掉路易十六的人头,结果对法国的历史进程会更好一些,然而历史终究是无法假设的,谁也不能在原时原地重新趟过那历史长河。汲取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不仅是法国人自己应该做的事,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典范性,它也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
桑松几代人虽然身为刽子手,但是,他们并不是毫无良知或者毫无感情的人。他们的心中也会为他们认为被冤屈的死刑犯鸣不平,而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使命,既不可能,也不允许他们做出丝毫宽恕行动,除非让死囚尽快死亡,或者使他(或她)在其他人之前死去也算是一种优待的话。比如夏尔-亨利·桑松,他在一生中砍掉了不下2700颗人头,包括国王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丹东、罗伯斯庇尔等历史名人的头颅,而他本人在“恐怖时期”曾经一度精神失常。作为一个已经看惯了鲜血之人,也忍受不了良心的折磨。这也许就是他的最大不幸之处。而在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断头铡超速运转,革命民众疯狂推崇断头铡,称之为“神圣-断头铡”、“法律之剑”,称执行死刑是“红色弥撒”,是革命仪式的牺牲,人们为之歌,为之舞;断头铡甚至成为一时的时尚,将它做成如儿童玩具、木偶、耳坠、水果刀等各种各样的饰物和生活小工具。更有甚者,有的女人竟堂而皇之地给情夫们准备了“断头铡式的避孕套”,将当时各种各样的乐趣混于其中了。如此种种,该是革命民众的残忍的愚昧和不幸了。
法国大革命的同代人杜塔尔关于断头铡这样写道:
“尽管回忆起遭受磨难的人性使我很痛苦,我还是要说,在政治上,这些处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巨大的影响就是安抚民众对于他们所遭受的灾难的不满,满足他们的复仇之心。失业的商人、面对物价飞涨而工资几乎失去价值的工人,只有在看到比他们更不幸的人的时候,才能勉强接受他们自己的不幸。”
这种冷静的思考,在那个大众普遍疯狂崇拜断头铡的时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思考在当时虽然显得苍白无力,却也反射出正义人性的光辉和伟大。当集体的狂热达到一种失控状态之时,党派之争也逐渐激化,激化到彼此之间相互仇视,达到必置异己者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此时,断头铡的政治角色也发生了象征性的变化:从“政治惩罚的象征”变成了“党派之争的象征”、“党内派性之争的象征”。断头铡先是处死革命的对象,如保王教士、议员、贵族等,后来的主要目标是处死革命队伍中的不同派别如吉伦特派,再后来的主要目标是处死革命党雅各宾派内部的不同势力,最后雅各宾派最高领导、号称“廉洁公”的罗伯斯庇尔处心积虑地处死了本该是自己亲密战友的丹东,而后,则以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推上断头台告终,从而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为拿破伦建立帝国准备了条件。这血淋淋的历史现实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有益教训。难怪胡斯曼·卡米伊(1871-1968,比利时政治家,众议院议长、教育大臣,创立比利时社会党,社会主义国际主席)指出:“过去的革命表现出它是最残忍的制度”。这句话也许缺乏应有的分析,但是它一语中的点明了伴随革命可能发生的一个本质侧面。当我们在本书中读到雅各宾派最高革命领袖如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者,竟因疯狂派性大发作而相互厮杀,最后两人都死于断头铡下,造成革命派自毁,葬送革命成果,令人扼腕叹息。究竟何谓革命,他们孰革命,孰反革命,实堪难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悲剧正是法国人民在找到一种稳定和民主的政治体制之前所付出的血的代价。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悟到“自由、平等、博爱”这法兰西共和国三信条,凝聚了法国人民的政治信仰和智慧,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采取共和国体制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本书透过特殊的历史视角,使我们了解到,这种理念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同时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应是天下革命者,尤其是革命精英们,应读之书、必读之书。兴许,如果世上的革命精英们读懂法国大革命,悟出法国大革命给予后世的启示真谛,就不会发生或少发生伴随革命的那些痛苦、荒诞和疯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