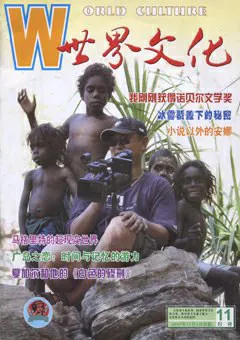广岛之恋:时间与记忆的游历
上世纪50年代末,战后法国开始了一场被称为“新小说”,“新浪潮”(及“左岸派”)电影的艺术实践。文本和电影第一次互为彼此而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浪潮”电影对传统电影的高度自觉与革新,其创造性的试图通过胶片传递出在文学哲学领域里被反复演绎着的现代主义气质,在这个意义上“新浪潮”可算作名副其实的“作家电影”。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新小说派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与“左岸派”导演阿伦雷乃合作的作品《广岛之恋》。
这部电影完成于1959年,阿伦雷乃延续了其对反战题材的关注,然而,与其前两部反战作品《格而尼卡》及《夜与雾》不同,《广岛之恋》试图将对战争的关注缩回到人物心理层面之下,甚至更温情——爱情之下。
在这个故事里,法国女人与日本男人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呼唤对方“拉维尔”及“广岛”——两座因为同一场战争而建立起联系的城市。他们在战后某一日的广岛相识相恋,二十四小时的爱情与碎片般关于战争的记忆互相打断,再互相被唤起。
我们可以将电影中频繁出现的蒙太奇看作两种时间——物理时间及心理时间(或曰思想时间)的彼此作用,考虑到无论是在战争之中还是之后,已经无所谓纯然的物理时间,它在战争及政治语境下被赋予了承载宏大叙事的口吻,时间不再天真无邪的等待着叙事,哪怕一个单纯的数字,比如1949年,对中国人而言它再也不会单纯的只表征物理时间了,我们不妨也将这样的时间称为宏伟时间,
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的,便是这部影片中宏伟时间是如何将心理时间撕裂,强暴的;以及心理时间在宏伟时间中是怎样一再厌弃自身,否定自身的,而呈现这二者的目的,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存在主义的思考纬度。
如上所说,纯然的“物理时间”在这部电影中是无足轻重的,它从未被标示出来。但“宏伟时间”却通过“原子弹”投下的“那一天”,战争结束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显示出其在历史时间流中“硬梆梆”的存在。在这样坚硬的毫无生气的语境下,个人,两个相爱的恋人的闯入,无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召唤出我们的人本意识。而当二人的心理时间通过性爱和爱情关系被放置在一起,更是加剧了爱情(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生命)与战争的矛盾。
影片的开始,原子弹爆炸,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画面随即出现的是男女主人公赤裸拥抱着的肩膀,镜头里只有躯体,没有脸,显然是在提醒,这有可能是任何时间任何两个人的身体,而肩膀上的汗珠,以及两个躯体间的紧搂动作,令人“既感到清新,又图生欲念”。
杜拉斯选择从这样一个场景进入该故事,选择从传递“清新”与“欲念”矛盾交织的心理体验入手,而不是从一个物理场景或一个宏大时间中进入,显然是在提醒我们重视影片中活跃着的记忆及意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主人公在电影中始终是鲜有行动的,他们没有名字,只是“他”和“她”,杜拉斯没有使用任何词汇去描写他们的外貌,面孔或姿态。刻意使其表面身份显得游离,“他”和“她”既可能是战争过后任意一个广岛男人和法国女人,但又因其记忆而永远区别于他人,这种区别是创伤性的,彼此隔离的,是宏大时间之下个人不可复制的一次性即永远完成了的“体验”(而非经验),这在下文进一步得到加强。
他和她的初次对话,是他们慢慢步入记忆的过程。
法国女人不断重复说到“在广岛,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镜头随之指向战争博物馆,并穿插了原子弹毁坏广岛的纪录片,女人的声音“平静,毫无生气,像背诵似的”,不断重复“看到了”,而日本男人自始自终的回答都是——“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无所见”,男人的否定——须注意这句话,“你什么都没看见”并不等同于“广岛什么也没发生”。在通常情况下对他人记忆的否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日本男人在这里的一再反复的否定,恰是在揭示他心里意识中某处印记,这便是战争创伤。否定这处记忆,正是为了强调这一切的发生,以及它永远的发生了,它被放置在过去完成时中。男人还特别否定了这跟复制品、照片、纪念性雕塑都不同——因为发生的这一切具有“一次性”的意义,这一点不同于对其的影音记录,而关于它发生过的最真实的证据是它在人们记忆中的痕迹。
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影片一开始出现的几乎全是否定与怀疑,男人与女人坚定的互相否定(“这一切,全是你胡编乱造”),女人对广岛游客的否定(他们“仅仅是哭泣而已”),对战争纪念性建筑的否定(“尽管人们有时会对它们一笑了之”),这向我们揭示了心理时间是如何将个人记忆隔绝成为一个封闭体的,这个自足的记忆空间的存在,正是起因于宏大时间解放了心理时间,恰是因为心灵看到的这一切使其受到足够的震憾,以致其无法再正常的去思维,此时心理时间便与物理时间脱钩,而脱钩后的心理时间只能自我分化,于是便在体系内自我解释自我否定。
由此出发,在回忆完一切以后,法国女人接下去说:“我记忆力很好,但我会遗忘一切”,“和你一样,我忘记了”,然而她却又继续沉入其中想象着“地面温度将高达一万度”“整个城市将被从地面揭起”“四名大学生情同手足,一起在等待传奇式的死亡”,这便是心理时间在自身体系内的循环,这远非自足闲适的过程,而是充满矛盾的,每当心理时间被拉回为过去时时,记忆便条件反射般的拼命挣脱,而挣脱的结果是心理时间自身也被撕扯成越发尖利的碎片。
法国女人关于战后广岛的记忆,随即被另一段1943年内韦尔的记忆横加插入,宏大时间的线形链条彻底被打乱,心理时间不仅将记忆变为共时性的平行的存在,记忆与记忆之间还互相提示彼此串联。当男人熟睡时,法国女人“注视这个日本男人的双手时,猛然间,一个年轻男人的躯体浮现在他躺着的位置上,取代了他”,心理时间与宏大时间的接口处是如此残忍——由初恋情人的尸体而进入,而记忆中细节处更是用了放大镜在观看,“这只手因为临终的痉挛而抖动”。
从这时的对话开始,法国女人第二次提及她的家乡。
对话呈现于文本的样子便是任由记忆碎片在心理中游走的过程。记忆的碎片是流动的,仿佛某种带有生命性的东西,它在心理时间中自我持存,即使偶尔的沉寂也不过是暂时的休眠,在内韦尔发生的一切并非通过法国女人完整精确的叙述来展现,通过多处拼接我们得知:她亲眼目睹初恋情人——一个德国士兵,被她的法国同胞杀死,而她自己则因为跟“国家的敌人”恋爱,被剃了头囚禁在地下室,受尽歧视。
关于心理时间与记忆的讨论,我不再用之后的文本再加证明,因为我们可以从主人公4次交谈中找到某种类似于格式塔心理的对应结构。关于整部电影,我最后想说的是,与其说杜拉斯和阿伦雷乃是在讲述一个法国女人与两个男人间的爱情,不如说是讲述其记忆在心理时间中的一场游历,正如上文所示,这样的游历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却是高度哲学性的,他试图唤起某种对真实的洞察,记忆的引入,是想揭示一种更纯粹真实的心理情感。这便回到了关于他真正想说的东西上:关于生命,爱情,战争,时间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