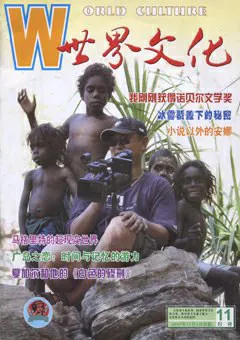小说以外的安娜
上个世纪50年代,国外某组织曾就“你最喜爱的小说”做过一次世界性的调查,结果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名列榜首。从那时起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小说仍然是读者最喜爱的文学作品之一。之所以如此,除安娜这个形象生动、感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娜作为文学形象,具有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安娜现象”在小说以外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时而可见的。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富于传奇经历的克吕德内夫人,就正是这样一位现实生活中的安娜。
嫁给一个卡列宁式的丈夫
克吕德内夫人原名朱丽·巴尔布,1764年出生于当时的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的里沃尼亚省的里加,一个有着古老德俄贵族世系的家庭。父亲是哲学家和共济会会员,热爱艺术,是文学事业的赞助者,母亲是虔诚的路德派教徒。
朱丽18岁时,和比她大15岁并曾两次结婚又都离婚的俄国外交官克吕德内男爵结了婚。男爵是个有头脑、有教养的高尚的人,性格沉静,也不乏热情,但却是一个卡列宁式的人物,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与其说是爱人,倒不如说是父亲。正像奥布朗斯基对妹妹安娜所说的那样:“你嫁给一个比你大20岁的人,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也不可能有爱情。这是一个错误。”朱丽结婚前曾跟著名的巴黎芭蕾舞师维斯特里学过舞蹈,所以,这位随外交官进入18世纪最出色的欧洲上流社会的夫人的主要兴趣和活动就是业余演出披巾舞。德国著名作家斯塔尔夫人曾在她的小说《黛尔芬》中以克吕德内夫人为原型描绘了黛尔芬跳披巾舞的形象:“优雅和美丽从未对一大批人产生过这样突出的影响……她开始轻快地舞蹈,把一块印度披巾围在自己身上,显出她身体的轮廓,她垂着长发的头往后仰,使自己构成一幅十分媚人的画面。”
一年以后,这位夫人跟随担任威尼斯大使的丈夫来到这个当时最放荡的城市,过上了眼光缭乱的生活,并且成了她丈夫的私人秘书亚历山大·斯塔克杰夫暗恋的对象。这位秘书陪同他心中的情人到处游逛,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之后,用一封信向自己的上司坦白了自己的爱情,而这位卡列宁却不知出于什么想法,把信拿给妻子看了。单恋的男人离开了,但他那炽热的感情在这位美丽的少妇心中唤醒了强烈的爱和被爱的愿望。她想使她的丈夫成为她热烈的爱情的对象,可是,这位卡列宁式的父亲般的丈夫,对她热烈的感情只想加以抑制。这就把她推向家庭以外。她在所有的舞会上任性地、毫无顾忌地卖弄风情。频繁的舞会和披巾舞的演出把她的身体累垮了,她的神经变得衰弱,肺部受到感染。这时他们在哥本哈根。她的丈夫让她到南方地中海岸上安静温暖的地方去度过1789年的冬天。
渥伦斯基们
而她却急匆匆地赶到了巴黎。在这个著名的文化大都市,她结识了一些大作家,产生了阅读的兴趣,并遭遇了她的“渥伦斯基”——一个青年军官德·弗雷热维尔。经过一番斗争,她依从了他,并听从他的劝诱,违反她丈夫的初衷,在巴黎一连度过了两个冬天。
路易十六逃跑未遂后,巴黎不再是克吕德内夫人安全居住的地方,她让“渥伦斯基”假份男仆,俩人逃离巴黎,来到汉堡,仍以主仆身份同居,甚至在她丈夫到汉堡接她回哥本哈根时,她仍不肯和她心爱的仆人“渥伦斯基”分手。夫妻俩大吵了一架,丈夫提出离婚。这正是托尔斯泰的安娜百般欲求而不可得的,可这位“安娜”却不顾女人的自尊,竟然扑倒在丈夫的脚下,请求宽恕。她的父亲般的卡列宁丈夫,作为一个“有修养的、高尚的”人,宽恕了她。但她却并未遵守自己的诺言,而是继续在欧洲各地游逛,过了10年18世纪末那种放荡的贵妇人的生活。
在这10年中,她参加了一个又一个舞会和宴会,在业余演出中跳斯塔尔夫人描述的那种披巾舞,并频繁地更换她的“渥伦斯基”。
1800—1801年,她以俄国大使夫人的身份住在她丈夫任职的柏林。她的不守时和古怪的脾气,使她在威廉三世这个处事井井有条的宫庭里并不特别受欢迎。虽然她那单纯质朴的态度10年前曾使人无法抗拒,她那表情丰富的面容和娴雅的风度向来招人喜爱,但她知道,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美人,何况她的面容和肤色也不像年轻时那样鲜嫩了。因此,她就设法靠大胆的打扮来引人注目,靠打份得异常妖冶,甚至不穿什么来造成轰动。在这期间,她为了一次新的爱情再一次离开了她的丈夫。
1801年秋,她对斯塔尔夫人作了长时间的访问,产生了当女作家的愿望。不久,她在巴黎听到了克吕德内死亡的消息。她非常震惊,心中充满悲痛和悔恨,闭门不出,也不接待任何人。她一直想再次回到他跟前,减轻多年来给他造成的伤害,报答他始终给予的宽宏大量。这样的机会永远失去了。
但她不可能长期过那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她开始写小说,并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宣传策略,使她的长篇小说《瓦勒丽》于1803年底出版,大获成功。
皈依宗教
1805年,由于几个偶然事件的启示和某种内在的倾向,克吕德内夫人突然皈依宗教,成了热忱的基督徒。她过去的整个生活在此时满怀宗教热情的她看来,都是错误的。从这时起,她将年轻时在爱情上表现的那种热情都倾注到礼拜和行善上了。她成了基督教各种谦卑美德的典型。为了帮助受苦的人,她爬到最脏的阁楼上去。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女仆因为主人让她出来扫地而在街头哭泣。这位高贵的夫人就拿过扫帚,自己扫起人行道来。一位宗教界的领导人,在对她进行过仔细观察后写道:“她对一切人的痛苦和需要表现了最深切、最纯正、最积极、最无私、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同情。”
她甚至要对沙皇施加影响。1815年6月4日晚上,她不顾副官的阻拦,不经通报强行来到沙皇亚历山大面前,他们俩人在小房间里呆了3个钟头。当她离开时,亚历山大眼中充满泪水,心头十分激动。不久,他就完全处于她的影响之下了。他们俩人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圣经》,讨论神学问题。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亚历山大立即出发前往巴黎,并约好克吕德内夫人随后跟去。9月初,在香槟省的美德营举行15万俄军大检阅。一清早,沙皇就派自己的马车去接她,让她像一个上天派来把他的军队引向胜利的使者那样参加检阅。对于当时的情形,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圣伯夫曾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记录如下:“她光着头,或是戴上她那经常挂在手臂上的小草帽;她那仍然很漂亮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肩上,前额有一绺卷发搭在额上。她穿着一件朴素的黑袍(其式样和她的体态给人以雅致的感觉),腰间系着一根简单的带子。她就这样打扮,在黎明时分来到美德营,在祈祷时站在吃惊的军队面前。”
几天以后,克吕德内夫人修改了由沙皇亚历山大起草的俄、普、奥三国国王协议草稿,并给这个协议起了个名字:神圣同盟。
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反动的同盟。
走向底层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宗教信仰变得更加真诚和狂热,并努力把这种信仰变成行动。她心中唯一的愿望和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帮助穷人和病人。她给穷人讲道,创建教会,宣告天国即将来临。可是她没想到,过去那些把她当作宫廷贵妇笑脸相待的王公贵族、权威人士和所有的大人物,看到她走向底层,面向人民群众,就本能地把她当作敌人。有一次她从瑞士的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讲道传教,几乎是进行了一种疯狂的宗教胜利游行;之后她再次进入这个国家时,却被从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中驱逐出来。巴登发生灾荒时,她慷慨大方地进行慈善救助活动,宪兵把她的房子围住,驱散了向她谋求帮助的人。她设法通过阿尔萨斯进入法国,被警察押送到俄国边境,在那里由威腾堡的警察交给巴伐利亚的警察,又由巴伐利亚的警察交给萨克逊的警察,最后将她交给了她本国当局。从此她永远失掉了沙皇的宠幸。因为她所理解的基督教只能引起统治当局的反感。在她散发的宗教杂志和小册子中,她谈到了社会上的坏事,穷人们的说不完的痛苦和统治者对他们的不公正的压迫,这些言论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而她本人则被视为革命者。她甚至还对希腊独立战争表示热烈的同情,宣称作为神圣同盟的发起人亚历山大皇帝有责任站在反对土耳其圣战的前列。在这个问题上,她虽然不能和拜伦相比,可是考虑到她个人的经历,还可说是勇气可嘉的。
被沙皇抛弃之后,克吕德内夫人离开了彼得堡,开始过一个真诚的传教士的自我惩罚的苦修生活。她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尽一切可能减轻别人的痛苦。1824年,当她远道到克里米亚传道时,她永远地离开了那些穷苦的人们。
克吕德内夫人曾在谈到日内瓦的贵妇人时说:“她们既没有品德上招人喜爱之处,也没有罪恶上的迷人之处。”后面这句话用在她本人身上倒也合适:她那些放荡的年月,那些频繁更换情人的年月,从她身上放射的迷人光彩,无疑是含有罪恶的。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是爱情的精神守望者。她以生命和激情,以她对爱情的真诚而不可动摇的信念,在现实生活中寻求爱情的神圣和纯洁。她是爱的天使。而克吕德内夫人却只能说是爱的撒旦。可是,当她晚年为救援穷苦人而受苦,到处被统治者所驱逐,并因此而死时,我们在她身上也看到了道德的闪光。不管怎么说,此时她是真诚的,她值得我们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