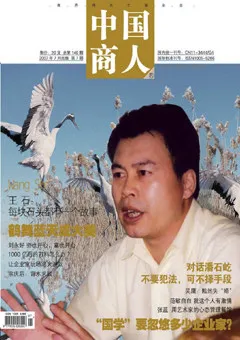长远生财茂 发展利中祥

那时,长发祥的后面是作坊,如顾客需要在他们这里裁衣,后堂的裁缝脖子上挂着根皮尺,会声音宏亮地跑出来招呼:老祖宗……
说老西安,不能没有“长发祥”。
西安的“老字号”,远没有北京、天津那么多,也没有湖广和沪杭的“老字号”那么宏大气派。西安有着“周秦汉唐”“十三朝古都”等诸多的辉煌标志和灿烂符号,但就是缺乏与其辉煌和灿烂同步同趋、同题同意的历史遗存。西安是一个近乎“传说”的城市。
透过古典的门板
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我想只要它进入了“传说”,就必然散放出某种气息。这种气息往往具有巫婆“放蛊”的作用,还有说书匠摇唇鼓舌“话说”出的境界,另外就是历代帝王和圣贤根据自家需要,反复添加和删改的一部部“史鉴”、“史稿”。如今的西安,没有太多“老字号”,也没有足够古典的“老派”经营模式和营销理念。我曾无数次地做过试验:倘若从今天的《西安地图》上抹去大雁塔和四角城楼,那么这座“千年帝都”立马就会混同于中国的随便哪一座城市。不论是海外游客还是国内的学者,他们倾注于西安的那种热衷,只是在读了许多和听了许多关于西安的历史故事之后,对自己从行为到精神的某种“放蛊”;在“放蛊”中陶然于唐风汉韵,陶醉于宫殿宫廷。历史在西安是“空在”的破碎,完全依靠游客和研究者在心里弥补和缝合。
我曾经无数地做过另一个试验:站在西安城南的乐游原上,俯瞰西安,一堆由钢筋和水泥堆砌成的仿清仿明建构,一堆几近破败的砖头和瓦片结构出“古典”。我在心里暗骂:这哪儿是典籍和传说里的西安古都,简直就是一座“砖瓦窑”。
这样,我在寻访老西安的时候,尤其重视依稀尚存的几家“老字号”的研究。我想:它们是西安历史的真实存在,是历史的实在“遗存”;它们从观念和形态、经营和规模等诸多方面,提供给我的是进入实在的“老西安”的古典形式的最好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
我这里打开“长发祥”,像剥开桔子那样绽放出它的香气和令人馋涎的桔肉和桔汁。

从 “皇商”到“老字号”
在西安,如今依然有“大尺子的长发祥”、“仁义忠厚的长发祥”等等传说。在这些传说里,长发祥一次次地复活,并且在复活当中加深人们对故旧生活的思念。故旧生活,往往透过时间传达给我们一种温存、温润与温暖,传达给我们一种生活的自然亮度、生存的本真姿态和生意的确切含意。
长发祥是“长远生财茂,发展利中祥”的缩意。至于这两句老诗的来例,今无考。但是这两句老诗却实在是概括了“老派陕商”的商业经营特色,涵盖了“老派陕商”那种“毛毛雨也能湿透衣裳”的持之一恒、不求速达的商业效益追求。长发祥,一个十足工稳的以经营呢绒绸缎、布匹绫罗的老字号的名称;长发祥,一个时代的商业风度、营销理念与商德商誉形象浓缩。
长发祥创建于光绪28年(公元1902年),原址在河南开封,开办者是河南朱仙镇的一个落榜秀才,名叫冯康瞿。关于冯康瞿我在朱仙镇、开封以及西安的各史志、史料馆里,没有找到太多相关的资料。但是有一笔记载却把冯康瞿与“长发祥”紧紧地连系在一起,并且赋于冯瞿康与长发祥某种“皇商”的意味。
冯康瞿是清王朝内阁大臣徐世昌的大表兄。进入民国,徐世昌出任过为期短暂的“民国代总统”,是个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人物。但是,徐世昌却是一个地道的民族主义者,有浓郁的乡土情结,倡导民族工业发展、呼吁“废除科考”,推行“量材录用”。在康、梁“变法”时期,徐世昌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在徐世昌出任内阁大臣其间,他的大表兄冯康瞿在京城应试,这时冯康瞿41岁,徐世昌39岁。冯康瞿在数度“榜上无名”之后,心情郁闷地与表弟商量,打算回到家乡,过“归隐林泉”的生活,打算在家乡“寻田问舍”,报效桑梓。这时一惯思想激进的徐世昌苦口相劝,劝冯康瞿回家乡振兴民族经济,“背靠朝廷”,为家乡父老做“衣被天下”的生意。
这样,落榜秀才冯康瞿回到开封,在那里开办了以经营呢绒绸缎、布匹桑麻为主的“长发斋”,网络和结识了开封城里的各路神仙,以充沛的货源和繁多的花色品种,确立了它与上流社会与大众百姓的生活联系。开业时间大约在光绪29年冬天,斋号的匾额出自徐世昌手笔。在清末及民国的种种传说里,“长发斋”的最初资本都是由徐世昌“捐赠”的。冯康瞿本是一介书生,是“不善经营、无能理财”的一介书生,这样冯康瞿回到家乡朱仙镇,请出远房表弟丁竹青出任掌柜。
丁竹青是“长发斋”的第一任掌柜。丁竹青饱读诗书,有着远通近控、熟稔国政的诸多特点,他赋予创业阶段的“长发斋”,一种“乡帮”特点:“长发斋”开业之际,满堂的领东、相公及杂役,均为来自朱仙镇的本门族兄和远房表亲。事实证明,这种乡帮化、家族化的管理方法,大力地推动了“长发斋”的发展,使其之后的“分号”联销联营模式成为可能,为日后的飙升与发展奠定了令人信服的基础。进入民国,尤其是在徐世昌出任“民国代总统”的短暂时期,长发斋一跃而起,先后在河南郑州开设了“长发祥”、“义丰永”、“祥记”等三家字号。这时,丁竹青向股东冯康瞿提出告老还乡,踏上了寂寞冷清的回乡土路。这种“全身而退”赋于长发祥大旗之下的商业经营,一种接力与薪火相传的意味。但是,丁竹青在离任之前,也给各字号里的领东和二掌柜留下了“无才不养金玉”的用人用贤规矩。这样,“笤帚把出身”(也就是学徒出身)的第二任掌柜来式如开始领东长发祥,使长发祥再一次进入了腾飞阶段。

来式如为人智慧,精通商略,为长发祥制订了完备的经营方法,并使其方法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在来式如领东期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数次的衰落和迂回。
在1934年陇海铁路通抵西安之前,历任陕西省主席都倾心地方经济发展,提倡“招徕”、鼓荡“陕商”走出去,启发“陕帮”开胸怀。1928年,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先生就曾邀请过开封长发祥来陕经营。1933年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先生在火车即将通达西安的时候,再次面向全国,发出“招徕”吁请。可以说,长发祥是在积极地响应杨虎城先生的“招徕”政策的基础上,前来陕西寻找机会的。至于当时杨虎城对各路商帮的承诺,那是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事情,是那个时代陕西各级长官对“振兴陕西,扶助农桑”的拳拳之举。冯玉祥主陕期间,也发表过近似于捶胸蹲足、捶头打脑似的“万民讲话”。对陕商和陕帮的闭关自守、墨守成规等一系列陋习,提出了十分恳切的批评。
1940年,西安长发祥已拥有“十万大洋“的积累,并先后挤垮了“老九章”“大纶”等同行同业,以其霸主姿态,领跑西安绸缎及布匹销售行业。
1934年冬天,河南长发祥落定在西安竹笆市,开始了临街商卖、惠顾城乡的商品经营活动。原来河南的几家长发祥旗下的字号,后来均在日寇铁蹄之下,毁于战火。1944年因西安商业经营中心东移,长发祥遂迁东大街现址。长发祥和它满堂的河南籍商人,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之后,陪着笑脸,倾情倾心地和陕商交流与融通,传下一段段佳话。
1953年,长发祥领东来式如,积极响应社会主义对工商业者的改造,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如今,长发祥是响名叮当的“老字号”。但“老字号”又是什么呢?是一块闪闪放光的金字匾额吗?是声名显赫的美声美誉吗?
都不是。“老字号”是一群人的沧桑苍茫的人生故事,是一家企业沉浮与挣扎的历史故实。
“日月滚金球”
1934冬天,一帮土衣土貌的河南籍商人,站在了西安城楼的下面。他们肯定没有想过:这里是他们最后的归宿,这里是他们的子子孙孙起根发苗的地方。那是一个民族面临考验的特殊年头,军阀混战,经济衰微,国政废弛;街市上过往着什百为群的难民,过往着无以数计的伤兵兵痞、土匪强人。不难想见,长发祥领东来式如拜会各路“神仙”的情境:那时的西安城,有着太多的“山头”,官商一家、官匪一家、官绅一家,城虽不大,但城里的每个角落都潜藏着足以使初来乍到的长发祥“闭门”与“关张”的这样那样的黑势力、恶势力。长发祥是如何面对陕帮陕商,是如何扎根百姓,是如何确立了在西安城的理想位置呢?
长发祥首先选择的是忠厚忠诚的对待陕帮的态度,其次选择了“顾客就是财神”的经营风度。另外,长发祥十分重视领东、掌柜以及相公的业务能力,培养出了一批“商卖场上”和“财货行当”的经营高手和理财高手。
长发祥的店堂经营模式,不同于老派陕商在店堂里敬供行当祖师和“关二爷”(关公),长发祥在本应当是神龛的店堂冲门位置,长年设置着八仙桌,茶几茶椅、炮台烟、龙井茶,任城乡顾客随便享用。八仙桌的上面是品蓝缎子上绣的五个斗大的金字:日月滚金球。透着和谐与融洽,透着俚俗与亲切。
在老长发祥的门前,永远都袖手站着捧着笑脸、穿着棉袍的二掌柜。长发祥二掌柜的笑脸,深深地扎根在每个老西安人的心里,成为长发祥的特色符号,使老西安人久久难以忘怀。这个二掌柜不只是简单地迎来送往,他站在店门前,和往来的四乡骡马大车打招呼,和车上坐着的大姑娘、小媳妇打趣,给骑着驴来买嫁妆的新娘子拴驴,搀扶城乡的那些小脚老太太,给坐在八仙桌边的官绅富绅点烟锅,另外,二掌柜甚至还给那些乡下进城的大户人家的“老祖宗”捶背。可以说,一个干净漂亮的二掌柜,洒脱得就像一阵春风,制造出了“宾至如归”的情境,然后才是掌柜的双手低垂至膝的“请安”,相公目不斜视的“捧茶”和麻溜的一路小跑的几个圆头圆脸、睁目豁眼的相公娃的“捧样”。那时的长发祥,顾客不用站在柜台前选货,只需要往八仙桌边一坐,掌柜和相公娃就基本清楚了顾客的要求。在老长发祥,每个相公娃必须经过三年严格的学徒,学徒期间不能“顶生意”,只能扫地、抹案、捶背、端茶,其余时间才能跟着师傅学习“三准”基本功。所谓三准就是:眼准、手准、心准。在漫长的几十年经营过程上,长发祥没有发生过一例把绸缎撕“毛边”的,更没有过一例“缺尺短寸”的事故。相反,长发祥本着“舍小求大”的经营理念,长期实施“满尺长寸”的营销方式,也就是你买每一尺绸缎,我舍给你一寸。所以,长发祥在西安有着“大寸子的长发祥”商业美誉。
在长发祥,买卖成交之后,相公捧着账单收款,那账单是桃红色的,透着喜气,上面印着“吉祥富贵”,“万事遂意”等吉祥话语。那时长发祥的后面是作坊,如顾客需要在他们这里裁衣,后堂的裁缝脖子上挂着根皮尺,会声音宏亮地跑出来招呼:老祖宗,可把我想日踏了!(西安土话:你把我想死了的意思)然后才请安,躬身量体,等等。
另外,长发祥的“礼票”也是它商业推广、扩大经营的重要手段。所谓“礼票”,就是凡有馈赠亲友礼品者,可先在商店内卖好“礼票”,让亲友持票选样拿货。那时西安的各行各业,都有在年关上、喜庆时给朋友和员工散发长发祥“礼票”的讲究。礼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长发祥商德商誉的传播方式和重要标志。
可以说,长发祥的经营思想里体现着一个重要的传统情结,这就是舍得。
可以说,长发祥生动地理解了“长”对商业经营的作用,没有“短、平、快”的对待商业活动,没有急功近利的把商业活动处理成“一次性消费”。
长发祥奉行对顾客:一要敬好,二要周全,三要诚信无欺。所以,从1934年到1953年,长发祥始终是西安人民生活的朋友和顾问,深得城乡人民的热爱。
从“无才不养金玉”到“柜考”
从商是一种高级的人生经验,它需要的元素远比从政从文、从医从工要复杂,而且复杂得多。一个优秀的商人,他的大脑要像化学实验室的烧杯:耐酸耐碱耐火烧。他的手脚要像杂技演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的表情要像政客一样从容、要像演员一样妩媚、要像圣人一样庄严。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孙悟空,不仅要有七十二变的能力,重要的是他赋予商业活动,某种德与品、智与灵,几近赏心悦目的神仙境地。
来式如这个由“相公娃”、二掌柜一路成长起来的“领东”,在老掌柜丁竹青“无才不养金玉”的价值观作用之下,荣登领东宝座,并继承这个价值观念,积极推行对相公的“柜考”制度,确保了长发祥的服务质量和员工素质。
店东认为,商卖要有成效,员工素质是首要的决定因素。所谓“无才不养金玉”,也就是没有有本领、有德性的店员,商卖就得不到大的发展。在长发祥当三年学徒期间,不能上柜“顶生意”;学徒第一年,干杂活,抹案扫地,学规矩(放屁都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学徒第二年,开始学卷布、折布、摆货、捆扎、认货;学徒第三年,学写字、珠算、绸缎知识、应酬、行当秘语和待客语言。三年学徒期满,要经过严格的“柜考”,柜考最残酷的是要“闯四关”:一、让学徒蒙上眼睛,用手感来鉴别毛、丝、棉、麻、葛、绉等产品及产地;二、不论顾客胖瘦高矮,要一口报准看体算料的数量;3、根据布料的幅面和颜色及尺寸,能随意自如地报价、折垒和捆扎;4、学徒期满,必须能够算出所售布料的利润,而且必须做到“一口清”。在老长发祥,商品标签正面是销售价,背面用密码写得有成本价,密码用“长远生财茂,日月滚金球”组成,每个字代表一个数码。若能闯过四关,学徒才有“顶生意”的资格。老长发祥十分重视品行、礼仪、廉耻,以“寡廉鲜耻”与“枉口嚼舌”为相公人生的大忌。老长发祥的相公娃,一律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赌博、不准和不三不四的男女来往,甚至上柜台时身上都不允许揣钱。老长发祥还有一条铁律:亲友和熟人来买布,要让其他相公接待。长发祥的相公都很懂规矩,模样也都周正,很得城里城外太太、姨太、小姐、丫环的喜爱。那时,许多太太小姐,不买布也经常到长发祥逛一逛,转一转,忽闪着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店里的一个个憨头瓷脑的相公娃,在内心里纵情畅美。
另外,长发祥在经营理财方面,也有自己的道行,它的商品几乎无一不是苏、杭、川、广厂家的最新货色。1944年,长发祥在全国各地驻有16个“庄客“,所谓“庄客”其实就是采购员。这些“庄客”都是相公出身,有着超人的对绸缎及布匹布料的认识与判断,并能够就绸缎与布匹的颜色与花样,做出流行与否的准确判断。长发祥一惯坚持“源头进货”的原则,从不在“批头庄”(转手转卖及批发市场)进货,确保了商品的品质,同时降低了成本。
另外,长发祥在老西安是尤其重视品牌宣传的企业。每到年关,长发祥大肆宣传,雇来鼓乐队,吹吹打打、沿街号叫,并向路人馈赠手帕、香胰子、雪花膏,以此扩大影响、以广招徕。来式如领东有句商业名言:货不压柜利自生,钱不存柜利自来。为此,长发祥在30年代和40年代,经常举行“拍卖活动”,推销积压货。从利益最大化考虑,长发祥在40年代抗战期间物价暴跌、生意萧条,许多商家濒于破产之际,别出心裁地投资于“行商”(游商),采取“赊销”给无业“货郎”的方法,解决了无数逃难流民的生活,并积极推动了长发祥在“乱世年代”的稳步发展。昨天还有老人给我说:1947年,西安街上的货郎比现在街上卖《华商报》的报童还多,卖得都是长发祥的货色。
现在的长发祥是位居闹市中心的一幢九层高的商业大厦。名字还叫长发祥,还经营绸缎缎和布匹,但已混同于金碧辉煌和富丽堂皇的许多“商厦”和“购物广场”,找不到它历史的遗韵和魅人的绝响。
想起长发祥,我的耳边立马回荡起了那远逝的市声和市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