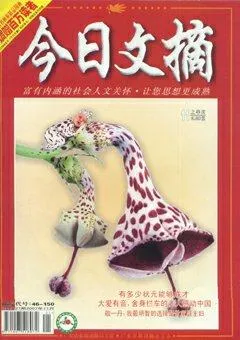敬一丹:我最明智的选择是做家庭主妇
“梓木需要的,不是一个指点江山的女主持人,他需要的,是一个嘘寒问暖,出门前给他整整着装、回家后给他一双拖鞋的太太———而我,就是留恋这种最古老职业的女人……”
敬一丹在《焦点访谈》正做得如日中天的时候,忽然就淡出了荧屏,一晃多年都没有回归。
2007年春节过后,有记者采访敬一丹,委婉地问及她的工作状况时,敬一丹在电话那边笑了:“我现在有两份工作,一份是央视的播音指导,还有一份,是一种最古老的职业……”
■人最怕的是可以把自己的未来卜得一清二楚
我是哈尔滨人,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一直想读研究生,但因为英语太差,考了两年都没考上。
第三年去考试的时候,在考场认识了梓木,他坐在我后排。考试结束后,他对我说:“我想认识你做个朋友,可以吗?”
作为“考友”,我们就这么开始了接触。这次,我们都考上了,而且都是北京的院校。我进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梓木进了清华大学经济系。
我们在北京都举目无亲,于是很自然地走得很近,也都觉得对方踏实、靠得住。那时我们都是年过而立的人了,面对婚姻更加理智和清醒,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都觉得对方是个适合结婚的好人选。开学两个月后,我们领取了结婚证。
婚后的生活很清贫。我们都是自费进修,学费生活费就够多的,再加上都没什么积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于是决定半工半读去挣钱。我去北京广播电台兼职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深夜栏目,他打着清华研究生的招牌去给这个厂那个公司做员工培训。
我一直很怀念当初那段赚小钱的岁月。我主持的夜间节目时段是每晚12点到2点,每天半夜从台里出来,总能看见梓木推着那辆10块钱淘来的破自行车在电台门口等我,从复兴门到租住的北三环要40来分钟,我坐在后座上,梓木弯着腰蹬车,呼吸粗重而有力。虽然很穷,但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真实,用自己的双手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为了下个月的房租水电一起忙活,齐心协力,少了谁都不行。
在北京读了3年书,过了3年婚姻生活,也做了3年“外来劳工”。我毕业的时候正好央视经济部来招人,我于是进了央视,梓木则进了国家经贸办。
因为担任《焦点访谈》主持人,我成了“名嘴”。梓木也算得上是一帆风顺,41岁就当上了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我们还有了活泼健康的女儿王尔晴。
生下女儿不到4个月,因为要去云南采访,我不得不给女儿断了奶。产假结束后,外出采访更频繁了,我经常不在家,就算人在北京,也会因为录节目做后期忙得没个准点。对于丈夫女儿,我觉得格外亏欠,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的收入比梓木高。我把工资卡交给梓木,当做是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
梓木于是除了”做官”,也做起了家庭妇男,他是那种不喜欢外人介入自己生活的人,所以我们没有请保姆,几乎所有的家务事都是梓木承担。
女主外、男主内,虽然不大传统,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我们的婚姻就这么慢慢往前走着。
一次我们在家聊天,互相想象对方20年后的情况:我会因为《焦点访谈》事业稳固,最终在退休前谋得一个央视的领导待遇,逢年过节去领点木耳、黄花菜、购物券之类的过节物资。梓木会四平八稳地升迁,说不定会慢慢熬到一个高级干部的级别。
人最怕的不是前途未卜,而是可以把自己的未来卜得一清二楚。这样在别人看来安宁稳定的未来,却不是我俩需要的。
谈得更深后,我们都发觉,为对方做的很多事情,自己以为是牺牲、是奉献,竟然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我觉得我工作是在减轻梓木的经济压力,但梓木的理想是办自己的实业,成为这个家当之无愧的经济柱石;对于我,他只希望我能做好这个家的大后方,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投身事业,而并不希望我来赚钱养家糊口。
我想,这样的误会绝不仅仅只存在于我们这一个家庭,很多夫妻,一起过了一辈子,也没搞懂对方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还好,为时尚早,还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我从最初的勉强接受,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新身份
我支持梓木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于是他辞职下海,经过一年的奔波,他组建了由63家企业做股东的华泰保险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梓木的新工作很忙,既然当初答应了支持他,我觉得我也该有更多的行动。于是,我开始慢慢淡出《焦点访谈》。露面的频率从一天一次到几天一次到半月一次到一月一次,尽可能少地接选题跑线索忙节目,把越来越多的重心往家庭转移。
在家的生活非常单纯。早上7点起床,做一顿简单营养的早餐,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稀里哗啦吃完。先帮梓木正正领带拉拉西装,叮嘱一声“小心开车”,送他出门。然后给女儿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牵着她的小手送她去学校。
回家的路上绕到菜场买点新鲜的蔬菜水果肉食,回到家,换一身宽松的家居服开始做卫生。把要洗的衣服放进洗衣机,需要干洗的送到干洗店,地板先吸尘,再用半干的拖把拖一次,再用干拖把拖一次。如果地板光泽暗淡,就再打上一遍水晶蜡。
梓木告诉我,布艺家具用吸尘器、实木家具用纯棉抹布、真皮沙发用麂皮搽巾……我于是很快就学会了这些快速又省力的技巧。
中午给自己做一顿搭配均衡的简单午餐。拿一本喜欢的书去阳台晒着太阳翻翻,倦了,就小睡一会。睡醒了,把干了的衣服收下来叠好,需熨烫的烫一下,袜子配对,放进各人的衣柜和抽屉。然后去学校接女儿回家,一路听她叽叽喳喳讲述一天的校园生活,聒噪却真实。
回到家,女儿看着电视,我在厨房开始做每天最重要的晚饭。荤菜、素菜、汤羹、主食、餐后水果。搭配得停停当当,最后一道菜端上餐桌的时候,也正是梓木回家的点儿。喂女儿一口肉,给梓木夹一筷子菜。吃饭不仅是生存需要,餐桌上除了饭菜,还有很多让人觉得快乐和温暖的“佐料”。
吃完饭,梓木跟女儿说说话,我收拾好碗筷,一家人一起去小区散步,一边信马由缰地讲些可有可无的闲话。散完步回家,这才各自为政:女儿去学习,梓木去准备次日的工作,我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
每个女人骨子里面其实都是很依恋这样的家居生活的。我从最初的勉强接受,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新身份,喜欢上了这种新”职业”,我的很多观念,也因此发生了很奇妙的变化……
■我觉得20年来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回家做家庭主妇
一次去一个跟我以前一样追逐事业的女朋友家,她的家非常整洁,除了墙上有一幅油画,卧室里有张结婚照,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有条不紊一板一眼,每件家具包括每一张纸都很规矩地呆在该呆的地方。她说,只有这样才好打理,不会为打扫过多地浪费时间。
以前,我家也是这样,但现在,我每天花在打扫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因为家里经常发生各种家具错位的现象,在这些错位的家具上还摆着越来越多的各种小玩意,我打扫它们的时候常常会把其中一两件拿在手里把玩一阵,那些和这些玩意有关的回忆就会慢慢浮现出来,时间就这样一分一分地浪费掉了。
家里的墙也越来越乱,一溜儿挂着女儿不同时期不同年龄的照片、奖状、涂鸦,看上去像是一部家庭成长记录史。我常常在一溜照片下驻足,想想好像前不久还只会在地上爬的那个小婴儿,怎么会一阵风似的变成了少女?
朋友家的厨房也很洁净,简直就是一尘不染。而我们家的厨房总有忘记擦掉的油渍及半杯来不及倒掉的牛奶。朋友说她很少在家做饭,平时都是叫外卖,把做饭的时间节约下来干更多有意义的事。但我却觉得为家人做饭本来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洗衣间几乎也没有杂物,朋友说外面的衣服都送到洗衣店去洗,内衣从来不买需要手洗的。为了方便机洗就让全家换下棉质的舒服内衣?放弃那些蕾丝的、手绣的、抽纱的漂亮内衣和全棉睡衣?以前我会觉得这样很正常,但现在,我觉得我做不到。
让我越来越沉迷做家庭主妇的原因,除了享受这种过程的满足外,还有梓木对我与原先越来越不同的改变……
以前我俩都是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在一起安排活动。我也不知道梓木有哪些爱好。如今闲了,我才发现,我嫁的这个男人,除了会在家做家务,原来还有那么广泛的兴趣——他喜欢各种运动:骑马、滑雪、潜水、冲浪……样样都擅长。以前休息时他也说过带我出去运动,但我却愿意在家好好休息。现在,我终于有了时间精力与他并肩运动了,我发觉他在运动场的身影远比在家矫健,他击球的动作远比拖地潇洒,而他对我的呵护就像当年去电台接我下班一样温柔……
我开始越来越像个家庭主妇,除了“内政”,我还开始考虑“外交”。以前逢年过节,跟他一起回到哈尔滨,总是格外忙碌。亲友家都必须造访到,比上班还忙。
又到了春节,我给梓木出主意。可以将双方的亲人组织成一个“旅游团”,利用假期带领大家度假旅游。我就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负责带大家玩。看着亲人们因为我的安排吃得好睡得香玩得尽兴,大家脸上都是很快乐的笑容,每张照片都是阳光灿烂。我觉得这个职位真的非常有趣。
因为我这个家庭主妇越来越称职,梓木经常对我说委屈我了,感谢我为了他的事业放弃了自己那么有前途的工作和机会。我原本也以为离开主持人岗位会让我觉得很心痛,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告别“事业女性”的身份回归家庭妇女时,我发觉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家庭琐事上,我居然获得了乐趣,并且对这份没有前途的职业情有独钟。
很多朋友开玩笑地说自从梓木创业以后我就越来越不求上进胸无大志了,我承认,但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做主持人,我得到的只是一份不菲的薪水,却会失去作为一个女人应该经历的一些生命过程:亲手带大自己的孩子,听她说第一句话,看她走第一步路,生病时握着她的手;做好一顿饭满意地等丈夫归来,听他对饭菜的赞美和看他狼吞虎咽;在料理家务的时候看家在自己的双手下一点点拭去灰尘绽放光辉;就算躺在床上,也只需要考虑明天该选择怎样的营养搭配……内心轻松,不再有摆脱不掉的压力,祥和而安宁。
转眼跟梓木结婚20年了,我觉得我这20年来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做主持人回家做家庭主妇——梓木需要的不是一个指点江山的女主持人,他需要的,是一个嘘寒问暖、出门前给他正正着装、回家后给他一双拖鞋的太太——而我,就是留恋这种最古老职业的女人…… ■
(伍思阳荐自《读者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