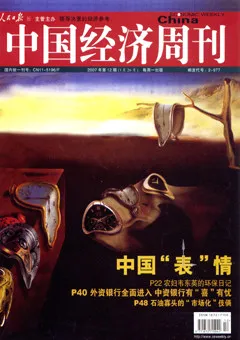韦东英的环保日记
韦东英从未想过,有一天她会和一座化工园较上劲。
而且,这劲还将继续较下去。

刚满39岁的韦东英是杭州市萧山区南阳化工园的一个普通农民,1991年嫁入南阳镇。1年后,她种的地就被镇里用来建了化工园。没了地的韦东英开始帮捕鱼为业的丈夫卖鱼。但是,由于化工园的企业随意排放污水,导致钱塘江的鱼变得越来越少。
地没了,鱼少了,韦东英的埋怨多了。
写日记、拍照、取样、给区环保局打电话、给国家环保总局写信……为了能让化工园搬走,三年多来,只有初中文化的韦东英不断尝试着各种方法。
2007年3月,因为受邀参加央视“小丫跑两会”的节目录制,韦东英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节目现场,她的故事引起了金志国的关注。金志国还表示,将在两会后邀请其他地方的代表一起对南阳化工园的环境问题进行调研,如果的确存在环境问题,他们将会行使人大代表职责对当地政府进行问责。
“代表都说要去了,这次化工园该要搬出去了吧。”韦东英喃喃道。
“傻瓜”日记
韦东英的这场“较劲”始于一家镀锌厂的建立。
工厂建设初期,因为担心将来会有污染,韦东英还曾和其他村民一起去厂里了解情况。在被告之是五金厂,保证没有污染后,韦东英并没有太在意。但没想到在开工第一天,散发出的气味就让韦东英恶心得想吐。
感觉被骗的韦东英很不满,于是又和其他一些村民一起去厂里要求停工。但是,并没有结果。
不久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情让韦东英对整个化工园产生了更大的不满情绪。
2003年年底的一天,韦东英去钱塘江边接丈夫邵关通回家,在途中,他们看见很多污水未经处理就向内河排放。于是,夫妇俩就给萧山区环保局打了举报电话,希望来人管管这里的污染企业,但对方并未受理而是让他们直接找南阳镇。
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情,邵关通记忆犹新。当天夜里12点,本该早已熟睡的韦东英却还在床上埋怨着白天的事。于是邵关通建议妻子,“你要是真憋着难受,就把它写下来吧,或许心里会痛快。”没想到,韦东英真就立刻下床,开始在本子上写道“难道环保局的职责就是有人举报就往别处推吗?”
这是韦东英第一次写日记。此前,只有初中文化的韦东英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开始写日记,而且,是因为环境这样的大问题。
第二天是除夕,她曾经闹“事”的镀锌厂给她送来了2000块钱,希望他们“帮帮忙”,好让厂子能够顺利开工生产。
“如果我拿了这2000元就闷声不想,想必该厂的气味再难闻也不能说。这2000元真有这么重要吗,拿着它去享受那难闻的废气?我决定这钱不能拿。拿了这样的钱会害己害人的。”韦东英在她的第二篇日记里写道。
年刚过,她就把这笔钱退给了镀锌厂。为此,一些村民笑她是傻瓜:“钱都拿到了,还闹那么多事干嘛?”
“这个傻瓜我来做。”面对嘲笑,执拗的韦东英居然较起了劲,“电视上说了,环境是无价的,他们拿钱是要买这个无价的东西,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了。”
除了化工园污染带来的生计问题、气味问题,还有另一个更可怕的阴影正笼罩在韦东英所住的村庄。她发现,村里得癌症的人变的多了,并且各种癌症都有。据韦东英粗略统计,自化工园建成以来,这个只有1500多人的村子里已经有60多人死于癌症。
这一切,更加坚定了韦东英要和化工厂较劲的决心,她希望有一天环保部门能够真正重视这里的污染,并将这里的污染企业都赶出去。
不过,企业还没来得及被赶出去,危险就已开始渐渐袭来。一些“镇上”的人开始劝她不要再闹,不然要让她坐牢。
“反正这里臭死了,在家里气味这么难闻,还不如去住牢房,牢房的气味还要好闻一些。”深受化工厂排污之害的韦东英,这一次决定“拼”了。
农妇“义务监督员”
韦东英没想到自己会“拼”得这么认真。除了继续写日记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外,原本对环保一窍不通的她还开始学着对污水取样,为了保留证据,她还学会了拍照。
2004年3月31日,韦东英从邻居家借来了相机,第一次去排污口拍照。
那一天,韦东英看到了江边大坝旁的死鱼。那刻的心情,韦东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样的情景让我看了就心碎,如果污水长期往江里排放,江里的水资源能丰富吗?”
自那之后,每当夫妇俩发现有企业往钱塘江里排污水,他们就会给当地的环保局打电话举报。有时,因为担心环保局人赶到时企业已经停止偷排,而没有证据处罚,韦东英就先用旧矿泉水瓶子接下污水做“样品”。
日子久了,韦东英居然成了“义务监督员”,没事时,常拉着丈夫一起去江边检查有无企业又在偷排污水。与此同时,韦东英在当地开始有了一些“名气”,村民遇到环境问题,也来找她反映情况。
由于向萧山环保局的举报迟迟不见结果,加上自己的证据始终不被环保局采纳,韦东英渐渐对萧山环保局失去了信任。为了能继续制止南阳化工园的污染,韦东英开始给杭州市,浙江省的环保部门打举报电话,并联合群众签名给国家环保总局写举报信……
直到2004年末,这个“义务监督员”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南阳化工园成了“杭州市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区”,萧山环保局也开始对南阳化工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之后,杭州本地媒体报道称“2007年底,南阳化工园将全部搬迁”。
再次上书国家环保总局
韦东英的目标似乎就要实现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2007年春节过后,韦东英的“证据照”已经积累了5斤多重,标满日期的取样瓶也排成了一排。但是,整个化工园却没有任何搬迁的迹象。
韦东英开始急了,她一一给萧山环保局、浙江省环保局打电话询问。然而得到的答案都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就已经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怎么可能呢?明明说了要搬迁的!看着3月3日自己刚从江边取的水样,韦东英怎么也不相信此刻南阳的环境会“达标”。 光线下,瓶子里的水呈棕色,有很多悬浮小颗粒。
这一次,她又将希望寄托在了国家环保总局。“我希望国家环保总局能够派工作人员到南阳实地调查,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如萧山环保局报告里所说的那样。还我们老百姓真正的知情权,让我们知道这里的环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过,相比2004年的那次举报,这一次的韦东英显得有些孤单。上一次,很多村民都在举报信上签了名,而现在几乎没有村民再关心这件事了。“做了很多事,却一直不见效果,他们不清楚还要弄这个干嘛?”
萧山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环保局设有激励措施,对每次举报偷排污水的人可以给其奖励500至1000元。
不过,韦东英说她从未享受过这种奖励措施。3年多的“义务监督员”生活,韦东英在陪上自己的时间、精力及金钱之余,没有得到环保局一分钱的奖励。
爱恨环保局
在萧山环保局,韦东英也算是一位“名人”。3月初,萧山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表示,他们也曾多次邀请韦东英出席环保局的一些会议。
对于韦东英对萧山环保局的不满以及不信任,萧山环保局表示可以理解,因为韦东英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环境,只是对政策法规以及环保部门的运作不清楚,才产生了一些误解。
环保局似乎也有自己的苦衷。
据萧山环保局城乡环境督察中队的工作人员介绍,萧山环保局现有三支督察中队,通常,遇到企业偷排污水的情况,督察中队应在2个小时内赶到现场。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并不能完全实现。一个督察中队,通常有三名工作人员及一台车。如果接到举报时正在另一个执法现场,那么2小时内通常无法赶到另一个现场。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督察中队的工作也很忙,平均下来一天要跑3到4个地方。除了举报,还有自己组织的突发检查。一旦发现偷排污水的情况,通常会罚款1到10万元。来自萧山环保局的数据也显示,2006年,该局的行政处罚高达1200多万。

对于南阳的环境问题,萧山环保局相关人士表示,“2006年夏天,我们‘挖地三尺’,清除了所有的地下偷排管网,还关停了3家污染企业。2006年8月,南阳化工园已经成功摘掉了‘杭州市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区’的帽子。现在,所有的污水通过新建的管网统一排放到污水处理厂,不可能再有污染了。”
在园区工人李先生看来,现在化工园的空气明显比三年前好了很多。不过,他所在的工厂因为2006年被环保局进行整顿后,效益差了很多,原先5个车间现在只剩2个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韦东英还要“闹”下去,企业也觉得很难理解。镀锌厂一位姓斯的负责人表示,“污染厂都关停了,剩下的环境都达标,我们是没有污染的”。在她看来,韦东英之前的“闹”是为了保护环境,现在连政府都说这里的环境达标了,韦东英要是再“闹”下去,就有些无理取闹了。
谁阻碍了公众参与?
韦东英从不觉得自己是在无理取闹。
“我们的那些标语上都写了‘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我想我有权利检举污染行为。”韦东英说,她不是很懂法律,但是如果村里要建污染企业就应该先通过村民。不然,村民就要把它赶出去。
事实上,近几年,像韦东英一样开始关注身边污染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和韦东英一样,希望能够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知道周围的企业是否有污染,是否破坏了环境。而这也引起了国家环保总局的关注,“公众参与”日益成为环境保护中的一个流行词。
2005年的“圆明园环评风波”,更是引爆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甚至有下岗工人自费远途来到北京,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叫停圆明园防渗膜工程的建设。
2006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出台了中国环保领域的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于这部匆匆出台的规章,环保部门也坦陈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今年的“两会”上,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关牧村也提交了《用法律手段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的提案。希望法律规定和保护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监督权、诉讼权;公民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提出控告和检举,并有权对有关政府部门的环境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韦东英说,她不懂什么是公众参与,也没想过自己会和一座化工园较上劲。不过她很希望这次人大代表能够真正把南阳化工园的环境污染调查做好,因为这个事她不想再做了。
“我太累了,撑不住了,我文化程度也不高,实在做不下去了。我想请他们(人大代表)把我们的环境弄好。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想他(丈夫邵关通)去捕鱼,我去卖鱼,我就想过这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