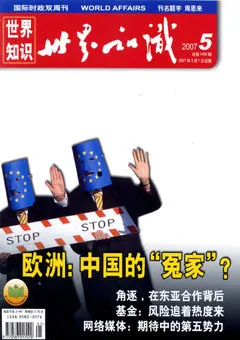西天诸神的魅力

婆罗门教、佛教和印度教彼此促生,相互借鉴,它们都萌生在雅利安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构成古印度文明的精髓部分,是印度文学、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的思想灵魂,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中印友好年”的重要文化交流项目,《西天诸神——古代印度瑰宝展》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首都博物馆隆重开展。此次展览不仅有助于唤起人们对中印文化的关注,还会让观众饱览古印度宗教的无穷魅力。
婆罗门教:雅利安祭司的虔诚颂歌
婆罗门教是南亚次大陆上古老的原始信仰,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在入侵者雅利安人残酷的征服战争中逐渐形成。这个牧牛民族的故乡本在遥远的中亚,他们为了追逐水草而率先侵袭伊朗高原,接着又分批向西迁徙闯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或向东南挺进渗透到南亚的恒河流域。
大批印度土著居民在雅利安的战车和刀剑下魂飞魄散,幸存者悲惨地沦为征服者的奴隶。为了庆祝伟大胜利,雅利安祭司用梵语把不朽功绩书写成美妙的赞美诗,祈祷武士们获得继续前进的勇气和魔力。《梨俱吠陀》、《耶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便是这些颂歌的合集,传唱着一个动荡时代的壮烈旋律,蕴涵着婆罗门教的思想内核。然而,真诚质朴的吠陀圣歌不足以表达抽象奥妙的神意,须有哲理学说对其加以阐释才能深入人心,《梵书》和《森林书》等一系列典籍就发挥了这般作用,推波助澜地把雅利安宗教思想升华到极致。这些看似陌生的文献并非神秘天书,其中一些典故已悄然在我们耳边传诵多年,譬如家喻户晓的盲人摸象的寓言就出自《奥义书》。尽管有了健全的理论体系,深奥枯燥的教义仍然很难被普通人接受,于是虔诚的知识分子信徒便开始编写引人入胜的神怪故事,并且历时数百年之久,最终汇集成《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两部恢宏的长篇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获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婆罗门教信仰来自原始的万物有灵论,被人们崇拜的神祗往往是多种自然现象的人格化形象,罩染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数不胜数的婆罗门诸神中,造物主梵天、破坏神湿婆和保护神毗湿奴居于最显赫地位,主宰着世间万物。毗湿奴有四臂,头戴宝冠,手持仙杖与海螺。他变幻无穷,经常化成英雄或走兽,帮助雅利安人战胜强敌,闯出逆境。在他的多种化身中,牧童克里希纳是比较多见的一种,曾用单臂举起戈瓦尔丹山,让牧人和牲畜躲到山下避雨,度过了洪水的劫难。毗湿奴还让英雄摩奴造了一艘船,载上家人和七位圣贤,然后自己变为一条大鱼,引导那条船停泊在一处山顶,直到洪水退尽。《罗摩衍那》主人公罗摩也是毗湿奴的化身,他在神猴哈努曼的帮助下,打垮了印度南方岛屿上的十首恶魔罗波那,此举象征着雅利安人对斯里兰卡土著人的征服。神猴是一种图腾,代表着印度半岛上某个雅利安同盟部落。神猴哈努曼的故事被佛教吸收,并随之传播到中国,为神话小说《西游记》主人公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形象提供了原型。

婆罗门教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种姓制度。随着古印度社会的发展,等级制度越来越鲜明,人们被划分为高低不同的种姓阶层。祭司地位最优越,被称作“婆罗门”,他们的使命是学习吠陀经典和主持祭祀仪式;王公贵族及武士属于“刹帝利”,用武器保护百姓们的财产;“吠舍”是雅利安自由民,从事农业、商业和畜牧业,承担着供养婆罗门的义务,同时还要向武士们缴纳税金;被征服者则叫作“首陀罗”,这群人没有任何权利,惟一要做的就是用劳动来奉养高种姓阶层。婆罗门教千方百计给这种不公平现象制造依据,《梨俱吠陀》最后一卷描述了种姓的起源:“当原始人普鲁沙被众神当作祭品进行分割时,他的嘴成了婆罗门,他的双臂造出了刹帝利,他的双腿变成吠舍,他的双脚生下首陀罗。”婆罗门教还宣扬业报轮回说,声称欲望会唆使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中有所表现,这叫做造“业”。人死后要按照“业”的好坏,投生到较高或较低的种姓。业报轮回说把被压迫者受苦的原因归结为前世活动的后果,劝说大家修身忍性,以此消弭反抗情绪。
佛教:释迦圣者的艰深足迹
雅利安祭司之所以能够享受更多权利,皆因古时大事“唯祀与戎”(只有祭祀与战争)。献祭是雅利安人行动的主导,他们常常用牺牲动物的手段征求天意,有时甚至靠杀人来表达对神的无限敬仰。传说婆罗门祭司的咒语还有神奇魔力,可以帮助刹帝利在战争中取胜。刹帝利种姓在战争中以掠夺和扩大领土的方式使自己日益富有强大,到公元前5世纪,恒河流域崛起了军事国家,建筑浮雕上的狮身鹫首有翼怪兽就是强大王权的象征。刹帝利渐渐破除了对婆罗门的迷信,不但要求在政治军事上居于最高地位,还要求在宗教和社会等级中成为显赫群体。吠舍种姓中有很多人经商致富,他们对婆罗门祭司的特权地位深感不满,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来颠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
佛陀释迦牟尼本名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6世纪生于喜马拉雅山下的迦毗罗卫国,是统治者净饭王之子。这位王子的诞生非常离奇,据佛经记载,其母摩耶夫人梦见白象从自己右肋进入身体而受孕,14个月后才生出孩子。乔答摩长大后毅然放弃荣华富贵去游历苦行寻求真理,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千百年来备受信徒尊崇。有学者研究证明,迦毗罗卫国实行的是共和政体,国王都在民主选举中产生,所以乔答摩并无继承王位的重任,他的出家也就没有太多牵挂。在一株菩提树下静坐49天后,佛陀终于茅塞顿开。他悟出人生苦难的根源在于“欲爱”,由此提倡清心寡欲,用八种“正道”来实现解脱,同时还号召众生平等。早期佛教从婆罗门教中汲取了许多养分,它不仅接受了业报轮回学说,而且还把一些婆罗门神祗任命为佛陀的守护者。

释迦牟尼毕生致力于弘扬佛法,足迹遍布印度各地,80岁时在居师那迦安然圆寂。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的阿育王大力扶持佛教,全国范围内修造起大量别致的寺院和精湛石窟。这时印度还出现了一种半球形的砖石建筑“窣堵波”,用来盛殓佛陀、僧侣或圣徒的遗物,中国的宝塔便是从“窣堵波”演化而来。随后的大约六七百年时光中,无论是大月氏人的贵霜王朝还是雅利安人的笈多王朝,统治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组织佛教徒结集,讨论有关佛教的理论和教义等事务,加快了佛教传播。恒河下游的那烂陀寺一度成为讲经说法的圣地,唐玄奘就曾来这里求取真经。佛教在笈多王朝时期显现出衰落迹象,虽然公元8世纪后统治东印度的波罗王朝使佛教在那里保留着最后的繁荣,但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佛教在印度基本消亡。也有学者认为,佛教衰落是因为商业的不景气,毕竟商人是佛教财政收入的主要提供者。
印度教:湿婆的毁灭之舞
公元4世纪后,由于佛教和耆那教的发展传播,婆罗门教开始衰落,但这个原始信仰并未消亡。公元8世纪,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印度传统宗教之一,耆那意为“胜利者”或“修行完成者”)的一些教义,结合印度的民间信仰进行了改革,逐渐脱胎换骨成为印度教。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便出自古老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最后篇章。
印度教哲学家宣扬人生有四个目的,即“法、利、欲和解脱”。为了追求这些境界,他们把人生划分为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和遁世期几个阶段。青少年先要刻苦学习“法”,也就是万物的规律和人伦常理;成年后娶妻生子,在“法”的限定内追求“利”和“欲”;人到中年则要离家,去森林中苦行悟道;最后托钵修行,云游四方,终此一生。瑜伽就是印度教徒克制炽烈欲望,以求解脱的修炼手段。
印度教仍然信奉婆罗门教的三大主神:梵天、湿婆和毗湿奴。湿婆常常以舞王姿态出现,他挥动臂膊,翩翩起舞,右手抓铜鼓,左手持火焰,脚踏“无知”的人格化身阿帕斯马拉。印度教徒敬畏湿婆的破坏力,认为那迷人的舞蹈实际蕴含着毁灭世界的超级能量,并流传着很多关于湿婆除妖降魔的故事。
印度教的魅力令人称奇,很多狂热的教徒竟甘愿以死殉神。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谈到古印度人在扎格纳特乘车节的庆典上,把巨大的毗湿奴神像安放于四轮车中拉出来游街,沿路会有一些教徒奋不顾身钻到车轮底下,被压得粉身碎骨,他们认为只有捐献出宝贵的生命才可达到敬神的最高境界。
婆罗门教、佛教和印度教彼此促生,相互借鉴,它们都萌生在雅利安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构成古印度文明的精髓部分,是印度文学、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的思想灵魂,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