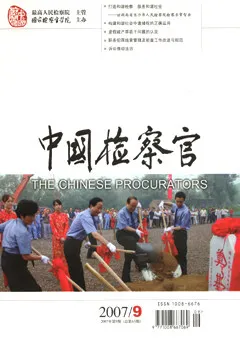同案犯发生损害的刑法评价
内容摘要:由四起同案犯死亡案件引发对其他同伙刑事责任的探讨。通过类型化方法介绍了实践中导致同案犯损害的五种情形及归责,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在共同犯罪行为本身具有某种危险性导致同案犯损害的情况下,其他同伙的刑事责任问题。
关键词:同案犯 发生损害 刑法评价
一、缘起:四则同案犯死亡案例引发的问题
案例一:2006年3月15日10时许,犯罪嫌疑人贺某、韩某、暴某(中途有事)伙同曹某预谋通过制造交通事故的方法勒索钱财。11时许,贺某、韩某、曹某选定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大货车作为作案目标,由曹某、贺某分别驾驶一辆小汽车在大货车前方行驶。当行至北京市某区路口处,曹某驾驶的前车(内乘贺某)突然制动后头朝东南横向停在公路上,紧跟其后的贺某驾驶小汽车紧急制动,大货车先将贺某驾驶的夏利车撞到旁边的路沟里,后继续前行又撞到曹某驾驶的桑塔纳车,曹某当场死亡。[1]
案例二:2005年春节前夕,犯罪嫌疑人王某窜至辽宁省朝阳市电柱厂一闲置车间,发现几根牵拉“人”字屋顶的钢梁。于是找到欧某商量把钢梁割下来卖钱。当时两人知道这样做有危险,就找到自称干过拆迁的姚某,姚到现场察看称,用水焊割就没事。2005年2月10日(大年初二)12时许,3人雇一辆农用车带着水焊机来到现场,就在姚某割下2根钢梁后,正要爬上一道主墙顶部旁边的钢梁上继续焊切时,屋顶突然坍塌,姚某被当场砸死。[2]
案例三:2004年9月10日,同住在上海闵行区的张某、谈某等三人酗酒后,预谋偷电线卖钱。晚8时许,3人准备钳子、扳手等工具,窜至位于浦星路的一条河边,发现一根电线杆上有三根电线凌空架着。在判明没有“通电”后,由阿土根(化名)爬上电线杆,裸手用钳子剪下电线,张某和谈某在底下接应。就在阿土根爬上第二根电线杆剪电线时,听见一声惨叫,阿土根从高处跌下来,当场死亡。张某、谈某恐盗窃行为败露,将尸体移至河中一小水泥船上,用电话线、布条将尸体捆扎在船上,将船沉入河中。后被河道保洁工发现。经法医鉴定,尸体已高度腐烂。[3]
案例四:2005年5月27日晚,张某、董某、陈某携带撬棍、杀羊刀、水果刀等作案工具,驾驶机动三轮车窜至宿州埇桥区北杨寨乡丁楼村,采取挖墙、撬锁等手段,盗窃丁某家黄豆、羊、啤酒等物品,价值2000余元。作案后欲逃离该村。在村西头,陈驾驶三轮车,张坐在后车厢,这时同伙董某从后面追赶上车时,张误认为董是前来追赶的村民,便用水果刀连刺两刀,致董某因大出血死亡。为掩盖罪证,两人在返回途中将董的尸体扔至一机井内,又将作案工具、三轮车抛弃、隐匿。后两人投案自首。[4]
上述四则同案犯死亡案给刑法理论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其他同伙应否对同案犯的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抑或同案犯发生损害应否纳入刑法之评价。
二、导致同案犯损害的原因及归责
从客观上讲,犯罪是存在风险的。这种风险不单指来自刑罚的惩罚,而且也包含犯罪过程中行为人人身财产的损害。就共同犯罪而言,导致同案犯人身财产损害的主要原因有:
(一)外力作用导致同案犯损害
主要是指纯粹意义上的非人为因素导致的同案犯损害。例如,某甲与某乙在实施共同盗窃行为过程中,甲因建筑物上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其伤亡。在该情形下,由于其他同伙主观上不存在犯罪故意或过失,客观上亦未实施任何侵害行为,甚至与共同犯罪行为本身没有关联,完全属于一种裸露的事实状态,不受法律评价。因此,其他同伙对同案犯的损害结果不承担刑事责任。
(二)正当防卫行为导致同案犯损害
是指在实施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害人或其他人基于正当防卫行为导致部分犯罪行为人损害结果发生。例如,A和B共谋抢劫某银行,正在实施抢劫行为的过程中,银行安保人员将A当场击毙,B被抓获。由于这种情形不具有可预见性,而且其损害结果又是因他人有意识的合法行为所致,与共同犯罪行为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其他同伙不应对同案犯的损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三)第三人无罪过行为导致同案犯损害
是指在实施共同犯罪过程中,第三人无罪过行为导致部分犯罪行为人损害结果发生。案例一中“货车司机致曹某死亡”就属于这种情形,在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货车司机不可能明知,也不具有预见义务,完全是处于一种无罪过状态,因而曹某的死亡结果对于货车司机而言,纯属意外事件。在第三人无罪过行为导致同案犯损害的情形下,如果同案犯损害结果属于共同犯罪行为的必然危险结果,其他同伙应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不属于,其他同伙则不承担刑事责任。
(四)共同犯罪行为发生指向性错误导致同案犯损害
是指在实施共同犯罪过程中,部分同伙基于打击犯罪对象的故意,因其他原因而发生指向性错误,致使同案犯人身财产发生损害。案例四中张某误认为同伙董某是前来追赶的村民,便用水果刀连刺两刀,致董某因大出血死亡,就属于该情形。法院认定张某指向性错误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五)共同犯罪行为没有发生指向性错误,但因具有危险性导致同案犯损害
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因其行为具有危险性以及部分同伙故意或过失导致同案犯或自身发生损害结果。例如,某甲与某乙为盗窃珍贵文物自行制造雷管,就在制造过程中,甲因往竹筒内挤压炸药过多,导致雷管爆炸,结果乙被炸死,甲被炸成轻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同伙希望通过犯罪行为致使同案犯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应当预见其犯罪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同案犯人身财产的,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损害结果,应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则属于意外事件,不承担刑事责任。
三、其他同伙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法理分析
对于共同犯罪行为具有某种危险性导致同案犯损害的,其他同伙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又将承担何种刑事责任等问题,需要作进一步地探讨。
(一)关于共同犯罪行为具有必然危险性的问题
1.必然危险性的判断。比照刑法上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判断标准:一是主观说。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认识或所能认识的事实为标准,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危险性。二是客观说。以社会一般人对行为必然危险性的认识或预见为判断标准。三是折中说。以行为时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或预见以及虽社会一般人不能认识或预见但行为人能够认识或预见为基础,判断其行为是否具有必然危险性。[5]笔者认为,在判断必然危险性时,应采取折中说,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行为人行为时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2.纳入刑法评价的必要性。在共同犯罪行为具有必然危险性的情况下,其他同伙主观上对行为产生的危险范围和结果是有明确的认识或者说估计、预测的,而且积极追求这种危险发生,或者因考虑不周、指令、操作不当或其他疏忽大意的事由致使这种危险发生;客观上实施了具有必然危险性的共同犯罪行为,并造成了同案犯损害的结果。因而,其他同伙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评价基础,应纳入刑法评价。至于该危险是由其他同伙还是由受损的同案犯自身实现,在所不问,只要其行为是共同犯罪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预备行为、实施行为和事后逃离现场行为,均可以追究其他同伙的刑事责任。
3.刑事责任的认定。在必然危险性的情况下,存在故意与过失两种责任体系:(1)其他同伙希望通过“虚假”共同犯罪行为致使同案犯人身财产损害。例如,甲欲害死乙,一天甲与乙“共谋”去盗窃藏獒,实际上这些藏獒系甲所养。在盗窃的过程中,乙被甲养的藏獒活活咬死。甲则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不成立盗窃罪。(2)其他同伙应当预见共同犯罪行为具有必然危险性,因疏忽大意致使同案犯损害结果发生。例如,甲、乙共谋盗窃高压电缆,其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这种危险性,但因一心想到卖钱后如何挥霍而忘记采取任何防电措施,结果乙被当场电死。如果盗窃电缆数额较大,甲则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和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关于共同犯罪行为具有或然危险性的问题
1.或然危险性的含义。实践中,或然危险性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共同犯罪行为本身危险性不大,也就是说导致同案犯损害发生的机率低,二是在特定条件下,原本较小的危险被临时放大。例如,案例二中王某等人预谋盗窃屋顶上的钢梁,王某、欧某已经预见其行为具有一定危险性,但在找到自称干过拆迁的姚某后,这种危险性被大大降低。就在姚某采用专业切技术割下2根钢梁,正要爬上主墙顶部旁边的钢梁上继续焊切时,屋顶突然坍塌。这样,原本较小的危险性又被临时放大。
2.或然危险性不应纳入刑法评价。一种危险能否被归责,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如果尽到了一定的注意义务,即使风险发生也不能归责于行为人;反之,如果未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则应将危险归责于行为人。而在共同犯罪行为具有或然危险性的情况下,行为人注意义务一般要求比较低,即便行为人未采取防范措施,也不能由此追究其刑事责任,或危险被临时放大,因行为人事前无法认识,应属于意外事件,而不属于故意或过失。
3.其他同伙行为的定性。在或然危险性情况下,其他同伙行为的定性应区别对待:(1)对同案犯损害结果不承担刑事责任;(2)如果原共同犯罪行为构成犯罪的,应按照其触犯的罪名定罪处罚;(3)如果将死伤的同案犯隐匿、抛弃的,按照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帮助毁灭证据罪、侮辱尸体罪或其他罪名定罪处罚。
(三)关于允许同伙制造危险的问题
这里的允许同伙造成危险,是指同案犯不是故意地给自己造成危险,而是在意识到某种危险的情况下,让其他同伙给自己造成危险。例如,同案犯指使同伙违反禁止性规定超速行驶,目的是希望追上前车实施抢劫行为。由于车速过快,导致车祸,造成同案犯(指令者)死亡。在这个案例中,超速行驶是违法的,由此造成了同案犯的死亡后果,能否以过失致人死亡对其他同伙(驾驶者)定罪处罚?一般认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依据是被害人承诺的理论,认为具体法益所有人可以对他人侵害自己支配的权益表示许诺,从而阻却他人侵害行为的违法性。
但是,德国学者罗克辛认为不能以被害人承诺的法理解决该问题。因为被害人认为虽然存在危险但这种危险并不会实际发生,具有某种侥幸心理,因而并不存在对危害结果的承诺。罗克辛还指出,既然被侵害人本身就是其所遭遇事故的肇事人,如果还需产生一种刑事惩罚,这是令人难以满意的。[6]在本案中,其前提是同案犯完全认识到某种危险,并且有意识地造成了这种危险,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其他同伙对同案犯损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相反,如果是其他同伙说服了犹豫不决的同案犯,并对同案犯隐瞒、淡化了这种风险,或者事故是由于与被接受的风险无关的驾驶错误造成的,则可以追究其他同伙的刑事责任。
四、结论
同案犯发生损害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其他同伙才对此承担刑事责任:一是共同犯罪行为发生指向性错误致同案犯损害的;二是共同犯罪行
为具有必然危险性致同案犯损害的。
注释:
[1]本案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北京市首例“碰瓷”致同案犯死亡案。详细案情与评判参见《“碰瓷”勒索他人却致同伙死亡的行为如何定性》,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1期。
[2]参见《胆大小偷竟偷房梁厂房坍塌砸死小偷》,载《南京晨报》2005年2月18日。
[3]参见敏谂:《盗窃触电身亡贼伙沉尸构成侮辱尸体罪》,载“中国法院网”2005年3月18日
“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
154844&k-title=盗窃触电身亡”
[4]参见张成伍、欧阳顺:《偷盗误杀同伙进牢房》,载《安徽日报》2006年5月10日B2版。
[5]参见黎宏:《刑法因果关系论反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5期。
[6]参见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