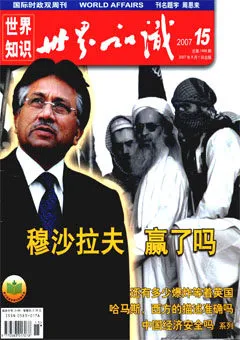怎样对老外说“不”
商务交往中说“不”,要分场合和条件,还要有艺术性,否则就会有不好的结果。老说“不”的人会被认为难以交往,对于做销售的人来讲这可能直接导致商机的丢失;但不得不说“不”的时候就要干脆明了地说“不”。有时说“不”反而会受到尊重,引起对方的兴趣。究竟何时说“不”何时不能说“不”,对谁可以说“不”对谁又不能说“不”,还要凭经验。
什么时候说“不”
不要随便对人说“不”。不要对自己潜在的买主说“不”,不要对谈判对手的大老板说“不”,就像不能对自己追求的女孩子说“不”一样。
一般来讲,什么时候说“不”,什么时候不说“不”,得看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做销售的时候,不应该说“不”,而当买方时就可以说“不”,因为不说“不”就会引起很多麻烦;求人时不能说“不”,而被求时就可以说“不”;自己着急时不可以说“不”,对方着急时就可以说“不”,以增加自己的要价;别无选择的时候不能说“不”,有备选时就可以说“不”。
对法国人尽量不要说“不”,因为他们比较爱面子,那就给以面子。对西欧贵族、有王室背景的人尽量不要说“不”,他们毕竟是贵族嘛!对阿拉伯国家的人少说“不”,因为大多交谈都没有下文,说不说“不”无所谓,又何必得罪他们呢?对日本人也最好别说“不”,因为他们表现得都很规矩,倾听时一口一个“哈依”,既然他老跟你说“是是”,你干嘛又要说“不是”呢?对美国人该说“不”就说“不”,因为他们习惯如此,如果他对你说“不”,你又为什么不能说“不”?!
不说“不”,并不意味着同意,含糊其辞是一种策略,只是让对方的感觉好一些,觉得你这个人可以交往。实际上,大部分场合的承诺都是不了了之,不置可否则是会谈中常用的方法。
我和纽约一家投资公司的会谈就是如此。当时我希望搞清对方的背景和他们在我们的项目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我推荐的公司表示了兴趣,介绍人又说他们是一个很有钱、可以参股的投资公司。可是当介绍合作方式时,我感觉他们希望做中介,为我们推荐的公司提供上市服务,而不是作为战略投资者直接参股。于是在会谈快结束时,我特别明确地问:你们究竟想在这个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合资人还是中介?
面对一桌子人和我这个咄咄逼人的问题,那个把领带像绳子一样挂在脖子上的胖胖的犹太人挤眉弄眼地说:“我早上是父亲,中午是儿子,夜里则成为丈夫!”
大家哄笑之间,我知道他已很巧妙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因为这类公司会根据不同的项目扮演多重角色。
尽量不说“不”
有次和某个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会谈,那是个相对贫穷的中东国家,可大使一开始却对我说起他们国家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事。我以为听错了,叮问了两遍,大使有些不高兴,一个电话把翻译叫来了。他和翻译说的阿拉伯语我更听不懂,翻译成中文又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依然用英语和他对话。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我再也没有打断他,听不懂也只好装懂,毕竟,大使到哪里都是受尊敬的人物,我不能让他觉得我认为他的英语不好。不过,他的口音实在太重,连我带去的既懂阿语又懂英语的同事,有时也搞不清他在说什么。
在介绍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向他说明这是一个金融性的机构,既作投资也有生产性企业,又是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的结合体。但这种什么都做的公司在一些国家确实不多见,所以大使听后也是一头雾水,问了我三遍:中信究竟是企业还是银行?我知道言多语失,如果我一开始就只从生产或者金融的某一个角度去介绍我们公司,恐怕效果会好一些。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像中信这样的公司,尤其对较小的阿拉伯国家,说多了反而让他觉得我有吹牛的嫌疑。所以,我在临走时灵机一动,把他拉到院子里,从树缝中就能看到京城大厦矗立在不远处。我告诉他,亮马河对面的大楼就是我所在公司的总部,是他真正的邻居。
大使最终相信中信是个不小的公司,表示以后要带他们国家来访的部长拜会我们。

我们公司对这种礼节性的访问比较头疼,因为这样的高层代表团要见我们的高层,可又没有实际业务,总公司领导就不愿意多见。我明知道不好办但还是应承下来,毕竟是我们在推销自己,不愿意说“不”,以免给他一个难合作的印象。
果然,至今他也没有带部长来访,没给我添麻烦。但如果我当时说“不”,就白白得罪了他。
该说“不”就说“不”
有一次,我陪同我们公司内部的投资者去辽宁考察两个项目。安排日程的时候就一波三折,因为那两个项目的管理层不够热情,没有提供多少材料,也没有什么安排,于是投资者就不想去了。他告诉我,去外地考察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是对方负责接送和当地的食宿。
我告诉他,条件不好的项目的管理层,往往在接待上多下工夫,尤其是受政府支持的项目,他们把招商引资当成一个任务,也肯为此花预算,但是项目本身好坏就很难说了。作为投资者,要的是项目的回报,而非接待上的热情。我介绍的项目公司牛得很,既不接送,也不安排当地的食宿,但他们连年收益,未来利润预期很好,会给投资者提供丰厚的回报,所以受投资者的追捧,去谈判的人很多,他们没那么多时间用于招待,也不想花那么多的招待费,投资者愿来就来,不愿来就算了。
我这样实话实说了以后,我们的这位投资者反而去了。因为他知道,好的投资项目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是受人追捧的,就像投资者受人追捧一样。
不得不说“不”
有一次我们接待的投资者则是个另类。
那是法国的一家大型传媒集团,董事长和总裁先后离职。董事长在加入一家私人银行后,到中国来访问,对我们正在做的、需要投资4000万的媒体项目很有兴趣,但是回国之后,对我发去的电邮却全然不理睬。两个月后,他突然让他在香港的伙伴给我回了一个电,说董事长派来了前总裁,人已经在北京,第二天就要和我们谈。我知道这种突然约见的方式并不是法国人的习惯,对于按部就班的法国商人来说,一个跨国的约会,往往提前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就开始约定,因为这是一个按照日程表行事的民族。如果说人已经万里迢迢到了北京,第二天就要和我们谈的话,只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者原来安排的约会被取消,拿我们填补空缺;或者他临时想起我们,既然到了北京,就应付差事,顺便谈谈。总之,经验告诉我,他们并不是为我们项目来的。
前一次我们会谈时,离职董事长告诉我,他来北京两天,其中一天去山西平遥了。我知道像他那样的资深人士,来中国只是一般性考察,而游玩就占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到我们公司谈判是为了回去给董事会一个交待。这就像我们一些出国考察的团组一样,主要目的是游玩,顺便见一下当地知名企业,交换个名片,以便回来写出差报告。
这次接待的前总裁更牛,进门后大大咧咧坐下,面对我方一桌子人,拿出我给他们发的两页项目概要,不耐烦地抖着说,有没有比这更多的东西?一脸的傲慢。我看到他接到别人的名片就随便放到桌上,连礼貌的寒暄都没有。我犹豫后还是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因为毕竟想知道谈判对手的背景。结果他拿过来放在桌上,同样不给他的名片。
我有些不高兴,因为法国人一般比较礼貌,名片没有会特别说明一下。于是我很不客气地问:“你有名片没有?”可他竟然说:“什么是名片?我不是来此地了吗?”好像他来公司谈判是对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也就没好气地跟他说:“我们的材料是给投资者的。”暗示并没把他这样的人当成真正的投资者。结果这家伙气急败坏,更粗鲁地用法语对他同事讲:“他想要什么?要我现在就拿出4000万吗?”
那会儿我真想告诉他:你不用拿4000万了,我们也不必继续谈下去。然后把他轰出门。
只是,我们的项目不够成熟,团队也不够老练,又是第一次接待来自欧洲的投资者,借机演练一下队伍没有坏处,所以我才给他留下谈的机会,但是始终把他想要的、30多页的商务计划书正文放在手边。我要让他知道:我们有详细的项目介绍材料,可就是不给你,因为没把你当成有诚意的投资者。
在分手的时候,我只是冷淡地和他握手道别,连会谈室的门都没出,就让他东张西望地穿过我们弯弯曲曲的走廊,自己摸出去了。而通常对来访者,无论是投资人还是找我们投资的,我都是送到电梯门口,而且这还是在法国养成的习惯。
说“不”常常是最后的选择
商业谈判中,有时候说“不”是不得已的事。就是说,本不应该说“不”的场合,也没有说“不”的打算,但最后逼到那个份上,除了说“不”,没别的选择,那就只好如此。因为说与不说,结局都一样。
社会上有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但投资者并不是上帝。顾客是消费者,是弱势群体,他有改变主意和挑剔的权利,他毕竟是购买者,而商家是以卖出商品为目的的,所以可以把顾客奉为上帝。
投资者则不同,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是强者。他们虽然也有改变主意和挑剔的权利,但是受资方并不是以卖出为最高目的的,而是要卖一个好价钱。如果价钱不好,他宁可选择不卖。投资者购买项目这类东西有其目的,就是赚更多的钱,这种钱可能是项目进展本身带来的现金流,也可能是将他自己购买的股份兑现。总之,赚钱是其投资的真实目的。他是来分享利润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投资者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圣诞老人。
在谈判桌上,受资方和投资方应该平等相待。如果投资人一开始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是给人送钱来的,那谈判的天平就会倾斜,结果也不会理想。投资毕竟不是济贫。因此,对受资方来说,如果把投资者当成上帝,好吃好喝地供着,也不是件好事。那会给投资人一种优越感,他还会怀疑:他们怎么那么能花钱,我投资后,他们还会这么花吗?
所以,中国一些地方企业招商引资失败,有时就是因为他们给出的条件太好了,反而让投资者不相信。他们招待也太铺张,造成大量浪费,投资人会觉得:他们花自己的钱都这么铺张,一旦投资,那花我的钱又会怎样?!
我们需要西方投资者,不仅需要他们的钱,还需要他们的经验。每次和投资者的会谈,回答他们形形色色的提问,对我们都是一种演练。我们会知道投资者最关心哪类问题,以便下一次有针对性地做准备。但对那些狂妄的人,我也会让他知道他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不尊重对手的人,自己也不值得被尊重。
对这种人,恳求和热情是没用的,如果你不得不说“不”的时候,就痛快地告诉他。
敬请关注下期系列之五:见老外时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