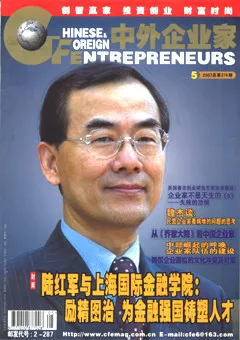论中国无罪推定原则的完善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文件所确认,也为《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法律文件所认同。是否推行这一原则已成为衡量各国民主法治发展程度和刑事司法领域中人权保护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在刑事立法中虽对无罪推定原则有所体现,但尚未建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为了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保持一致,严格执行我国所加入的国际公约,同时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在我国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宪法地位
无罪推定是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其规定在宪法之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11条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律举行公开审判中,依法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无罪。”《俄罗斯联邦宪法》在第2章“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第49条规定:“每个被控告有罪的人,在其罪未被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证明和未被法院所做出的具体法律效力的判决之前,都被视为无罪。”由此可见,无罪推定是一项强调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原则,与公民的人权保障密切相关。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对无罪推定原则作了表述,该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强化了法律对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原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它表明新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我国在宪法中也应当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9条第2款均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因而将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载入我国立法,将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它的重视,从有罪推定的误区走出来,进而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2条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是说在人民法院未做出正式判决以前,不能确切认为被告人有罪。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既不能认为受控者有罪,也不能认为其无罪,而是将其诉讼地位置于一种不确定的中间状态。而无罪推定的基本精髓在于:在法院未做出正式判决前,受刑事指控者一律被推定为无罪,是诉讼主体的确定状态。也就是说,在未经法院最终确切认定被指控者有罪之前,只能承认其本身原始的无罪状态。可见,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与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仍有区别,不是根本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应修改为:“任何人在人民法院做出生效判决之前,应视为无罪的人。”立法只有将无罪推定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才能将被追诉者作为独立的、与法官和检察官平等的人格实体对待,明确确认被追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真正赋予其与诉讼主体地位相适应的各种诉讼权利并设置程序保障措施,从而使无罪的人不被刑事追究。
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内在要求,没有沉默权的无罪推定,只能是不完全的无罪推定或者根本就不是无罪推定。而我国修改刑诉法并没有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理论界对沉默权的讨论直到今天仍在进行。充分考虑我国的现有条件和社会的接受程度,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坚持贯彻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国际标准,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在制度设计上,应从保障基本人权的高度出发,着眼于“确认权利”,而非“限制权利”,确立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沉默权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被羁押之日起至刑事诉讼程序终了时止均可行使沉默权,保障每个公民面对国家官员的讯问时能有效主张该项权利。同时,为尽量避免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还应建立鼓励供述的诉讼机制(易延友:《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应如实回答”的规定
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告知其享有沉默权,还应一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做出无罪或罪轻的辩解,有权对有关其个人基本情况以外的问题拒绝回答;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犯罪嫌疑人有消极忍受讯问的道德义务。
2.坦白从容、抗拒不从严
废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权,拒绝回答侦检人员、审判人员提出的问题不得仅仅因此而直接推断被告人有罪,也不得把沉默、拒绝回答问题作为从重处罚的根据。
3.拓宽、完善告知义务
应规定审判、侦查、检查人员,在刑事诉讼的各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告知义务,其范围应从原有的回避、辩护权利,扩大到供述自由,由个人承担虚假供述责任,不得劝供、骗供、诱供,更不能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4.有限的例外规则
刑事诉讼肩负着双重任务,即打击罪犯和保护人权。前者要求被告人如实供述,后者要求遵从被告人保持沉默的合理权利,平衡双方利益的结果就是对沉默权予以限制,但这种限制只能是有限的,即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被告人可以保持沉默,但司法人员可以做出对其不利的推定。借鉴其他国家对沉默权限制的立法,我国在引入沉默权时,也应该对其进行合理限制,笔者认为,对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紧急状态的特殊案件中,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被调查人员有“义务”如实回答,否则将对其作出不利的推定,具体哪些案件属于“特殊”的范围,在刑事诉讼中根据现行刑事实体法的规定先行引举。
四、完善疑罪从无从无制度
1.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
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变更问题,人们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判决以后,获取了新的、充分的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重新审判。例如《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一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退一步论,即使被告人真正有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经进一步工作,获取了新的、充分的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仍然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周道鸾,《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判决在性质上是无罪的,与无罪判决在法律后果上完全相同。法院判决后,如果侦查机关后来又取得了犯罪的证据,可以另行起诉。”(胡康生、李福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由此可见,对一个经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无罪判决如何处置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上述两书作者直言不讳,即有了证据另行起诉、另行审判就是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涉及到生效判决的稳定性问题,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新起诉和重新审判问题。在诉讼理论上关系到“一事不再理”诉讼原则问题,在程序上关系到审判兼程序的适用问题,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因为人民法院判决的变更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指案件一经法官宣判后,就发生“既判力”,不能因同一罪行而对被告再次起诉。即“同一案件曾经有实体上的确定判决,其犯罪的起诉权业已消灭不得再为诉讼之客体”(蔡墩铭,《刑事诉讼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这一原则为后人在刑事诉讼中广为适用,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西方国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甚至还把它规定为宪法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受同一犯罪处分的,不得令其两次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事实而重新被拘押或起诉,即使是以其他罪名案。”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适用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法院裁判的权威,兼以保护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以免其因同一案件而受多次裁判。
2.修改刑刑诉法第189条
虽然刑诉法第140条、第162条都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处理规则,但在审判程序中却明显违背这一规则,应将刑诉法第189条第3款:“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修改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定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确保立法的一贯性与原则的统一。还应当明确疑罪从无的既判力,废除经过补充侦查、证据充分后再次起诉的规定,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将控诉不利的后果转嫁给被追诉者,使之处于可随时被再行追诉的境地,确保疑罪从无的确定性。
无罪推定原则为世界上众多国家采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刑事诉讼基本准则,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标志。虽然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但我国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在立法上依然有些规定与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公然对立或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不断发展完善,同时严格执行我国所加入的国际公约,我国应当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内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进一步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