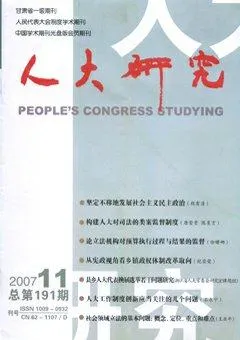有关选举制度的国际人权法理论和标准
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制度是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民主国家,选举就是授权,因此,选举也就成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在国际人权法体系中对如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作了详尽的规定,规定了缔约国应履行的国家义务和应保障的公民权利。尽管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的民主模式各异,其选举制度和选举权的内容也不同,但是其选举制度的设计均应符合国际人权法的相应的一般规定,履行一国的国际法律义务。
我国早在1998年就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并且2005年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所以根据国际人权体系,尤其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有关选举权的规定,对我国的选举制度改革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当下选举制度的改革也是我国向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迈进的重要的一步。
综上所述,无论在国际人权理论上,还是对于我国的选举制度的实践,以国际人权法体系中的标准为视角讨论我国的选举制度改革有很大意义。
国际人权法体系中有关选举制度的描述,主要是通过对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和保护来实现的。所谓选举权,就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参与国家选举的权利。选举是现代民主、文明国家的基础,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在民主社会,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政府,政府也因之取得合法性,同时人民也可以通过选票来改变政府,以实现公共权力机构的和平和有序地让渡和更迭;被选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被选举为国家代议机关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和选举权密不可分,它们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公民不仅有选举他人执掌国家权力的权利,也有被选举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直接执掌国家权力的权利。被选举权同样来源于人民主权,只要被选举人符合法定的条件,并取得了多数选民的认可和信任,他就可以进入国家机关,担任国家公职,行使国家权力,参与国家管理。选举权不仅仅是“投票权”,还包括投票所必需的知情、获得允诺等权利,以及作为保障与救济所必需的对选任对象的任职考核、罢免等权利;被选举权也不仅仅是“当选权”,还包括作为当选前的参选、竞选、候选等权利,以及当选之后的任职、辞职等权利。
由于选举是现代国家公民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为了保证选举的规范和有效,在法治社会,国家都会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通过立法来保障选举权,规范选举行为。如规定享有选举权的主体、选举的原则、选举的程序、选举的方式和对选举权的救济等。但不管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普遍、平等、自由的选举应是民主国家选举权的基本要求,同时国家也有义务为公民行使选举权提供法律和经济保障。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原则,并且在相关国际条约中给予确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十一条规定:(一)人人有直接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二)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1]。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二十五条规定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2]。
上述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权利,只有这些权利才完全具有民主参与的性质[3]。第二十五条的起草工作以《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以及苏联在1949年提出的一些草案和南斯拉夫与法国在1953年提出的妥协性建议为基础所规定的缔约国保障这种政治参与机会的义务,包括全面禁止歧视,明确了普遍、平等、直接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的选举,并且禁止19世纪和20世纪在资本主义国家很普遍、用以剥夺选举权的理由如基于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条件[4]。上述ICCPR的第二十五条,是国际人权法有关选举的核心条约,是最重要的有关选举制度的国际人权文件。
3.区域性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三条,各缔约国承担以适当的间隔和秘密投票的形式,在确保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条件下,举行自由选举,选举立法机关[5]。
《美洲人权公约》第二十三条,参加政府的权利,(一)每个公民应享有下列各项权利和机会:(1)直接地通过自由选出的代表参加对公共事务的处理;(2)在真正的定期选举中投票和被选举,这种定期选举应通过普遍的与平等的投票以及保证投票人自由表达其愿望的秘密投票来进行[6]。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第十三条,(一)每个公民均有权直接或通过按法律规定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自由地参与管理国家[7]。
4.正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1966年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HRC)所作出的第 二十五号一般性意见中第十条指出的:“选举权和公民投票权必须由法律规定,仅受合理的限制,如为投票权规定的最低年龄限制,以身体残疾为由或强加识字、教育或财产要求来限制选举权都是不合理的。是否是党员不得作为投票资格的条件,也不得作为取消资格的理由。” 第十一条,“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有投票权的所有人能行使这项权利。”
并且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八号、第二十三号一般性意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区域性人权机构关于这一权利个人来文的结论性意见;智利专家赫尔南桑塔克鲁兹在1961年应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要求所准备的有关在政治权利方面的歧视的联合国研究报告,明确阐述了政治权利在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方面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有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各种理论的阐释。
通过上述的各类国际条约可以看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国际人权法标准主要有:
(一)选举本身的要求:1.真正的。选民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影响,有资格的选民可以在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执政纲领,至少是单一政党的几个不同的候选人之间自由地进行选择。国际法不排除一党制,只要该一党制在该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基础上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代表了范围广泛的公众并呈现多元化时,在该一党体制内的不同候选人之间的选举就仍然是真正的选举。与此相应,HRC第二十五号一般性意见中强调,个人的竞选权不应该受到要求候选人应是某政党党员或具体政党的党员的无理限制,不得以政治见解为由剥夺任何人参加竞选的权利[8]。2.定期的。选举必须在常规的时间间隔内举行,具体时间间隔由缔约国决定,但不应过分地超出4至6年这一国家惯例。
(二)选举原则:选举的要义在于真实,即反映选民的真实意愿。如果公民在选举中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如舆论误导、政治压力、少数人操纵等,不仅选举的价值不能实现,相反,它还可能成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民主的核心是选择,而不是在已经选择的意见中进行选择,因此,民主是选举的价值取向。民主要求选举必须体现民意,从而成为民意的真实汇合,只有自由、公正的选举才能实现这一要求。“作为选举,只有当它是自由的和公正的时候才有意义。”[9]所以选举必须遵循一定的选举原则,主要有:
1.普遍的。即无限制,这对民主的、立宪的国家非常重要,意味着选举权不应只限于某些群体或阶级,而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无限制,是指无不合理的限制,即普遍是相对的,是一个由各国对其各自民主参与的理解所决定的相对原则。事实上,本条规定本身就存在限制,是公约中唯一一条不保障普遍人权,而保障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的规定,这就意味着缔约国可以拒绝给予外国人选举权。
2.平等的。普遍选举权涉及谁有权选举的问题,而平等选举权的原则则意味着在每一国家选举制度的框架内,投票人所投下的每张选票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划分选区和分配选票的办法不应该歪曲投票人的分配或歧视任何群体,不应该无理排除或限制公民自由选择其代表的权利。按照诺瓦克的说法,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选票的平等数量而言的[10]。
3.秘密(无记名)投票。这一原则是在ICCPR第二十五条起草过程中最没有争议的一条原则。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尊重投票的秘密性,而且还必须采取恰当的积极措施,保证举行选举期间投票保密的要求,并在有缺席投票制度的情况下,也对其进行保密。该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的影响,投票人可以不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压力,以免透露他们打算如何投票或投了谁的票,以及避免投票进程受到任何非法和任意干涉。本原则只涉及投票本身,而候选人的姓名以及为有效的提名候选人所需的支持声明都是公开的。
4.自由选举。主要是保护选民意志的自由表达。有投票权的人必须能自由投任何候选人的票,赞成或反对提交公民投票的任何提案,自由支持或反对政府不受可能扭曲或组织自由表达投票人意愿的任何类型的不当影响或压力。投票人应该可以独立形成见解,不受任何类型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强迫、引诱或操纵影响,参政政党和候选人能不受阻碍地开展竞选活动。这一原则与ICCPR第十八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十九条主张和发表自由,第二十条禁止鼓吹战争、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以及第二十一条和平集会权等政治自由有着密切的联系[11]。
(三)各公约中承认的对本项权利的限制:其首要原则就是这种限制必须是合理的。人权委员会第二十五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政治权利不受不合理的限制,换句话说,缔约国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对该权利加以限制,但不得歧视。1.限制的理由:根据各国国情、民主模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对选举权规定限制条件的理由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享受民主参与权利的人必须与国家有着某种关系即公民资格,并且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个人成熟性以能够为国家承担责任。2.限制的根据:必须是一国法律的规定。3.限制的内容:年龄、国籍、精神状况。在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所提到允许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只有两类人: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另外,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人们认为某些居住年限方面的要求以及剥夺某些被法院终审判定犯有某些罪行的人的选举权的做法,也可以被看做合理的限制。但是对选举权的广泛深远的限制,如文盲、军人、公务员、审前被拘禁者、反对派成员或妓女、流浪者、酗酒者以及吸毒者等“名声不好”的人排除在选举之外的做法,就不是合理的限制了。
对于被选举权:因为被选举担任公共职务涉及更大的责任,因此有时允许国家做出广泛深远的限制,某些在选举权方面不合理的排除限制在被选举权方面被认为是合理的。例如,担任公共职务的最低年龄通常要比参加选举的最低年龄高一些。对于有些职务,如国家领导人,国家通常规定了比参加选举的最低年龄高出很多。另外,某些候选人提名所必须满足的某些正式的条件,如一定的居住年限、支付某些费用或提供一定数量的支持声明等等,只要这些条件不是过分的或带有歧视性的,就是可以许可的限制,但是国家必须充分证明这些限制的合理性。
(四)国家的义务:
1.消极义务。即不歧视、没有不合理限制,在此不做赘述。
2.积极义务。对于本权利的保障,国家所负担的主要是积极义务,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享有该权利的所有人行使权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立法保护。建立完善的选举法等相关的法律制度,立法要符合公约的要求和人权精神,能够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B、机构方面,应成立独立的选务当局,监督选举程序以及确保选举以公平、不偏不倚的方式和根据与公约相一致的既定法律进行。
C、国家的公开义务。即将选举程序、候选人情况、选举结果等程序要做到公开,以保证公正地进行选举,并且通过这种公开以彰显一国选举制度的公信力,提高一国的公民参与民主的热情,改善民主环境。
D、保障公民与行使此权利相关的其他权利。主要是公约第十九条主张和发表自由,第二十一条和平集会权,第二十二条结社权等政治权利。这些权利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息息相关,只有公民能够充分行使这些政治权利,最根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才能够得以实现。
注释:
[1][2][5][6][7]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160、189、214页。
[3][4][8][10][11]【奥】曼费雷托·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432、437、442、444页。
[9]让马里·克雷特等著:《选举制度》,张新木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8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